湖南文联 2025-11-25 11:38:05

灯花照映荒原,丈量诗性人生——浅谈陈爱中诗集《灯花与荒原》
文|余瑞
当“灯花”穿越“荒原”,跨越南北地理的分界线,诗集《灯花与荒原》在陈爱中笔下完成了一场跨越十年的诗性重建。这部收录150多首诗作的集子,以“落雪・蝴蝶”与“月光・雨水”两辑为骨,以足迹与感悟为血,在个体抒情与诗学思辨的交织中,以具象诗作的深刻剖析为肉,为作者的诗歌创作递交了一份厚重答卷。这就如同诗人在序言中所讲“让这种感恩融汇到流淌的文字之河里,生生不息,当是最美的选择,于是我开始写作了。”
陈爱中的诗兼具鲜明的日常性与厚重的思想性,才情入诗,满溢文人气息,其核心在于意象系统的精妙建构。同时,诗人从不直白宣泄情感,也不刻意炫耀智识,而是将生活记录与哲思感悟藏在意象里,静待读者探寻。
诗行里的南北和鸣
诗集的底色是生命体验的广度与阅读思考的深度共同铺就的。十年光阴里,诗人的足迹从北国哈尔滨延伸至南疆南宁,八桂大地的风物与北域的雪色在诗行中悄然对话;而海量阅读积淀下的诗学素养,更让他得以找准坐标。这种“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的双重滋养,使得诗作避免了纯粹个人化书写的狭隘,挣脱了地域文化影响的桎梏。如果说“落雪・蝴蝶”辑深深烙印着北疆的精神胎记,更驮载着厚重的阅读思辨,那么“月光・雨水”辑则是浸润着某种独属于南疆的湿热感,将自然观察与主观感知熔铸成诗。
《在咖啡馆阅读陶渊明》中,“南山与篱笆,都是久远的无奈/却让后人层层叠叠地向往”,以陶渊明诗中的原型意象为引,直指隐逸文化背后“饥馑与贫穷”的现实底色,既凸显了精神的断裂,又揭示了在理想与生存间的双重失落。这种书写让诗作实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读者既能从“生活的记录”中看到可感的日常,又能在“不着边际的想象”中获得精神的跃升,正如灯花虽小,却能照亮荒原的纵深。《乌头白》短短六行便构建起多重隐喻网络,“秦王”与“太子丹”的身份对立,表露现实成功与理想殉道的抉择;“白鹭”呼应“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境,象征超脱的精神向往;而“泥淖”与“画地为牢”则直指现实困境与自我禁锢的精神囚笼,最终在理想与现实间彻底撕裂。《盛开的土豆花》以“白色”“粉红”的柔美花朵,绽放在历史创伤之地,最终归于“黑色”的毁灭与沉淀,用朴素的生命符号来反衬战争的残酷。《布满城堡的天空》中,“台阶”隐喻的信仰阶梯与“大炮、坦克”的暴力符号碰撞,“举手”与“屈膝”的肢体对比直指自由与压迫的悖论,在历史宏大叙事中照见个体的挣扎。
离开东北,在南宁生活数年,诗人依旧能写出“春天会躁动,夏天会泼洒/秋天呢,是一场不愿直面的事实/只有冬天,学会让这一切妥协”,简单两句便将自然意象与主观感知熔铸,既有生活观察的细腻,又有超乎寻常的想象跳跃。《邕江的记忆》中,“邕江”成为南方地域文化的诗意图腾,“我后来常常浸润到月光里/看银色如水倾泻/铺洒在你身上”,“月光”既是诗人个体感知的载体,也是历史记忆的见证,此刻诗人对这条江、江边人的感情达到某种致深的状态。而在对柳州的书写“启程的时候/扶柩的刘禹锡一定不会想到/落地生根的回返/会让这座城遍布柳州”,让历史的厚重自然浸润于当下景致。《木棉》中,诗人将木棉特质,精准比作中年的生命内质:“零落成泥碾作尘/忘掉自己/像极了中年的生活”,以自然意象道尽中年的沉淀与从容。这种个体与集体间的对话,让历史与现实在诗中凝望,擦出诗意火花,时间也在悄然中获得新生,形成独特的诗性。
和园与相思湖的诗性建构
在“月光・雨水”辑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和园故事》与《相思湖纪事》。如果说历史与哲学为诗集注入了深度,那么这两组诗作则以具象空间为锚点,构建起生命与救赎的精神镜像。诗人在这里生活工作,为人师、为人父,也许他在母亲那寻得的“灯花”会在此地传递给别人,成为他人照彻“荒原”的光。这两组诗延续了诗人“以日常见深邃”的创作特质,和园作为核心的空间意象,在《和园故事》中呈现出多维度的精神面相。“红楼”“白楼”的建筑符号与“榕树”“龙眼树”“三角梅”的自然意象交织,构成了记忆与现实的双重场域;“走廊上的镜子常常映现时光的幼年”,镜子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媒介;叠加的足印里既有“星辰的私语”,也有“高堂讲章的流布”,让和园成为“故我的”精神原乡。而“深秋淡去酷暑”的季节流转中,榕树“延伸出无数飞翔的翅膀”,与“宇宙射线的锐气”相互交织、贯通,赋予这片空间以突破禁锢的诗歌张力。其间最动人的莫过于“我们年轻到无法谈及生命/却在饱经沧桑的榕树下谈起救赎”的慨叹,青春的懵懂与榕树的沧桑形成强烈对照,将个体成长的迷茫置于时间的纵深中,让和园成为承载精神叩问的“哲学”场域——“和园是故我的”“和园是丰沛而妖娆的”“和园是执着而仁慈的”“和园会是归来的样子”“和园是哲学的”“和园是盎然的”。作者已经深入和园,了解它的深沉、典雅,也试图去探寻它的差异与独特,建构属于他的和园精神图谱。
《相思湖纪事》则在和园的基础上,将空间意境进一步延展与深化。相思湖的“沐紫荆”“多瓣槿”“三角梅”与和园的“竹林”“木棉花”“龙眼树”形成呼应,共同构建起南方校园的诗性意象。“撤了湖水/相思桥即将漫步于草原”的想象,打破了物理空间的局限,让具体景观升华为精神的漂泊,而草原又不免让人想到离之不远的荒原;“抹不去一袭绿衣/日月在互相嘲笑中更迭/走了的,迟早还会来”,则在自然轮回中寄托了对时光流转的坦然与对重逢的期许,为相思湖的自然景致注入了历史的厚重,使“喝茶、聊天”的日常场景与“柔暖的样子/我们是幸福的”的哲学叩问形成张力,让相思湖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成为承载生命困惑与精神“荒原”的救赎之地。这两组诗歌的意象系统与色彩运用极具匠心。“三角梅”的姹紫嫣红与“雪”的洁白形成对照,“深冬”的寒凉与“阳光”的温暖构成体感差异性,而“古石板如蛇爬行”的动态描写,则让人在四季无冬的岭南感受到几丝发自内心深处的寒意。这种意象建构延续了《盛开的土豆花》中“奥斯维辛的春天是热的”的技巧,以“白色”“粉红”到“黑色”的递进暗示美好与毁灭,在和园与相思湖的景致中,则以色彩的碰撞与融合,展现青春的绚烂与成长的沉重。
迁徙中的地域传承与诗性觉醒
地域迁徙与诗学传承在诗集中形成了鲜明的对话关系。2018年在哈尔滨诞生的《行走的瓦片》,与如今在南宁出版的《灯花与荒原》构成诗人创作轨迹的重要节点。如果说“瓦片”象征着诗人在北疆的精神扎根,那么“灯花”与“荒原”则暗含着他在南疆的生命觉醒,在陌生的地域语境中寻找生命与诗意的平衡。
在这个诗意渐趋稀薄的时代,《灯花与荒原》精练的语言囊括丰沛情感,以大胆想象营造亦真亦幻的氛围,既实现了诗人“神思独运”的创作理想,更证明了诗歌承载历史重量与哲学深度的可能。当我们翻动书页,总能被那些丰富的意象和直击灵魂的语句打动,那些回荡在和园榕树与相思湖碧水间的低语,也总会无声地滋养心灵的荒原。
《灯花与荒原》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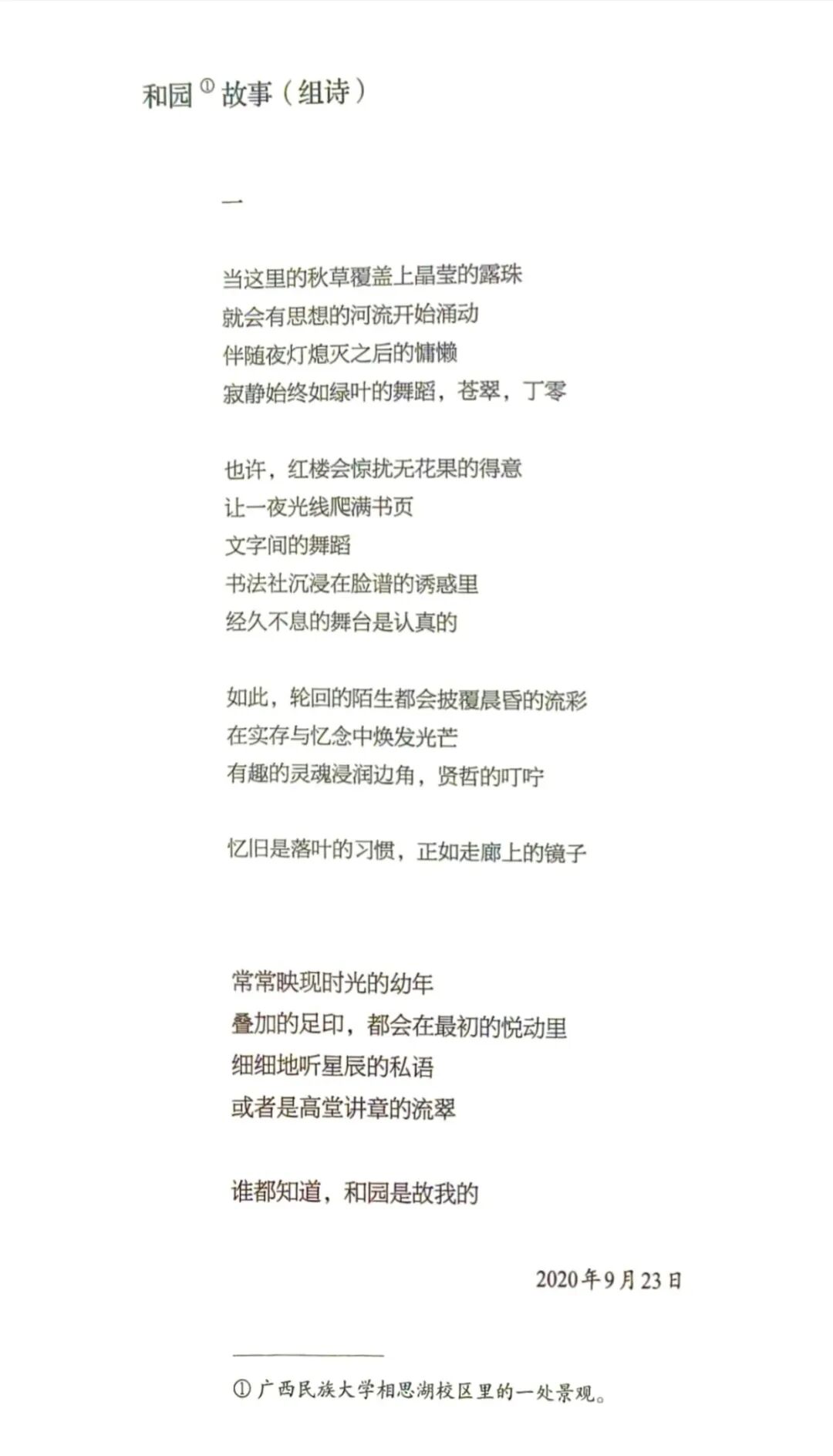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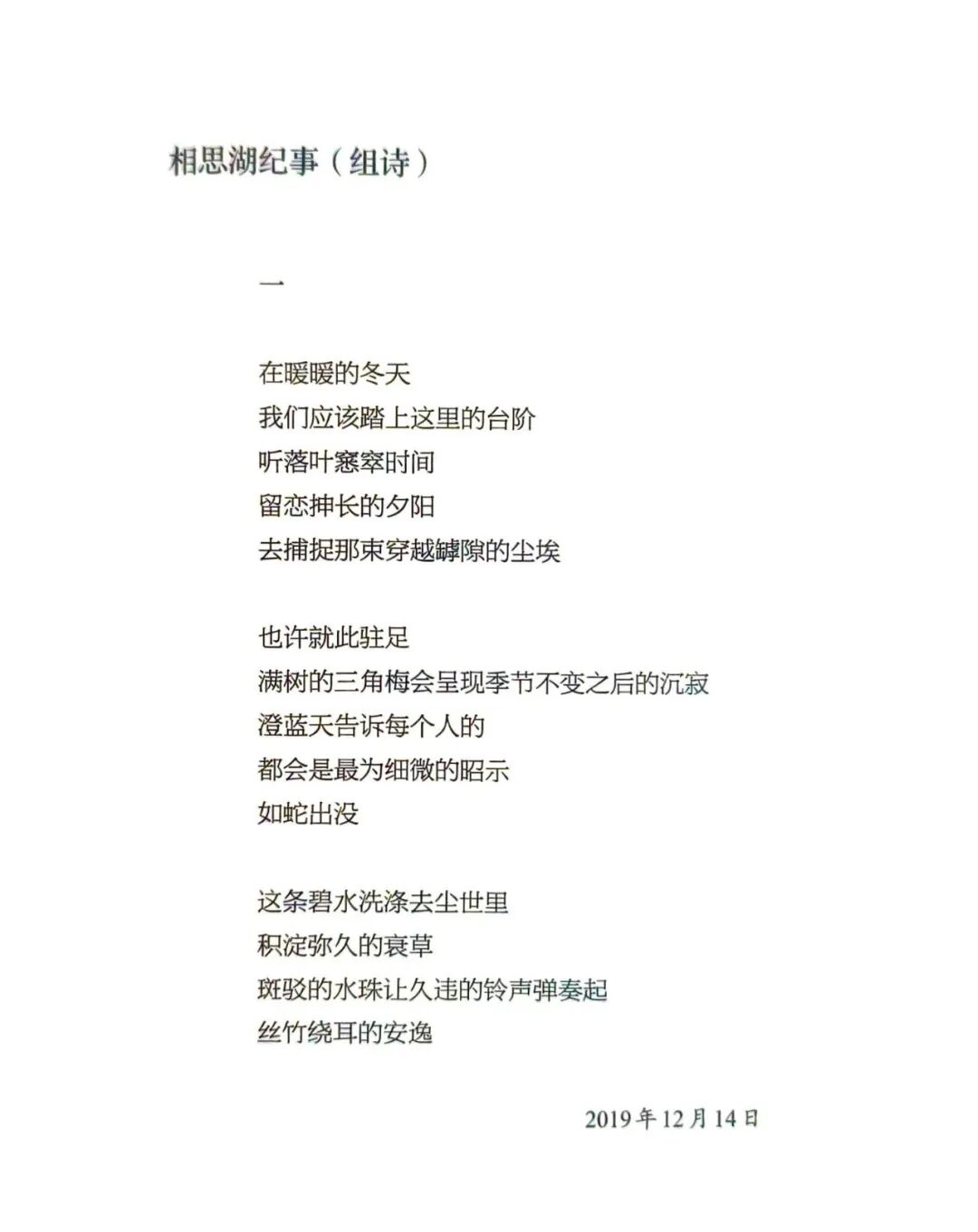
责编:周听听
一审:周听听
二审:蒋茜
三审:周韬
来源:湖南文联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