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联 2024-02-04 17:35:31

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建设的审美回望与理性探索——论王跃文长篇小说《家山》
文丨夏义生姚乐旗
继中篇小说《漫水》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后,作家王跃文再次深情回望家乡,推出了最新力作——长篇小说《家山》。该部作品于202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甫一问世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评论家李敬泽认为《家山》重返时间深处和历史深处的时候,也一定包含着对这个时代新的关切、新的认识角度、新的眼光。[1]的确,在“话语讲述的年代”,《家山》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大事件为时空背景,显然属于一部历史小说;但是,我们绝不可轻视作家“讲述话语的年代”,王跃文用“酝酿30年,构思10年,写作5年”[2]来概述《家山》的写作过程及其所凝聚的心血,而小说从构思写作到最终出版,也正是国家大力倡导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时段,很明显它又是新时代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的现代化视野来考量沙湾村的历史文本。此外,从文学出版的角度而言,《家山》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中第一批入选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侧面显示了《家山》与新时代乡村振兴主题相契合。因此,本文从“乡土现代性”的研究视角出发,考察《家山》中的“乡村建设”书写,深入剖析小说对中国现代历史上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史诗性呈现背后,所表征出的对此举措隐含的中国经验的归纳、总结和反思,继而发掘出王跃文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的探赜与理性思辨。
一、历史叙事:传统乡土社会的变革与重建
近代以来,乡土世界作为自然村舍的传统存在形态和自为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主动或被动地纳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遭遇着不断的变动和重组。[3]伴随中华民族的苦难、乡村经济破坏的日益加重和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觉醒、在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时代使命感召下,他们日渐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和主动改造乡村社会的必要性,以救济乡村、建设乡村、复兴乡村为目标,前赴后继地投入到乡村建设中去。从1904年的“翟城实验”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为代表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再到革命根据地建设、土地改革运动,近现代的中国乡村经历了深刻变革,也累积了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建设经验。虽然有学者论析了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思潮与当时乡土文学书写范型之间的联系[4],但在“启蒙”与“革命”双重变奏的社会思潮影响下,除解放区文学以外,在现代文学史上,真正有较大反响且直接反映20世纪上半叶乡村建设活动的乡土小说寥寥无几。而如叶圣陶的《倪焕之》、柔石的《二月》和师陀的《果园城记》等即使涉及此内容,但也都带有浓厚的沉郁基调。当代小说中虽在各个时期都有及时回应同时期的乡村建设活动,如8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古船》,90年代的《分享艰难》《年前年后》《九月还乡》,新世纪以来的《湖光山色》《麦河》《金谷银山》等,但受言说语境的影响,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历史叙事也鲜少正面表现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而主要聚焦于“革命”“战争”“苦难”“家族”等主题。
可以说,《家山》是百年文学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观照中国现代历史上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力作。王跃文为准确还原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历经的现代性变迁,搜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方志,钻研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基层管理制度、水利、教育等,还多次深入田野,实地走访勘察。他在《家山》中,既以大量的历史细节记录了时代革命潮汐对沙湾村陈旧而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改造,也描叙了现代知识分子在西方工业文明影响下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乡村重建愿望。
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是“皇权—绅权”并轨的“双轨政治”,即上层有中央政府,下层有以士绅阶层作为管事的自治团体[5],乡绅阶层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是乡村社会的核心力量。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超稳定的传统乡村秩序结构发生突变,乡村的话事权出现了转移。《家山》巧妙地以沙湾村农民协会兴起的改变映射和概括了乡村治理格局的变化。“沙湾是很赶时兴的,宣统元年就办过农会,为头的是扬高的老爹远达”[6],此时的农会是清政府效法西方,为发展农业而成立的,由士绅阶层主导,但“宣统皇帝搞的农会后来成了造他自己反的人”[7]。在大革命时期,扬高被推选为农会委员,这一时期的农会则为维系国民革命政府基层政治服务。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使远逸、远达和佑德公等乡绅退出乡村政治的舞台中心,他们作为旧辈所捍卫的世代相承、习以为常的“老规款”也逐渐被破除。佑德公说:“沙湾农会只办了两件事,就是准许妇女进祠堂烧香拜祖宗,还说不准女子包尖尖脚。”[8]作为国民革命政府的基层组织,农会还承担着改造习惯势力、宣传新思想的任务。在“桃香打官司”的故事中,沙湾村和舒家坪因宗族械斗酿成惨案,桃香担心丈夫被抵命而走进祠堂开会,后被八抬大轿抬进县政府打官司。“乡约老爷”桃香能有如此机会和待遇也侧面说明了国民革命运动对沙湾村沉疴痼疾的冲决。但乡下积重难返的包脚观念,虽上有政策明令禁止,下有像贞一一样的“新青年”奋力宣传女子包脚的危害,仍收效甚微。于是县长派农会召集放脚女子代表,在大街上开“洗脚会”,才革除沙湾村的包脚陋习。王跃文通过农会这一中介性角色勾勒出围绕在沙湾村周围的各方力量,绘制了一幅生动的沙湾全景图,清晰地展现了沙湾村在时代裹挟下的历史性蜕变,同时也显示了现代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向传统乡土社会的深入以及乡村宗法权威的式微。
在20世纪初变法维新的时代变革中,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学兴起,女性获得受教育权,读书人有了留学海外的机会。知识阶层“学而优则仕”的直接且明确的前途被阻断,迈入“告别士绅传统、寻找新的空间和新的身份、由此探索全新的知识分子道路的历程”[9]。新式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难,发出启蒙的“呐喊”,并积极利用所学投身到“自强”“求富”的救国之路中去。《家山》里的新式知识分子不仅在推动民众接受新思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以不畏艰难的实干精神致力于乡村建设。小说中的沙湾村受儒家文化浸淫颇深,有着“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时代大潮的影响下,旧式乡绅虽然对新学异常陌生,但在对子女接受新式教育上却并不十分古板。邵夫、贞一、齐峰等都曾在新式学堂读书,扬甫、扬圪、扬卿三兄弟还曾留学海外,他们勇担时代大任,或在政府当差、或加入革命、或救死扶伤……而其中人生选择最为特殊的要数扬卿。他曾在东洋学习水利专业,但因哥哥们都在外地,所以学成归来后,只好在家侍奉父母。而当乡村建设需要他时,他毫不犹豫发挥所学,在县长李明达的鼓励下,致力设计、建造红花溪水库。扬卿常竹杖芒鞋,躬身在山间田野测量数据,呕心沥血绘制地形图和制定水库建造方案,并且淡泊名利,不拿县政府一个铜毫子。最终,红花溪水库在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社会动乱等艰难条件下顺利建成,使多个村寨的万余亩田地能够自流灌溉,变为良田。小说中扬卿这一人物既有新式知识分子开阔的胸襟、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乡村的才干,还闪烁着散淡洒脱的名士风范,在品性修养和行事作风上,与王跃文擅写的理想知识分子官员形象谱系交相辉映,体现了其“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国人的精神滋养”[10]的诗学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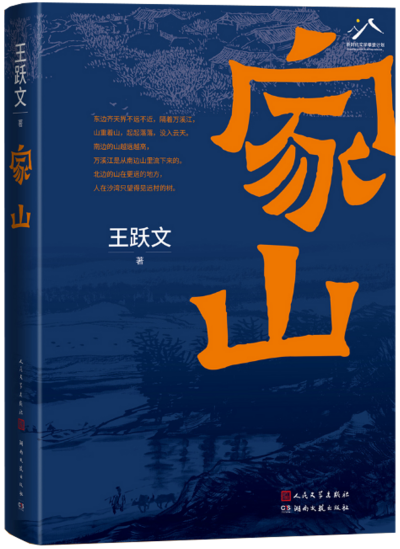
除了殚精竭虑为建造红花溪水库奔走,扬卿还联合邵夫、齐峰在沙湾村废私塾、立新学。在他们看来,科举制度废除后,已无设立私塾的必要,在沙湾村开办新式学堂是顺应时势的应有之义。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已意识到“踹了古家的薄子”和“救救孩子”的重要性,“救亡图存之唯一方法惟有灌入儿童脑筋俾适于现代新国民之修养”[11],倡导新式教育不单是为了变革陈腐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最终目的是启发乡民理性的觉醒,帮助其脱离愚昧人生,构建现代人格。这是乡村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更是身处深重灾难的民族出路之所在。在扬卿、齐峰和外来的史瑞萍等教师的努力下,从私塾单一的国学教学改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现代式教学,推动了沙湾村民众精神的改造,培养了如朱克文、修岳、有信等一批具有现代价值理念、能够切实推动沙湾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人”。在乡村教育方面,沙湾村或许受到当时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不仅有别开生面的义务教育,还开展过平民教育和国防教育。但是教识字的成人夜校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月,虽然国防教育由具有爱国意识的军官邵夫亲自动员开展,组织过军事训练,但等打仗真正需要征兵时,沙湾村立刻陷入混乱,不少村民想方设法推诿,怕自己或孩子上前线。这两项教育的无疾而终与事倍功半表明了价值观念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同时也说明新式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在中国军阀割据的基本国情下、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变局中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无论是新式知识分子利用现代知识改造水利发展农业、发展乡村学校教育的成功,还是开展理想主义式的平民夜校和国防教育的失败,这些都是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在具体实践中所累积的宝贵经验。
二、知识分子立场:对民国乡村建设破产的反省与批判
王跃文凭借鞭辟入里的历史眼光和知识分子立场,通过沙湾村的乡村建设映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验,这种经验形态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还包括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历程中的一切特殊经历。[12]新式知识分子热烈而赤诚地探索乡村发展的出路,显现了中华民族在兵连祸结的乱世之中同心御敌、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但是,总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基本宣告了民国时期沙湾村乡村建设的破产。
在对民国乡村建设破产的反省与批判中,王跃文显然接续了现代以来乡土小说的书写传统。一方面,《家山》继承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师的乡土批判书写,对沙湾村乡村建设的失败进行了沦肌浃髓的全方位总结,对“上不体恤,下不健全。佐治牴牾,胥吏刁顽。乡绅土劣,民众愚蛮”[13]的社会现状予以深切剖析,严厉批判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愚昧落后,冷峻深沉地痛斥农民的不觉悟,对民族的“根性”文化进行了透彻反省;但是,王跃文区别于“鲁迅传统”之处在于以知识分子的启蒙视角“俯视”乡村的同时,能够平等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清晰的自省意识反向思考新式知识分子对农民阶级核心利益诉求的忽略。另一方面,《家山》又继承了以茅盾、丁玲、周立波、赵树理、柳青等立足政治意识形态的乡土“史诗”书写传统,批判国民政府的专横跋扈和腐败无能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幼稚病”,从而揭示出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逻辑。在对历史趋势的表现中,王跃文跳出了“主题先行”而致小说内容“失真”的窠臼,没有按照出身、贫富、身份等给人物打上固化的“标签”,而是从合乎历史逻辑和人性的角度建构人物,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也没有进行脸谱化甚至妖魔化的刻画。王跃文之所以能够很好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地扬弃百年来乡土小说的书写陋习,得益于他一直坚守的“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文学必须对现实和历史问题作出思考,文学必须担负起社会责任”[14]的文学观念。
正如康德所言:“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15]《家山》承“五四”新文学之精神,以启蒙视角深刻洞察了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戕害人性的“吃人”面目和对现代文明的拒斥。现代文明在沙湾村如此难以扎根生长,既表露了封建势力的强大,也反映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在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中,《家山》主要通过沙湾村屡禁不止的包脚陋习来反映对女性的迫害。虽然清政府就曾下令禁止女子包脚,但是民间尤其是乡村,女子包脚的风气到辛亥革命胜利后都仍未刹住。“乡约老爷”桃香尽管敢于突破“老规款”进祠堂开会,并发挥自己“四六八句”的语言优势赢得官司,但封建礼教腐朽落后的观念已寄植于她的灵魂深处,她不仅常常对自己的一双大脚感到羞耻和痛恨,还强迫女儿月桂包脚,造成了女儿的脚残疾,也间接导致了女儿的婚姻悲剧和出家。在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中,小说开篇就以沙湾村和舒家坪的宗族械斗揭露了宗法制度的残忍和愚昧。小说中扬高这一人物集中体现了小农意识的自私、狭隘。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作为沙湾村农会的执行委员,扬高身上并没有多少现代意识,落后的宗族观念十分强烈。他在家族利益前罔顾是非,带头参与宗族械斗,担心“文武双全”的朱家超过陈家,反对朱克文回乡任教,战时征兵想方设法不让陈家子弟上前线打仗。辛亥革命以后,现代民主政治并没有彻底解放旧中国,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仍作为重要的生存标尺作用于乡村社会,这既是辛亥革命的失败,也是民国乡村建设的失败。
《家山》赓续“五四”新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主题,表现了在封建思想观念长期浸染下农民的麻木、愚昧和短视等劣根性,力透纸背地探讨了传统乡土社会小农经济所致使的农村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乡村土地私有制的根源性因素。对于封建统治的被推翻、民主政体的建立和新式知识分子不遗余力的启蒙,多数沙湾村民众不以为然,乡村社会基础板结固化。这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年累月地鲜少与外界沟通联系的小生产者已很难剪断千百年来小农意识的脐带,他们对社会民主变革十分麻木。青天白日旗已在城里挂了十几年,他们总是把“总统”喊作“皇帝”,把“县政府”喊作“县衙门”,对女子包脚禁令置若罔闻,最后是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观念恐吓下、怕在大庭广众之中被县长洗脚才不敢再包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包脚给女性带来的束缚和残害。除了对现代文明态度上的冷漠,这些愚昧、短视的农民也没有“自新”意识,他们接受、衡量变革和行事的准则是从实利主义出发,如放公听说新政府不招武举人,气得掰断梭镖把子、在屋里骂娘,悔不该领头组织农会,朱达望也认为“农会又不发油米,又不发光洋”[16]。在看不到教识字的夜校和参军有短期的实际利益回报时,沙湾村民众立马退学,并想方设法地逃兵役。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村长陈修根本应是一意修道成仙、无心于俗世的道士,但是他最大的爱好和人生追求却是存光洋、铜钱和置地。王跃文可谓把传统中国农民的劣根性和封建观念的顽固性刻画得入木三分。但是《家山》对农民的批判并不是单向度的,它也切中要害地体察到了新式知识分子及国民政府所倡导的启蒙和乡村建设与底层农民之间的“双向隔膜”,一方面是愚昧落后的沙湾村农民对立足于改造“乡”的现代性变革的不认同,另一方面则是新式知识分子及国民政府对他们之于“土”,即对质朴合理的生产生活需求的忽视。所以,朱达望会认为没有切实改善他们生活的农会没什么用;本为纾困宽农的“赋从租出”新税收政策,在佑德公看来减租不减赋是缺乏乡村生活经验的幼稚“书呆子”才想出来的。这种“双向隔膜”引发的错位对话,可以说是民国乡村建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看到了推翻千百年来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对农民阶级的压迫是农民真正获得解放的物质前提。
总体来说,新式知识分子和国民政府自上而下的启蒙和乡村建设,既没有正确把握国情,看到走改良主义道路是注定要失败的,也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参与其中,其所提出的乡村重建方案更没有充分地把农民的核心利益放在首位。相反,国家权力向乡村的不断渗入,使乡村社会的自治传统遭受破坏,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这些历史教训无疑也是20世纪上半叶乡村现代化建设“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山》鲜活地表现了国民政府“猛于虎”的苛政,通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历史逻辑阐释了国民政府为何倾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能建立的原因。一方面,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如县团防局长马宗仁为害一方,他怕强盗抢劫,把家中的金银细软足足装了18个铁桶沉入池塘,后来打捞时见少一个铁桶,就怀疑诬陷在他家池塘边卖油糍粑的马老三,把马老三折磨致死。更为荒唐的是,马宗仁引起公愤被杀后,又吸鸦片又赌博的马朝云接任了县团防局长;县政府推行“赋从租出”的新税收政策,本意想要减轻佃户的生存压力,但是大量的赋税被直接摊派到田主身上,乡绅们的利益被触犯,于是遭到乡绅阶层的联合抵制;沙湾村战时征壮丁,乐输委员向远丰对扬高表示只要贿赂他两万法币就可以免去修岳的兵役。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专横残暴,视民众如草芥。如历任县长多数都把“铲共”作为县政府第一要务,国民党不仅杀害共产党人,还要株连亲属。沙湾村“红属”不得不躲到凉水界避难,没来得及躲的直接被放火烧死;国民党军队不把壮丁当人、生活苛刻,五疤子受不了逃回沙湾村;红花溪水库修好后,百姓负担已经很重,县政府还要开征水利附捐。而中国共产党则一心为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用佑德公两箩筐炭,给他一块光洋,还给抗日家属发优待证。国民党罄竹难书的罪恶,也使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越来越得民心。国民党军官邵夫转投共产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产党员齐峰在沙湾村振臂一呼,组织成立自卫队。无道的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我们从民国乡村历史巨变中可以找到其深刻的历史逻辑。
三、当下视角: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理性思辨与寻路
学者谭桂林指出:“《家山》所写30年世变,其中之开阖曲微、人情世态,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的乡土想象。虽然作者一再声称写的就是自己的家山,但作者对所写的沙湾生活,既没有沈从文式的亲历,也没有周立波式的亲为……归根到底不过是作者自我的一部心灵史。”[17]《家山》以史料钩沉和现实原型为基础的文学想象,“及物性”和“现场感”俱足,从它对中国现代历史上传统乡土社会变革与重建的史诗性书写,以及它对民国乡村建设破产擘肌分理的反省与批判中,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着王跃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火种和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来推动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观。
《家山》的超越之处就在于,它继承乡土批判和乡土“史诗”书写传统,基于“民族志”叙事,对中国现代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围绕在传统乡土社会各方力量的评价只是小说的一条明线,小说的暗线则是通过探讨乡村建设的得失成败,特别是“乡贤”和“民间”不可忽视的价值,总结中国现代历史上乡村建设的中国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展开理性思辨与寻路。在《家山》的主体故事之外,还流淌着一条贯穿文本始终的“潜流”。《家山》赓续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对农耕文明追忆、留恋的乡土小说书写范型,致力于发掘沙湾村的风景美、风俗美和风情美,通过探讨“乡贤”和“民间”这二者不可忽视的社会价值,从多元现代性的视野出发,肯定优秀的传统乡贤文化和乡村素朴美德,以及异彩纷呈的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对西方中心主义所倡导的现代化方案的补充、纠偏和反拨,表达了对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以西方现代化为仿效对象的现代性焦虑,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的出路、乡村社会如何实现“诗意栖居”的探赜,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乡村建设“中国经验”的重要内容。
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说:“现代性的历程,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18]不同国情、不同文化的差异性、特殊性决定了现代化道路必然存在多种模式和多样的可能性。虽然,自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伊始,中国就走上了探索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但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统摄下,中国乡土文化的“在地性”特质被贬抑和排斥,频频遭遇各种势力的质询,逐渐沦为西方文明的他者。而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在城镇化的召唤下,“向城求生”的打工潮使乡村人口大量地涌向城镇,乡村“田土撂荒”“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十分突出;另一方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文化对乡村文明产生严重冲击。由是,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显著的城乡差距、物质上的脱贫和精神上的滑坡、自然生态的退化,亟需以中国式现代化来破解百余年来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困境。
王跃文清醒地批判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愚昧、落后和狭隘,但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家山》里的佑德公是沙湾村有口皆碑的乡贤,他不仅威望高,而且美名远扬。历届新上任的县长都要登门拜访他,为了政策能够顺利推行,还要打上他的旗号。他坚守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人生信条,通晓人情事理,陈、舒两家宗族械斗惨案发生后,他主动从中调和;他崇德向善,乐捐好施,允许村民到自家山上砍柴,收养孤儿有喜,资助他成家立业;他接受新思想,送女儿贞一上新式学校;他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沙湾村筹办农会、新式学堂时主动出钱出力,支持邵夫、贞一及其丈夫驰骋抗日战场;他组织沙湾村“红属”去凉水界避难、带头资助抗日军人家属被村民喊作“活菩萨”。逸公也是沙湾村受人敬重的乡贤。他是清末举人,做知县时廉洁奉公,体恤乡民;他是典型的旧式知识分子,却能宽容接纳时代的先声,送三个儿子留学东洋;他为避免堂兄弟反目成仇,慷慨送半幢窨子屋给达公;他临终时正值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其“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言也着实令人动容。扬卿则是新乡贤的代表,虽然有些孤傲,常闭关在家中阁楼,但当乡村建设需要时,他积极利用所学的水利知识建造红花溪水库,在沙湾村开办新式学堂。《家山》没有延续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对旧乡绅负面脸谱化的书写,也有意打破新旧势力绝对区隔冲突的叙事模式,真实地还原传统乡村的文明形态,通过两代乡贤对沙湾村乡村建设的代际传承,揭示出乡贤文化对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乡贤文化之所以在乡村建设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中国乡村的“熟人社会”特征及其由此积淀的乡村文化传统、血缘亲情文化和乡村醇厚素朴道德力量的支撑。乡村社会以传统乡土文化和血缘亲情为纽带而成为有机整体,是乡贤们维系乡情、反哺乡亲的精神原动力。在现代乡土社会的“样本”沙湾村,尽管村里有“红属”,但是村民之间并没有互相举报、构陷;在面临国民党“剿共”和1947年万溪江水灾时,沙湾村村民在佑德公等乡贤的带领下同心同德、共度时艰。这也极强地印证了传统的乡贤文化和乡村醇厚素朴的道德对乡村治理的积极效用,揭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民族奥秘,显露了王跃文“从民间、从草根寻求中国传统道德的火种”[19],来抵御外来不良文化腐蚀乡村社会的企望。
近代乡土小说作家对“风景的发现”,使文学中作为陌生化的审美客体而存在的人情风物不再只是调节叙事节奏、烘托叙事氛围的“闲笔”和“情语”的陪衬,进而演化成一种可以能动地表达现代思想的叙事装置。通过再现故乡具有“土气息泥滋味”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作家们纷纷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精神原乡”,或传递现代文明理念、或隐现漂泊的乡愁、或张扬乡土文化的异质性魅力、或无奈喟叹家园的失落……《家山》中极具湖湘地域色彩的“风景”描写,既是用静水流深的日常生活叙事来平衡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叙事,舒缓小说叙事节奏的重要表现形式,又张扬着王跃文醉心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意识,散发着他离乡后文化寻根与生命寻根的冲动,承载着他浓郁的乡土情结和乡愁乡恋情绪;它还作为一种独立的话语场域,寄寓着王跃文对现代社会科学崇拜的理性思辨与担忧,对感性状态下的乡土世界的主动赋魅和赏爱,充满了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在民间”的浪漫瞩望。
《家山》的开篇就是一段对洋溢着生机盎然、宁静悠远的田园情调的自然风景和乡俗的描写:沙湾村四面环山,西边是青青的豹子岭,各种野物山上尽有;东边是齐天界,重峦叠嶂,没入云天;万溪江的水从南边的山上流下;北边的山在更远的地方,人在沙湾只望得见远村的树。[20]也正因溆浦多山的地貌,古时便是偏居一隅的蛮荒之地,生存条件较恶劣,所以沙湾村也形成了“尚武”的彪悍民风,武举考试未废除前年轻男子多会打功。《家山》详细叙述了沙湾村奇趣多元、斑斓多姿的民俗事相。如在农业民俗上,沙湾村每年舞龙灯,祈求风调雨顺;食俗上,沙湾村坐落于湘西,喜食腊肉、糍粑、辣椒等,整个正月村民们都要在桌子中央摆一碗木雕的鱼;在民俗信仰上,村上的老樟树、五云寺黑水公公都是沙湾村民众崇拜的神灵;在婚姻仪礼上,沙湾村以公鸡代替未能亲自到场成亲的新郎官,还有摇花轿、哭嫁等婚俗;在民间艺术上,沙湾村每逢春节必连天上演辰河高腔目连戏;而在民间语言上,如闷子(谜语)、抬阿娘(娶亲)、揸火(烤火)等方言多半也是古语,既富有乡土气息又形象有趣。在科学主义的扩张和霸权下,这些新鲜活泼、意味深远的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常被打上“落后”的烙印,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们被指认为是不符合现代文明规范,需要被剔除、改造,甚至加以批判的内容。王跃文以逸公之口,表达了对“科学”迷信的质疑:“你们讲的德先生、赛先生都是好先生。但是,人过日子不要凡事都问科学。舞龙灯就没有虫灾,公公从小就不相信。但是,过年舞龙灯热热闹闹的,又有什么不好呢?你们不是很喜欢吗?”[21]王跃文作为“60后”作家,完整经历了当代中国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巨变。他知晓乡村要发展,必须对现代文明敞开怀抱,但他反对以“科学”之名,大肆否定、打压、排挤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自在的生存空间。他理解到乡村除了以农业生产承担社会分工外,还承担着乡村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功能,如果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来改造中国乡村,则会造成中国乡土文化根脉断裂的严重后果。
梁漱溟曾说过:“所谓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22]《家山》的深邃之处在于它不仅讲述了中国现代乡村建设的历史故事,而且从当下视角出发,站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上,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所鼓吹的一元现代性及其科学崇拜思潮下的工具理性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否定和破坏,以高度的文化自信重新审视传统乡贤文化和乡村醇厚的道德力量,以及地方文化、民间文化对于涵育文明乡风、构筑乡村共同体和永续乡土文化活力等的巨大价值,丰富和扩殖了现代性的内涵。小说对中国现代历史上乡村巨变的历史描摹和现代化的“自反性”思考,以及对中国现代历史上乡村建设“中国经验”的总结,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这一议题上形成深度契合的对话关系,构成了《家山》的复调叙事结构。
四、结语
《家山》将时代风云际会寓于寻常百姓的日常烟火中,含蓄蕴藉、舒缓有致地以沙湾村小小一隅讲述了20世纪上半叶传统乡土社会波谲云诡的现代性变迁,展现了在近代“科学”“民主”的时代跫音下,平凡的新式知识分子昂扬奋发的实干精神和之于家乡、之于国家、之于民族的拳拳之心;也以冷峻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反思民国乡村建设的沉重缓滞和民心渐失;特别是从沙湾村的历史巨变中国民党的失败教训和共产党的成功经验里归纳、总结出乡村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验”:乡村与国家是一体两面,没有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平的社会环境、清廉的政府及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绝不会有乡村的现代化;不废除乡村土地私有制这个根本制度,租佃关系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就是一个死结,小农思想意识就无法根除,永远不会有乡村的现代化;现代科学教育是乡村培育新人才、形塑新观念、以科技推动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活性因子如“乡贤文化”“民间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建设的根脉。只有正确把握中国经验,中国乡村才有可能步入健康的现代化之路。
从微观层面而言,《家山》是王跃文乡土叙事的双重转向,即从官场叙事转向乡土写作、从田园牧歌转向乡村的重大议题,这是他写作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从中观层面而言,《家山》以鲜有作家言及的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乡村建设为表现对象,综合继承并创新运用百年来乡土小说的三种传统的叙事范型,取得了不凡的艺术成就,是乡土文学史上又一重要收获;从宏观层面而言,王跃文对多元现代性的思考和对中国现代乡村建设的探赜,无疑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有着极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所以,《家山》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顺应时代大势,认清时代主题,紧跟时代步伐,承担时代使命”[23],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为人类现代文明贡献中国方案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攀登高峰之作。
[1]参见何晨:《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王跃文最新长篇小说〈家山〉面世》,《文艺报》2023年1月11日,第4版。
[2]张艾宁、李晶:《王跃文谈〈家山〉创作:十年打磨,日日掩泣》,《出版人》2023年第2期,第36页。
[3]参见姚乐旗、彭文忠:《21世纪乡村小说创业书写的叙事模式》,《云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第168页。
[4]参见黄健:《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思潮与乡土文学书写范型》,《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9年第1期,第2页。
[5]参见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8页。
[6]王跃文:《家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1页。
[7]同上,第7页。
[8]王跃文:《家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73页。
[9]袁红涛、王光东:《“教育”小说与知识阶层的现代转型——以〈倪焕之〉为中心》,《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第87页。
[10]王跃文:《梅溪湖答客问》,《王跃文文学回忆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0页。
[11]王跃文:《家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256页。
[12]参见李培林:《“中国经验”的内涵和基本要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1月10日,第3版。
[13]王跃文:《家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92页。
[14]王跃文:《现实主义文学的困窘》,《人民政协报》2012年8月27日,转引自龙永干:《王跃文和他的世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64页。
[15][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4页。
[16]王跃文:《家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5页。
[17]谭桂林:《百年变局中的民心之向——评〈家山〉中乡土想象与历史叙事的诗学重构》,《中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第205页。
[18][以]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4页。
[19]王跃文:《梅溪湖答客问》,《王跃文文学回忆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0页。
[20]参见王跃文:《家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页。
[21]王跃文:《家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344页。
[2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23]夏义生:《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时代性论述的思考》,《文艺论坛》2022年第4期,第5页。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26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夏义生姚乐旗单位: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暨南大学文学院
来源丨《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总第100期)
责编:周听听
一审:周听听
二审:张马良
三审:熊佳斌
来源:湖南文联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