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联 2024-01-02 16:18: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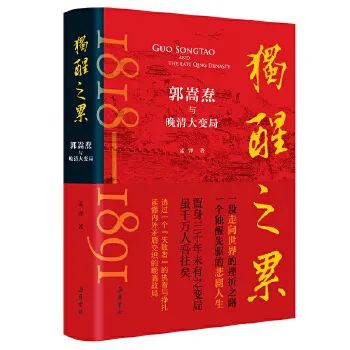
独醒是最大的孤独——从孟泽长篇传记《独醒之累》看郭嵩焘的人生悲剧
文丨贺有德
知名学者孟泽著《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可谓用心用情用功,既厚重——洋洋洒洒几十万字,深度解读伟大而孤独的郭嵩焘与分崩离析的晚清大变局;也沉重——先知先觉的郭嵩焘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孤独而痛苦一生,让后人扼腕长叹!
“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屈原的内心独白,道出了多少苏轼式“满肚子不合时宜”的孤独、寂寞、痛苦与无奈!从战国直到晚清,如三闾大夫屈原报国无门功业落空者不乏其人,身陷晚清大变局的郭嵩焘,绝对称得上“同是天涯沦落人”中的“佼佼者”!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悲剧总是在历史的天空如星光闪烁,让后来者痛惜,让后来者警醒。
郭嵩焘何许人也?这位生于湖南湘阴长于晚清末世的洋务先知、首位大使、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至今鲜为人知。不妨拂去历史的尘埃,翻开郭氏的人生履历,浮光掠影式扫描:1818年生于富家,求学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义结金兰,极有抱负,“笑谈都与圣贤邻”;后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府,著有《绥边征实》;1847年中进士,与曾国藩、罗泽南一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56年奉命赴上海,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见识西方文明;离开上海返京任翰林,入值南书房,皇命参赞主持天津海防的僧格林沁,认为“必与言战,终无了期”;作为钦差稽查山东沿海厘税遭算计受处分,仍回南书房;告假还乡,京城失陷;同治登基,得李鸿章倚重,郭氏复出,先后任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1866年,因左宗棠纠参,解职还乡;1874年,朝廷诏命赴京,任福建按察使;1876年,前往英国,就任驻英公使,兼任驻法公使,在此期间发回总理衙门刊印《使西纪程》,结果招惹祸端;1879年,因副手刘锡鸿算计,黯然离任;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接连发生,郭氏“不忍不谈洋务”,希望国人从“天朝上国”迷梦中觉醒,愿望成空;1891年在长沙病逝。
郭嵩焘的人生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生不逢时,晚清动荡,闭关锁国,盲目自大,不接受西方文明,也是个人悲剧——概而言之,因其四大意识:超前意识、自我意识、情感意识和忧患意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无法调和,更兼秉性不改,不知变通,注定是悲剧人物,个人焦灼痛苦,也使后人扼腕痛惜,最终以一个伟大的孤独者和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落幕……
郭嵩焘的超前意识,在那样的时代是极为可贵的,却也是极为可悲的,“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之故也。世人麻木,盲目自大,当时的晚清王朝如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密不透风,众人昏睡。一直以来,魏源被誉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有人如此评价林则徐——其实,真正当之无愧的,还是郭嵩焘;与郭氏相比,魏源也好,林则徐也好,可谓小巫见大巫,其广度与深度皆远不能及!
晚清分崩离析,郭氏先知先觉,远超时代。其一,关于洋人。郭氏认为洋人可“以理格之”“以礼通之”,纵然视之“夷狄”也“非有划然中外之分也”,且“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完全颠覆了时人多年“始则视之如犬羊”“终又怖之如鬼神”的传统认知。其二,关于商人。郭氏认为商人与士人平等。古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又有“无商不奸”之说,而郭氏认可商人,认可商业,这在当时无异于“异端邪说”。且郭氏认为“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但在当时显然难得认可。其三,关于“本末”。“政教工商”的“本末”,郭氏认为“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自效其诚”,“公之众庶”的政治是西洋立国之本,由此出发,教育学术,世道人心,自然改观,而工商繁荣,也水到渠成。其四,关于中国问题。郭氏直言“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而“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如刘蓉所言:“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英雄所见略同。这对当时昏庸腐朽透顶的晚清政府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可惜晚清举国“昏顽”,病入膏肓,无可救药,郭氏之说,自然如风过耳……
与其超前意识相承的是郭氏的自我意识。虽然“聪明反被聪明误”,但对自我的认知,也是先知先觉。郭氏自知得罪了身边的世界,但珍惜自己一辈子的经验与见识,遂将“乡里士大夫群据以为罪言”编成一书,名曰《罪言存略》,赠送至交,以翼“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又作《戏书小像》两首云:“傲慢疏慷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写尽骄傲与自信,写尽苦闷与悲凉。“百代千龄”后,我们终于重新审视郭嵩焘,这位胸怀与眼界远超时代的伟大的先行者,也是伟大的孤独者,自知之明超越时空!不仅如此,郭氏曾官至二品,对于百年之后朝廷按例当“赐谥立传”之事,也是颇具先见之明,在其《自叙》中自云“自分不敢希翼”——果然,去世之后,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赐谥立传”,未得恩准:“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此处“颇滋物议”之“所著书籍”正是之前所述《使西纪程》……
郭嵩焘的情感意识,正如孟泽在《后记》中所言:“人为情使,道由情生。”纵观郭氏一生,于家国天下,一往情深:怀抱多才,以身许国,兼具以天下为己任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志在“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无奈“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知其不可而为之,奈何与“今世周旋”“枘凿不相入”,“不能屈而相从”,注定一生虽豪迈而悲壮,“负独醒之累”,百折不挠,却始终困顿、挣扎、狼狈、沉屈……情感意识是把“双刃剑”,初为情所使,后为情所困,终为情所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留下不尽的孤独与伤痛……
与其情感意识相承的是郭嵩焘的忧患意识。郭氏对西方文明与中国问题的体察,远比同时代人深远,远没有同时代人乐观。“晚年参天地,观世局”,深感大清朝举国“昏顽”,忠奸不辨,强弱不分,用人不当,乃至“颠倒失次”,昏庸无道,导致人心不古,不仁不义,“上有酿乱之有司,下有应劫之百姓,乱至无日矣”,感慨“回首人间忧患长”……身处乱世,郭氏心中雪亮,预言走出秦汉以来“流极败坏”的诸多弊端,我们差不多需要三百年:三五十年或能“望见其涯略”,再以百年树人“涤荡旧染”,再以百年改变世道人心……忧患意识伴随终生,助其孤独,助其痛苦。
郭嵩焘的“四大意识”,致其一生深陷孤独、苦闷、愤懑,虽孤傲而无奈,壮志未酬,宏图未展,抱恨终生……在中国式的成王败寇标准面前,被视为失败者——其实,此标准不足以衡量所有人,还得从个人性情与时代潮流辩证看待。不妨这样假设:郭嵩焘生活的时代不是晚清,而是大唐或两宋,结局将会如何?不妨二次假设:晚清政府重用郭嵩焘,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明,结局又将如何?不妨再次假设:郭嵩焘知变通,少孤傲,不致“枘凿不相入”,不致报国无门,得偿所愿,结局又将如何?毫无疑问,个人命运必将重写,不再孤独而痛苦;晚清历史必将重写,再次出现“中兴”!可惜历史不允许假设,假设无法照进现实,悲剧不可避免……事实上,即使在腐朽的晚清,李鸿章对郭嵩焘很欣赏很信任,被视为粗人的曾国荃也为郭嵩焘抱不平,给予过那个时代最高的评价。百年之后,钟叔河先生称郭嵩焘为末世士大夫阶层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称郭嵩焘为那个时代“最勇于挽澜之人”,可惜因其“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而其“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最终结局无法更改。但不得不说:“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此论可谓入木三分,再恰当不过了。
郭嵩焘人生跌宕起伏,郭嵩焘的命运既离不开时代,也离不开个性,弄潮儿成孤独者,独醒之累,万世之叹!
责编:周听听
一审:周听听
二审:张马良
三审:熊佳斌
来源:湖南文联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