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南客户端 2016-04-26 12:2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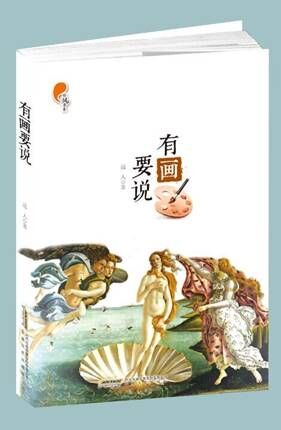
《有画要说》
远人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6年3月第一版
【《有画要说》选章】
《有画要说》自序:有意思的事
童年始,有至少十年时间孜孜学画,那时的最大愿望是长大后当个画家。自转而习文起,当画家的念头就断了,但没妨碍我继续喜欢读画,尤其西方绘画。购藏的百余本画册总耗去我很多阅读时间,逐渐便有了写关于绘画书的想法。
落笔后并不容易。如果按照那些画家的生平流派来写,难免变成资料堆砌,于是我选择了对单幅画的揣摩。当然不是揣摩那些画家的技法,而是从那些画中体会其他,譬如那个画家为什么要画这幅画?是什么触动他的构思?他又想通过这幅画传达些什么?除了我们看见的,还有没有隐藏的?当然不仅仅我会这么看:一个堪称伟大的画家已经是个思想家了,只是这个思想家不是用文字来表述思想。他选择绘画来表达,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手段。因此从画中读出一些思想或想法,才不算辜负画家们的劳作。“我要重新使绘画为精神服务。”杜尚这句话已经表明,他要画的根本就不是随随便便一幅画。涂鸦很容易,但精神不是靠涂鸦就能轻易出来。
既然有精神存在,那些画就肯定不会单纯。对非绘画专业的读者来说,能从其他的角度发现画中的意思,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事。因此在写的过程中,我不断告诉自己,别去管那些流派,别去管那些技法,你需要的是发现其中的表达,或者说,那些画中有什么触动了你,你就把那些触动写下来。
书的写作跨度三年有余,这是不短的过程,也是很享受、很有意思的过程,我没想到这些画会调动很多连我自己也没意识过的一些想法。从这点来说,写作也就是写自己的想法,如果连自己的想法都没有,写作也会变成很没意思的事。如果读者喜欢其中一些文字,那我得承认,是那些画太触动人的想法。
完成后的整理费了不少工夫。因随机面对画家,也就随机写下文字。作为一本随笔集,编排很重要,我没按写作顺序编排,在修订过程中,我选择了按画家出生年代来排。这么做的目的,是暗自希望读者在一幅幅画的翻阅中,能够感受西方绘画的一些变化轨迹,这未尝不是又一件有意思的事。
唤起历史的激情

【法】大卫《贺拉斯兄弟的誓言》(1784年)
唐朝诗人李贺在《南园》组诗中写下雄视千载的豪迈之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读这些猎猎飞扬之句,仿佛一个慷慨豪侠的时代便在眼前虎虎生风。
当然,以剑扶正气、文荡浊流的尚武之气又岂止唐朝才有?历史的种种激流不仅冲刷东方,西方历史同样如此。当我们面对亚瑟王的时代、面对斯巴达王的时代、面对亨利四世的时代、面对狮心王查理的时代、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总是无数男人的疆场热血成为全球历史的谱写之笔。他们或者流芳千古,或者寂寂无名,毕竟,“一将功成万骨枯”是永不改变的战争法则。关键是,那些走上疆场的男人们是否都能做到热血的澎湃和灵魂的激昂。
战争来临,永远是对男人的考验来临。
在一个国王都能被民众推上断头台的法国大革命时代,我们能够想象,雅各宾党人在当时唤起多少人的激情热血。堪称新古典主义巨匠的画家大卫(1748—1825)像所有人一样,投身这一历史洪流。只不过,大卫的武器依凭既不是剑,也不是文,毕其一生,大卫始终摆动手中画笔,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雄烈之气面对时代。在其笔下,《拿破仑的加冕礼》《波拿巴将军翻越圣伯纳山》《萨宾的妇女》,尤其完成即不朽的《马拉之死》等等,无不表现这位画家是如何将大革命政治与艺术进行完美结合的。
那幅堪称代表作的《贺拉斯兄弟的誓言》更无法不令人想起李贺的千古名诗。
该画背景取材于古罗马时期,当罗马人与邻近的伊特鲁里亚人发生战争之际,老贺拉斯让三个儿子奔赴沙场。临行前,父亲将三把宝剑交给儿子。画面上,老贺拉斯一手举剑,一手举在剑旁。三个全副武装的儿子并排而立,同时向剑伸出手臂,起誓要为国效命,不凯旋而归就马革裹尸。画面的庄严和人物的刚强充分显示了作为男人的三个儿子将如何沙场杀敌。在画面右边,几个女人极为柔弱地相互闭目垂首,但明显的是,她们知道这场告别前的誓言不属于她们,只属于这些堪称男人的贺拉斯兄弟。因而画面的张力也就此到达极致,令人在震动之余,又不禁感到慷慨中的悲凉。
正是在这些历史英雄主义中糅入人性的点滴,使这幅画不仅在法国赢得巨大声誉,在意大利也获得非凡成功,乃至当时罗马的老画家巴脱尼将自己的画板也送给大卫,并告诉他说,“只有我们两人才是画家,其他人都可以丢到河里去。”
生逢乱世,对多数人都是不幸。对大卫而言,却有幸目睹巴士底狱的攻占和路易十六的覆亡,有幸目睹拿破仑的加冕和溃败,有幸目睹吉伦特派与雅各宾党的权力争斗。乱世无情,历史却强健有力。大卫虽只是画家,却在历史的激荡中让自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正如李贺的诗歌能唤起时人的热血一样,大卫的张张画面也同样在唤起历史的激情。历史若无激情,则难以成为历史。历史的激情源于历史的理想。没有哪种理想会缺乏激情。大卫的个人激情和理想同样就在这些画面上映现。
从贺拉斯兄弟起誓的时刻里,我们能够看到,是否成为历史人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男人首先得成为一个男人。当马拉遇刺之后,公民希罗在翌日的国民公会会议中呼喊,“大卫,你在哪里?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报仇。要让敌人看到马拉被刺的情景发抖,这是人民的要求。”大卫的声音立刻在人群里响起,“好!我一定要画!”
这是时代听到的大卫的誓言。它像贺拉斯兄弟的誓言一样,每个字都撞痛历史的耳膜。
馈赠的记忆之树

【法】柯罗《孟特芳丹的回忆》(1865—1870年)
人似乎总是被时间中的规律支配。正如宋人蒋捷所填的那首《虞美人·听雨》,只寥寥五十六字,就将少年、壮年和老年听雨时的心绪描写得淋漓尽致。雨始终是雨,但随着听雨人的年龄改变,听雨的心情和感受就截然不同。对画家也是如此,少年时看风景和壮年老年时看风景,眼光不一样,心情也会不一样。只是,蒋捷的主题是人世的悲欢离合,而法国风景画大师柯罗(1796—1875)描绘的则是对人生的记忆。
人在老年当然会被记忆充满。关键是,人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记忆。柯罗的一生在风景中度过,其画布上的呈现也是一幅一幅风景。或许,热爱风景的人总是会比其他人要多上一份温柔,因为风景表现的核心质素是美。少年时看见的美仅仅是单纯的美,所以柯罗画下《娜妮桥的风景》等单纯的风景;壮年看见的美是叠合人生经历的美,所以柯罗会画下《小牧羊人》《塞纳河的女神》《西兰尼》等一些充满知识性和人生感悟性的风景。到晚年,画家几乎就沉浸在个人的回忆当中。作为漫游过欧洲诸国的画家,一生的回忆都涌入画家内心。只是,对柯罗来说,他的回忆不像东方文人墨客那样易于感时伤世,而是让那些回忆尽可能在心中涌动出人生中的深度美好。或许,也只有到达晚年的艺术家,才能真正分辨出人生中的种种滋味,也才能自然而又有意识地将所要表达的东西留给后人。
在柯罗的晚年画中,一系列注明为“回忆”的画作无不令人感到画家本人在对风景的描绘中,同时也渗透了人生所给予的种种心灵进入。人要进入某种事物,当然不是想进入就能进入。进入事物需要能力,而能力恰恰是时间才能给予。晚年的柯罗不仅是技艺上炉火纯青,对人与事的感受也达到智慧的境地。人的聪明与身俱来,智慧则一定随时间而来。当我们面对柯罗的那些回忆之作,诸如《意大利的回忆》《艿蜜湖景的回忆》《那不勒斯湖畔的回忆》《地中海岸的回忆》《明月的回忆》《丽华湖景的回忆》《亚维瑞城的回忆》《科布伦的回忆》《二轮马车,蒙勒兹附近的玛克西的回忆》等等,都能看到画家将所有的人生智慧置于画中。
尤其那幅六十八岁完成的《孟特芳丹的回忆》,更将柯罗带到毕生的艺术巅峰。
画面主体是一株巨大的老树。粗壮的树身向左倾斜,好像是风将它吹成那样。一根根树枝也弯曲有力地依附在树身之上。繁密的树叶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在大树左边,同样有株挺拔的高树,只是树身还瘦,树叶零零星星。在这株树下,一个穿橙色长裙的女人举起双手,好像要从树身上摘下树叶。有两个孩子和她聚在一起。她们也许就是她的孩子。因为是春天,她带着孩子来到树林。地上长满清新的草。处处给人生机。
如果不知道柯罗画下这幅画的年龄,我也许只会单纯地欣赏而不会感到惊讶。因为到达晚年的柯罗在告诉我们人生中最值得挽留和美好的部分。无数同样堪称大师的人在晚年给出的作品往往会充满惆怅和悲情、遗憾和感伤,但柯罗没有。在他的画笔下,仍然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似乎柯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他对人生的决无遗憾。无遗憾的人会对生活充满感激、感动和感谢。在柯罗这幅画中,我们的确能抚摸到这种感激、感动和感谢。或许,唯有对晚年的人生充满如此情感的人,才是对人生和自己最感到满意的人。一个人在晚年仍对人生不满意,那就未免将自己局限在狭窄的方寸之地。柯罗用充满生机的画面在告诉我们人生应有什么样的晚年体悟。从这幅画中我们的确能体会,柯罗在时间的流逝中终于走向了智慧。唯有智慧的人才会在最后不觉得人生遗憾,也唯有智慧的人,才会在最后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样的人生,幸福也好、悲伤也好,经过过多少悲欢离合也好,都是人生给予的馈赠。
接受馈赠而又将馈赠交给后人,只能说明柯罗内心在晚年的开阔。
那也恰恰是一个大师必然具备的开阔。
日常的才是本质的

【法】塞尚《桌布、水壶和高脚盘》(1893—1894年)
在现代派画家里面,塞尚(1839—1906)给我的感觉十分独特。他既不像他的前辈席里柯那样关注重大社会题材,也不像稍后的毕加索那样,追求风格的繁复多变。面对塞尚的画,我们差不多就是面对极为简单的日常物。
就日常这个词来说,既不诗意,也不引人注目。
但如果说艺术包罗万象,那么日常肯定会有日常的丰富一面和日常的自足一面。
塞尚关注的也就是这些丰富自足的日常。譬如他的《桌布、水壶和高脚盘》,不过是一张普普通通的桌子,桌子上有一块来不及铺平的台布,台布上面都是一些水果,那些水果基本上就是苹果、梨子、桃子、橘子等等。在这些水果旁边,更是任何一个家庭都备有的水壶。在另外的画中,除了这些之外,塞尚也无非就加上一些瓶子、茶杯、糖罐、篮子……有时他就把水果放在那个篮子里。
在今天,不论对普通美术爱好者来说,还是对各个地方美术学院的学生来说,静物写生几乎是他们起步时就需要训练的基本功。既然是基本功,也就意味它不过是走向真正目的的一个桥梁或者起点。塞尚名震全球的作品居然就是这些看似基本功的画作。其中当然有塞尚绘画的独特之处,但我更看重他表达的主题。
人总是对重大主题有不由自主的关注,就像一个最普通的人也喜欢去谈论国家大事一样,但不论他谈论得多么精妙,并不能就因此让自己变成一个能左右局势之人。普通人的世界都深陷日常——过平平淡淡的日子,走平平淡淡的道路。太平淡的不太被人注意,但恰恰在不被注意的日常里,我们将度过平平淡淡的一生。
塞尚从来不给人震撼,但他却给人说不出的亲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需要的其实也包括亲切。不仅是对人的方式,也包括对物的方式。在我们的习惯用语中,“人物”已经单纯地指向人了,但这其实是应该拆开的词语。这词语包括“人”和“物”。说它变得单一和习惯,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已将人与物的关系合而为一,甚至不会去想其中的差别。
但想不想是一回事,真不真又是另一回事了。
无论在谁的生活中,谁都希望发现真实、面对真实、获得真实、给予真实。但做到却着实很难。因为真实既可以说是最表面的,也可以说是最深处的。表面的不一定就能沉到深处去,深处的也不一定能浮到表面上来。很简单地说,真实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其实也就像我们的生活,总是在旁人和自我的悖论中冲突。
人都想从悖论中走出。但往往却又难以知道,走出悖论的方式,其实只需要直接面对事物最本质的方面。从本质中发现人,从本质中发现物。之所以要去发现,就在于这些本质常常处在被遮蔽的位置。导致遮蔽的东西很多,这其中既有人的自以为是,也有人发明的种种习俗和人所创造的各种知识。人创造这些,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我们的确在认识这个世界,但认识却又恰恰遮蔽了世界的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或许才是最本质的一面。因为它是不需要用习俗和知识去解释的一面。
就像塞尚的这些静物,从来不需要解释,但他却从这些不需要解释的物体中,让我们看见事物最本质的一面。撇开那些绘画技艺,我们可以说,塞尚的画平淡,但决不能说,他的画不给人最基本的启示。
星空里的激情

【荷兰】梵·高《星夜》(1889年)
在梵·高(1853—1890)一系列名闻遐迩的画作中,没哪幅画比《星夜》更让我感到内心震撼了。
整个画面以蓝色为基调,绝大部分空间被两条龙一样迎面绞合的庞大星群占据。右上方,斑斑点点的金黄色泽围住耀眼的月亮。另外还有几处星团散布,它们像缩小的月亮,更像地球之外的行星,令人夺目地旋转。在画面左边的黄金分割线位置上,一株由墨绿和深褐色弯曲线条组成的柏树呈火焰状腾空而起。画面的右下端,散布着一个微型教堂和零星的房屋,它们像是即将被身后巨浪样起伏的蓝色群山吞没。
那些天生为艺术而诞生的艺术家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他们的作品,我们就不可能想象这样的艺术存在。就像星星,在我们视线中只永远呈现宁静和安详。它们各自闪动,互不干扰。但到梵·高笔下,星群却首尾相连,变成巨大而浑浊的旋转体,像一股控制不住的激情在恣意纵横。
仅仅用变形还解释不了梵·高的艺术。更何况,梵·高的画也说不上是抽象之作。他画下的也差不多就是他看见的。不同的是,他面对他想画下的题材时,将自己的激情赋予了要画下的对象,或者反过来说,他所看见的事物本身唤起了他内心不为人见的巨大激情。面对《星夜》,甚至面对梵·高的全部作品,都令人感到,梵·高的激情几乎就是人类所能到达极限的激情。
没有谁不曾凝望星空。那些遥远的星光不单纯只给人美的享受,更唤起我们内心的联翩浮想——在人类无论哪种文明当中,都有来自星空的神话,都有来自星座的传说。可以说,在整个大自然中,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星空更能唤起人内心的最深欲望了。
内心的欲望有多强烈,人的激情也就有多强烈。
梵·高毫不遮掩地说出过自己对创作的欲望激情,“为了它,我宁愿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即使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也在所不惜……”这句话之所以令人惊骇,就在于它是人能够做到、却罕有人去实践的选择行为。
主动地抛弃理智,只可能服从最强烈的激情。
在梵·高的画笔之下,无处不是激情——通过《向日葵》,我们看到色彩的激情;通过《吃土豆的农人》,我们看到悲伤的激情;通过《乌鸦飞过麦田》,我们看到死亡的激情……而在《星夜》中,梵·高为我们展现出生命的激情。
也许可以说,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人是有激情的生命体。对任何人来说,激情都毫不陌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少年期和青春期,都或多或少地体验过、激动过。但没有勇气,我们就很难将这股原始而充沛的情感延续。特别是人受缚于物质、受缚于享乐的今天,激情的行为朝向了和激情本质无关的目的。“这一个将要扼杀另一个。”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借克洛德之口说出的这一神秘之言,未尝就不是在说人的理智将扼杀人的激情。在今天,扼杀变成了现实,激情也变成了今天的幸存之物和稀罕之物。
人越来越关注脚尖,当然也就不会再关注星空。但不去关注,不意味人的激情就真的在灵魂中永远缺席。至少,热爱梵·高的人,其实就是在热爱一种激情。当梵·高的作品在今天被标出天价出售之际,抛开那些商业运作,里面是不是也包涵人对生命和激情的最终肯定?
天才是有想法的人

【法】修拉《星期日午后的大碗岛》(1886年)
艺术史上的许多天才多半短命。随手可以找出很多例证,比如法国画家修拉(1859—1891),在三十一岁就因一场扁桃腺炎骤然去世。修拉的家人措手不及,修拉的朋友和敌人措手不及,整个当时的欧洲画坛也措手不及。
措手不及就离开人世,就如修拉在二十多岁就令画坛措手不及地感到震惊一样。似乎修拉的存在就是为了令人措手不及。但对修拉自己来说,年纪轻轻就名震巴黎却觉得没什么了不起。这也是天才的一个表现,无数天才都不会觉得自己的成功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在他们看来,自己只不过牛刀小试了一下而已。成功对普通人很难,对天才很容易,所以在天才眼里,成功只是手到擒来的一件平常之物。
但即便手到擒来,也在于天才总是有一些和旁人不一样的想法。世上有想法的人很多,但将想法付诸实施的人却少。很多人只是想一想,然后就丢开了。天才却喜欢将想法变成实际行动,然后表现在世人面前。我们或许承认,一个人有了想法,前提多半是这个想法还没有被他人尝试。如果被他人尝试过,也就不能叫想法了。所以有想法其实很难,有真正的想法更难。左右想法的,往往是对陌生的好奇驱使。所以,天才的出现令人觉得陌生,是因为天才的想法陌生,陌生得前所未见,因而也陌生得令人惊讶。
修拉虽然在安格尔学生亨利·勒曼门下老老实实地学过一些绘画基础。但对天才而言,有个基础差不多就够了。从这里还能看到,如果不是修拉,我们在今天很可能不知道安格尔这个学生的名字,他画过些什么几乎没人见过。这也就说明,名师往往可怕,会束缚住学生的很多想法。修拉的学生生涯只有一年,大概是他在学习基础时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但修拉的老师崇敬自己的老师,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有想法也会自行掐灭。不知是不是不大瞧得起这位老师,总之在修拉的画面上,看不出和祖师安格尔有什么瓜葛。
安格尔自成大器,毕生“为艺术而艺术”,终其一生,也的确为后世竖立起自己的标杆。但天才不大相信标杆,所以修拉转过身拨弄自己的想法去了。修拉拨弄的想法是用小笔触在画布上点出色点,看修拉画画的人,难免会看得极不耐烦。谁又数过修拉一幅画上究竟点了多少个色点呢?估计下决心的人数不到一半,就会咬牙切齿地放弃。但对修拉来说,这是他的想法,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就在于天才喜欢沉浸在自己的想法深处,旁人怎么看,和天才自己是没关系的。所以修拉整日关在画室,不厌其烦地将那些色点点上画布。
在画布上点上色点就是天才吗?当然不能简单这么说,问题是修拉点上色点时,着实带了很多自己的想法,至少,他的很多精力没用在观摩同行的画上。对绘画的天才而言,绘画没什么神秘。修拉兴致勃勃地研究了很多科学理论,然后得出那些理论对想法的指导。这就不一样了。天才不是整天睡觉就可以成为天才的。前面说了,天才是有想法的人。天才的想法往往指东打西,给旁人的感觉还可能南辕北辙,但天才自己知道,那些想法需要些什么支撑。现在应该明白,天才表面上横空出世,其实不那么简单。该付出的还是得付出,关键只在于,天才的那个想法和别人都不一样。为什么很多人放弃想法,大约也是知道,将想法变成现实,中间还是有距离,或者说,中间会有受不了的东西。
修拉忍受了别人受不了的,所以他成为了修拉。从绘画史来看,在修拉之前,有哪个画家拥有他的那些想法呢?一个也没有,所以,修拉走的路是别人没走过的路,所以,修拉有了很多终生不渝的朋友,也有了很多终生不渝的敌人。
修拉死得意外,死得简单,也可以说,他死得很天才。如果他活着,还会有更高的成就吗?这就难说了,因为即使是天才,也很难有第二个震惊世界的想法。修拉的想法已经完成,所以,对天才的死,没必要过多惋惜。至于修拉的画,因为不多,我们都已经看到,就省略对它们的描写了。
在阻挡的父亲手臂

【奥匈帝国】席勒《双人像—内贝施父子》(1913年)
在任何时候看见维也纳这个名字,都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伟大的艺术,仿佛维也纳就是艺术的另一个名字。出生于维也纳近郊的埃贡·席勒(1890—1918)早早就注定是这个城市天才的代表。在其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中,以令人惊心动魄的画面留下他所在时代的激变身影。
席勒所在的时代正是全欧开始动荡的时代。当时统治欧洲最大版图的奥匈帝国已经有了七百多年历史,伴随种族冲突而来的不安全感和虚无感在二十世纪初年成为全欧面对的社会现实。似乎总是这样,社会越动荡,艺术就越得到表现的空间。尤其绘画领域,肖像画不再流行,画家们的画笔几乎都伸向表现时代悲剧气氛的宏大场景。唯独德语国家保持了肖像画传统,但这些肖像也不再是雍容华贵的上流人物,而是往往表现出冷漠与自嘲。在席勒从未放弃过的肖像画中,充满的就是这一自我嘲讽和人与人的疏离,结果导致席勒将画笔转向令人惊骇的性的领域,似乎在阴霾笼罩的时代,唯有性,才能让人掩耳盗铃地得到释放。
但决不是因为性的表现,才使年纪轻轻的席勒受到画坛重视,恰恰在他的表现中,隐喻了一个时代的失落。在1909年,刚过二十岁的席勒就受到当时维也纳画坛执牛耳的画家克里姆特邀请,参加其主持的第二次分离派艺术展。席勒的作品虽然没怎么受到注意,但却奠定了他在画坛的位置,乃至克里姆特逝世之后,年轻的席勒便成为维也纳画坛炙手可热的代表性人物。
面对绘画,席勒当然踌躇满志,但面对时代,席勒又以一个艺术家的超常敏感刻画出悲剧性的气氛。在其笔下,除展示性区的画外,喻示死亡的画也在不断出现,其人物的眼神总是被惊恐充满。但席勒的悲观并未局限在这两个领域。譬如,完成于1913年的《双人像——贝内施父子》就独树一帜地表现了席勒对时代的理解。
画中的贝内施是席勒的赞助商,画中的儿子奥图刚刚十七岁。贝内施父亲背对画面,伸臂在儿子面前。奥图的眼神是席勒画中难得一见的清澈和单纯。他双手交握,似乎不理解父亲的阻挡行为。对十七岁的少年来说,渴望进入外面的广阔生活,但父亲却在阻止。为什么阻止?或许,这就是席勒对时代最深刻的把握体现。因为外面的生活不再是歌舞升平,尽管画中贝内施眼神冰冷,却是斜视而出地朝向外面。阻挡儿子出去,无疑是他对生活已有最深的体会和了解。席勒画下的阻挡,可以解释成父亲的权威,但未尝不能解释成父亲对儿子的保护欲望。他不希望儿子过早地踏入动荡不安的社会。这幅看起来简单的双人像,在没有任何背景的画面上取得令人震惊的效果。没有背景,因为时代就是背景。贝内施父子的动作已经表现了时代给人的惊恐和不安。这是席勒那个年龄不可想象的表现力体现。
但没人阻挡过席勒。席勒的父亲在他十五岁时便已去世。因此对席勒来说,在他少年时期便踏入了外面、踏入了社会。尽管依靠不可一世的天才在画坛取得成功,但外面毕竟是外面,外面的一切冷暖都被席勒早早品尝。在完成这幅画的翌年,动荡不已的欧洲终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应征入伍的席勒没上战场,但面对了时代最惨烈的一面。而更惨烈的现实也终于发生在席勒身上。怀孕待产的妻子在1918年10月感染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去世,仅过三天,席勒感染同样的病毒去世。当然不止席勒夫妇,这场无可阻拦的疾病肆虐全欧,也传染到奥匈帝国的五脏六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永远在历史中消失。被贝内施父亲阻拦儿子出去的外面,不仅再是动荡,而是那个帝国和时代的土崩瓦解。对席勒而言,太想有一条这样的手臂将他阻挡在命运之外。但命运将其塑造为天才,也就塑造了命运自身对他的妒忌。所以天才总是流星,短暂得令人惋惜,又强烈得令人耀眼生花。

【后记】
写作这本书时,我总不时会想起美国诗人梅利尔的一个观点。在他看来,作家永远嫉妒画家,因为作家需要借助语言来支撑对观看的表达,而画家则直接将看见的表现出来。这句话给我体会很深。在写作中,我总是感觉语言不够将画家们的所见所思完整地表达,遑论解读。
我的目的不是解读。令我诧异的是,在国内好几个媒体的专栏发表中,总有读者将它们看成画评。但在我看来,很少有人能够得上画评家,因为画作本身,已经达到了完整。评论一幅画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我选择了站在画外,站在画家们的生平之外来直接面对作品。这让我心里多少不那么发虚,因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套用之,有一千个读者也就有一千种看画的眼光。我只不过如实写下我的读画感受。
这是一部随笔集,不是一部评论集,我要强调的仅此而已。
书将付梓之际,由衷感谢为这些文字开设专栏和提供发表版面的报刊,感谢王晓笛先生在出版过程中的无私付出,感谢小虫女士不辞辛劳,在图片上提供的帮助,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对书稿的接受,尤要感谢责任编辑岑杰先生,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其宽容和一丝不苟的作风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人与人之间总有缘分,书与出版也会基于缘分。缘分是用来珍惜的,就像一个作家永远会珍惜自己的文字,一个画家永远会珍惜自己的思想一样。任何一本书,都的确需要在作者与出版者共同的珍惜中交给读者。
远 人
2015年4月29日
【推荐语】
在诗人的心灵世界中,诗与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有着特殊的连接通道,因此诗人体验和品悟艺术的角度与路径常常异于他人。诗人以心之诚挚、情之深挚、心眼之独到、思绪之诗性,常常能领略和洞察到艺术的无穷韵致与幽深底蕴,结晶为新颖而鲜美的艺术奇异之果。远人这部堪称艺术探幽的《有画要说》便是明证。
——龚旭东(著名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
远人谈画的文字,既避免了标准艺术史方式的墨守成规,又避免了常规艺术欣赏上的模糊含混。它们不是单纯对画意的语言诠释,而是对等的爱与创造性的反应。远人清新的眼光和语言,复活乃至再造了绘画的微妙气氛、色彩与力量,并凭此互动,深入对存在于创造奥妙的考察。
——马永波(著名诗人、翻译家、文艺学博士后)
作为研精覃思、博考经籍的思想型作家,当远人遇到哪些画作之时,一再回复到他的诗人本性,以纯粹而富足的文字,放开诸般官能,却简到极致,不事雕琢,就那么任性而直接地呈现给你。
——田耳(著名小说家、鲁迅文学奖得主)
远人,1970年代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7岁发表处女作,有诗歌、小说、评论、散文等500余件作品散见于《大家》《钟山》《随笔》《花城》《山花》《芙蓉》《诗刊》《星星》《文艺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青年文学》《书屋》《博览群书》等海内外20余家报刊及数十种年度最佳选本。出版有长篇小说《伤害》《秘道》,散文集《河床上的大地》《真实与戏拟》《新疆纪行》,艺术随笔集《怎样读一幅画》,诗集《你交给我一个远方》等,主编出版《21世纪的中国诗歌》《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在多家媒体开有专栏。
责编:李婷婷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