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双石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5-10-11 09:4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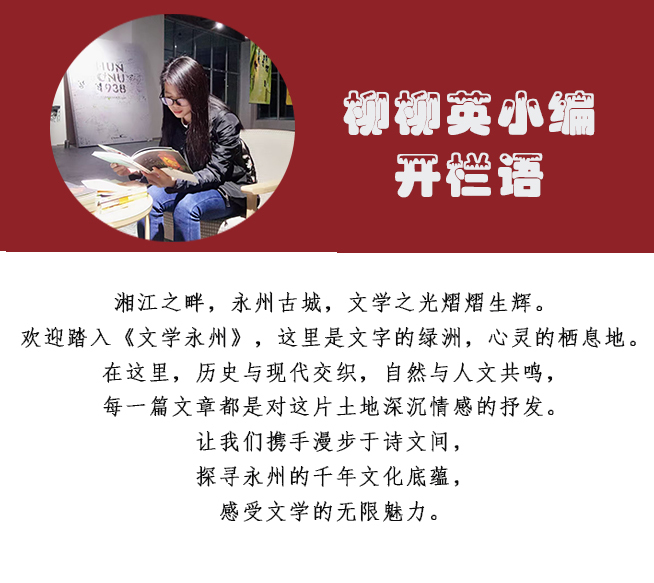
黄阳司:青春记忆中的山河
■魏双石
这大约是人到中年后特有的心境了罢——总在某些恍惚的刹那,被一阵无由的风,或一声遥远的鸣响,轻易地拽回一个地名里去。那地名,在岁月的深潭里沉埋已久,本以为早已苔藓遍布,形同化石了;不料它竟鲜活如初,只消一念,便粼粼地荡开波光,将一整幅青葱的画卷,哗啦啦地铺展在眼前。那画卷的名字,便叫黄阳司。

一九九二年的九月,我们这群来自四乡八野的“尖子生”,像一滴滴兀自跳跃的山泉,从易家桥、高溪市、阳山观那些被田埂与炊烟包裹的乡中心小学,汇入了黄阳司区中学这条宽阔的河流。我们的解放鞋上,还沾着故乡的泥土,眼神里怯生生地装着对“区中”这个“大世界”的全部憧憬。与我们一同构成这河流的,还有另一股水流——黄阳司氮肥厂、冶炼厂的子弟。他们脚上是洁白的运动鞋,嘴里吐露着略带傲气的“官话”。于是,乡野的质朴与厂矿的规整,泥土的芬芳与工业区特有的氨水气味,便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猝不及防地碰撞、交融,奏响了我们青春的开场锣鼓。

若论那三年里最富生命律动的景象,绝非课堂上的琅琅书声,而是每周六上午准时上演的“胜利大逃亡”。最后一节课的铃声,是比任何号令都更催人心魄的。老师那句“下课”的尾音,尚在粉笔灰里悬浮,我们早已如绷紧了弹簧的机括,只一瞬,便从座位上弹起,汇成一股喧嚣的、奔腾的激流,涌出教室,在校门口迅速分岔,流向各自遥远的家。
最富野性冒险的一支,奔向了那座小小的黄阳司火车站。对于家在铁路沿线的同学而言,那轰隆作响、吐着白气的货运火车,便是他们免费的、驰骋的“钢铁坐骑”。他们像灵活的猿猴,看准了车速减缓的当口,手脚并用地攀上那冰冷的、布满铆钉的铁皮车厢。风,顿时成了有形的力量,蛮横地灌满他们的衣衫,将头发吹成一面飞扬的旗帜。他们就在那“哐当—哐当—”永不停歇的、雄浑的节奏里,对着身后急速退去的田野、山丘和天空,发出毫无意义的、纯粹的呐喊。那是一种混杂着危险与自由的、令人心醉的浪漫。
另一股更为沉默却也更为坚韧的人流,则涌向了古老的湘江渡口。那江水是常年浑浊的土黄色,一条老旧木船,一个皮肤被江风与日头染成古铜色、终日里不言不语的摆渡老叟,构成了归途中最具古意,也最磨人性子的一环。船桨“吱呀—吱呀—”地摇着,不紧不慢地剖开凝滞般的水面,仿佛在切割一块厚重的黄绸。船行得慢,人心却早已像离弦的箭,飞到了对岸那绵延的群山之后。上岸,不过是另一段征途的开始。十几里的山路,要靠双脚一步步去丈量。那蜿蜒的、时而被野草淹没的小径,见证过他们雨中滑倒的泥泞,也收藏过他们歇脚时,望着满天星斗哼出的、不成调的歌。
还有一路,算是幸运儿,可以坐上那定时往返的客班轮船。虽免了风吹日晒,但马达“突突”的轰鸣震得人耳膜发麻,船舱里弥漫着汗味、机油味和江水腥气的混合气体,同样是一段需要默默捱过的、滞重的时光。至于那些氮肥厂、冶炼厂的子弟,他们则自成一体,说着我们半懂不懂的厂矿篮球赛、露天电影和俱乐部舞会,步行着回到那个有围墙的、飘着特殊工业气味的小社会里去。
如今想来,我们哪里仅仅是在上学?我们分明是在用每一种最原始也最真诚的交通方式,虔诚地穿越着山河,去奔赴一个名为“知识”与“未来”的缥缈约定。每一次周日的返校,肩上的行囊里,是沉甸甸的米和母亲亲手腌制的、咸得发苦的萝卜干;而每一次周六的归去,心里装载的,是一周的疲惫,和一份被家的灯火熨帖着的渴望。
青春的画卷,色调纵然是土黄与灰蓝为主,也总会点染上一两笔惊心动魄的绯红。谁的心里,不曾住过一个“小芳”呢?她或许就坐在前排,两根乌黑的麻花辫垂在肩上,回头问你一道复杂的几何题时,眼眸清澈得像浸在井水里的星星。她或许是那个在渡口等船时,总是独自靠在柳树下看书的厂矿女孩,白色的连衣裙角在江风的吹拂下,像一只不安分的、欲飞的蝶。你或许从未与她说过一句话,只是在窄窄的船舱里,她不经意的衣角拂过你的手背,那瞬间的触感,便能让你心头一颤,继而面红耳赤,仿佛犯了天大的过错。那份纯粹到不染尘埃的悸动,那个被钢笔反复描摹在日记本扉页的名字,是那段清贫岁月里,最奢侈、最甜蜜的宝藏。她如今在哪里呢?想必也早已被生活打磨成了另一个模样,但在记忆的渡口,她永远是那江风里白衣飘飘的侧影,是悬在旧时光里一轮永不西沉的、温柔的月亮。
我们也曾懵懂地谈古论今。在镇子边上那块刻着“唐叟钓矶”的巨石旁,我们遥想那位唐代隐士的孤高风骨,也在那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面上,分食过从食堂偷偷带出来的、一小瓣沁凉的西瓜。我们曾站在冶炼厂那高耸入云的烟囱下,一边被那巨大的阴影笼罩,一边争论着它究竟是贡献了税收,还是污染了我们头顶这一小片天空。我们也曾并排坐在火车站废弃的铁轨上,枕木间的野草搔着脚踝,我们说着遥不可及的理想,说明天,说远方,仿佛脚下这两条沉默地伸向天际的钢轨,真能忠诚地将我们带往任何想去的地方。
一九九五年的夏天,一场考试,为我们这三年的山河跋涉,画上了一个仓促的句点。我们再次像水珠一样,从黄阳司这片青春的河床溅起,四散奔流,汇入更广阔也更茫茫的人海。那些一同爬过火车、挤过渡船、走过夜路的伙伴,那些曾让你心弦微颤的名字与面容,许多都已湮没在时代的烟尘里,失了音讯。我们都成了彼此生命中的过客,却共同拥有着一个名叫“黄阳司”的精神故乡。
而今,三十年弹指而过。听闻,当年的渡口,那“吱呀”的桨声早已被马达取代,那摆渡的老叟想必也已作古;货运火车管理森严,再无人能攀上那飞驰的浪漫;客班轮船也因了公路的发达,停了许久了。我们这一代人,被时代的洪流不容分说地裹挟着,在都市的玻璃幕墙与立交桥的丛林里,拼命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安身立命。
然而,每当夜深人静,当白日的喧嚣如潮水般退去,疲惫从骨头的缝隙里丝丝渗出时,我总会闭上眼,回到那片江风里去。那湘江上混合着水汽与泥土气息的风,那火车站喷薄而出的、带着煤烟味儿的乳白蒸汽,那周六放学前震天的喧哗与奔跑的脚步声,还有心里那个永远清晰、永远美好的“小芳”的身影……它们从记忆的深处浮现,带着毛茸茸的光边。那用双脚、用木船、用火车车厢一寸寸丈量过的三年,那清苦却饱满、艰辛却闪亮的青春岁月,原来,是我此生穿越过最远的山河,也是我此后一生,取之不尽的勇气,与回甘的温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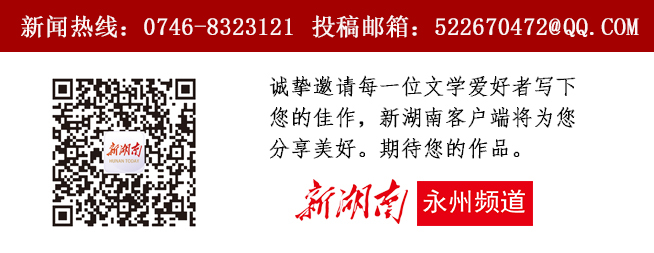
责编:黄柳英
一审:黄柳英
二审:李礼壹
三审:李寒露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