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5-10-01 15:03:04
文丨黄耀红
 易彬:《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2月第1版,6月第2次印刷
易彬:《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2月第1版,6月第2次印刷
一、多重文献里的生命复活
易彬于穆旦研究上兀兀穷年,早为今日学界所注目。《幻想的尽头:穆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以下简称《穆旦传》,并随文标注页码)问世未久,适值穆旦《赞美》中的诗句出现在全国高考语文卷的作文命题之中。穆旦这个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断被打捞、被重估的寂寞诗人,一时获得如此强大的公众关注,确实有些始料未及。不过,网上诸多热炒穆旦其人其诗的文本,并未深度进入穆旦的精神世界。相对于媒介的喧嚣,易彬的《穆旦传》以其洋洋46.5万字的皇皇巨幅,将人们带入穆旦一生的云谲波诡与苦乐悲欣。这里有穆旦作为诗人的丰富及这种丰富所孕育的痛苦。
与诸多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穆旦生命中的起伏、显隐,令人唏嘘。然而,《穆旦传》并不曾停留于历史的伤感。易彬以其驾轻就熟的文献还原、文献互证的学术路数,不断为读者打开隐秘而幽微的思想话语空间,一层一层揭示那些附着于文献之中的精神密码与历史图景,流现那些被侮辱、被扭曲的苦痛和执着。作为传记,《穆旦传》走的并非林语堂之于苏东坡的文学共情之路,它更多地属于学术型传记。
《穆旦传》里的文献,给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有五类。第一类文献是作品,即穆旦发表于不同时期的诗歌及其他作品。这些年,包括穆旦诗歌在内的发表物不断被整理和发掘,但论时间跨度之长、作品类型之丰,《穆旦传》可谓凤毛麟角,这无疑是作者爬梳整理之学术定力的见证。易彬不仅对穆旦的存世作品有其独特的分析与解读,更重要的是,他着意标出了各诗的出处,在确保版本精准的同时,更将这些作品深度植入不同的时代语境,并织入诗人个体生命的遭遇和心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献缀联着穆旦的少年与青年、家国和江山,当然也标举着他对于中国新诗建构的卓越贡献。第二类文献是书信,即穆旦在不同时期与其家人、亲友、同学的书信往返。与发表于媒体的作品不同,书信所面对的是穆旦的私人交往语境,因此,它所传达的思想、态度与情感,或许比作品更直接真实,也更自由自在。第三类文献是档案。这类文字以穆旦于特定年代里的“思想检讨”与“问题交代”为主,它们所见证的是穆旦于1950年代后的精神境遇,所有的档案文献均打上年代的烙印,也意味着体制与权力对个体的生命碾压。第四类是各类原始书报刊文献,除了众多期刊报纸之外,还有穆旦就读于南开与清华时的校刊、纪念册等稀见文献。第五类是口述文献,其中既有2002年以来易彬对穆旦相关人物的访谈,也有对《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等相关人物的口述的整合。

对《穆旦传》来说,文献是支撑文本的结构或骨架,更是文本的血肉与灵魂。可以说,文献即是穆旦生命永恒的“栖居之处”。在文献处理上,《穆旦传》并未满足于文献的丰富,易彬摒弃了史料推进的线性铺陈方式,以其居高总揽的视域,致力找寻文献间的语境呼应或事件的因果关联,从而建立起文献间的互文、互证关系。因此,文献之于传记不只是一种结构性力量,更是一种重构力量。举例来说,1929年正值穆旦进入中学,而这一年又正值民国教育部颁发新的中小学课程《暂时标准》。易彬敏感地意识到,在当时的中小学课程标准里,“用语体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成为主要目的”(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这其实是穆旦一生从事新诗创作的语文背景,它意味着“以白话文为主要形式的新兴语文教育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书报’之中所蕴含的新兴的公共知识更多地进入穆旦的视线之中”(第53页)。确实,由“文言”而“语体”的历史性转型,正是穆旦及穆旦一代选择现代新诗的时代因由。
中国文学里有着极其悠久的纪传传统。笔者联想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沈从文在读到《史记·列传》时所提及的“事功”与“有情”的关系。在沈从文眼里,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并不只看到历史的兴替与英雄的功过,而是回到个体生命与环境的体验与共情之中。“有情”之“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319页)沈从文说:“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抒情”(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6页)。这样看来,《穆旦传》作为诗人传记的终极价值亦即沈从文先生所说的“抒情考古学”价值。《穆旦传》对于研究现代新诗、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具有史与诗相交织的意义。
二、百年新诗发展中的个体建构
 穆旦1949年3月在泰国曼谷。资料图
穆旦1949年3月在泰国曼谷。资料图
在中国新诗发展与建构的百年历史中,穆旦作为个体建构的价值独一无二。这不仅表现为他天纵其才的诗歌才情,而且穆旦的一生真正称得上是中国新诗成长同行。穆旦生于1918年,当时的中国新诗正处于初生期。在他不到60年的一生里,他的生命、诗歌与时代共同编织成他的命运。二三十岁时,他亲历了山河破碎、南渡北归;政权鼎革之后,他的四五十岁又陷入风声鹤唳的政治整肃之中。穆旦的人生就像其诗句所写:“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花吹熄”(《你看》)。等他像一片落叶那样飘向“幻想的尽头”时,他又不无悲悯地意识到:“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冥想》)。
如果将穆旦的诗准确系年,那么他的诗不失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个人样本。由少年到青年,由青春到迟暮,这些诗歌以三四十年代为主,但整体上还是纵贯其坎坷一生。我们注意到,《穆旦传》中,易彬在援引和阐释穆旦诗作之时,总是有意识地将穆旦诗歌置入与卞之琳、杜运燮等同时代诗人互相比较的解诗场域,从而凸显出穆旦诗歌的个性及其现代诗学价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的穆旦,一直处于中国文学史之外。在“革命话语”取代“文学话语”、集体编写凌驾个人撰述的时代,穆旦的被忽略、被放逐、被隐没亦如他的宿命,就像沈从文、张爱玲被忽视一样,都属于单一观念滤镜下的“变形”。就穆旦而言,更有其人生履历上特殊问题。易彬说:“穆旦没有进入任何一种文学史序列,自然是受制于文学史的写作环境,也可见出其政治上的灰色以及名声的微薄。”(第460页)穆旦由隐而不彰到“惊奇重现”,其深层的力量来自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告别了“神话珠网”的时代,它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融入世界文学谱系,并且有意识地与世界进行有效对话。穆旦之于中国现代新诗的建构意义,可以作专题学术探讨。从《穆旦传》里,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在文学与政治、自我与时代的关系上,穆旦建构起属于他的独立的现代诗学观。
 穆旦戎装1942年摄于印度加尔各答。资料图
穆旦戎装1942年摄于印度加尔各答。资料图
首先,在国家与民族的重大主题上,穆旦始终反对将诗作为标语与口号,反对新诗中那些贫血的词藻,即使在战时中国,他看到的是“她在新生中的蓬勃、痛苦和欢快的激动”,是“一切呻吟,痛苦,斗争,和希望”。他甚至认为,这种不失理性的抒情,“此后新诗唯一可以凭藉的路子。”(穆旦:《他死在第二次》,香港版《大公报·文艺》第794期,1940年3月3日)《赞美》这首广为人知的诗为例。易彬认为:《赞美》“所选用的词语和意象并不是明朗型或‘赞美型’的,而基本上是与生命力的张扬相反的词语,如‘荒凉’‘坎坷’‘枯槁’‘踟蹰’‘耻辱’‘忧郁’‘干枯’‘灰色’‘饥饿’‘呻吟’‘寒冷’等;其意象更是无一例外的非歌颂型意象,如‘沙漠’‘骡子车’‘槽子船’‘茅屋’‘沼泽’等。”(第125页)确实,穆旦在《赞美》里用的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而不是庸常所说的“我们民族已经起来”或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已经起来”之类。他一直在有意回避一个空洞的“大我”,回避那个抽离了个性的“我们”。因此,他反对一切宣传鼓动式的政治抒情。用袁可嘉的话说,就是“他对祖国的赞歌,不是轻飘飘的,而是伴随着深沉的痛苦的,是‘带血’的歌。”(袁可嘉:《九叶集》“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回望上世纪三十四年代的中国,启蒙、战争、图存、救亡,它们都不是纸面上的“大词”,而是真实的生命体验。然而,这些“大词”又习惯性地将新诗引向“大我”,并随时可能淹没“小我”的独特。然而,在穆旦心里,国家、民族、人民这些概念,既带有“五四”的启蒙色彩,更关联着抗日救亡的男儿血性。“国家不幸诗家幸”。由北而南的三千里迁徙之后,所谓国难与国运、历史与人性、民族与未来,从此都连着他所亲历的破碎、耻辱与沉寂。他的心里装着中国的辽阔大地。穆旦从未因此而忽略“自我”作为生命存在的事实。对此,易彬分析道:“在现代中国,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个人所欲追求的是自由、独立的精神品格,国家所要求的却是集体意志、全民抗战,国家总是不断将‘小我’拉入‘大我’的行列,不断地压低乃至扼杀那种基于个人的生存体验而发出的声音”。因此,穆旦一些重大的人生选择“并非对于社会制度的简单认同,并非去做一个集体性的‘大我’,而是为了在民族国家建构这一无可逃避的时代背景之下实践个人自由的信仰,秉持‘良心’,保持‘个性’。”(第357页)应当说,这是易彬对穆旦的懂得,更是他对穆旦的致敬。一百年多来来,中国新诗如果有“良心”和“个性”的存在,首先它就不能沦为政治的附庸,不能成为宣传品,而应当保持“诗之为诗”的独立审美性。
其次,穆旦在现代诗歌里永远清晰地看得见“人”,更看得同“个体”的真实面孔。这种“人”的自觉,不仅丰富了穆旦的情感丰富性,而且赋予了他诗歌中难得的超越性力量。今天,或许人们津津乐道却又疑惑顿生的是,为什么穆旦会在24岁辞去令人羡慕的西南联大教职而毅然加入远征军、赴缅甸担任随军翻译?为什么他不在后方做一个大学教师而前线远征作战,这对于承平年代的青年人来说,或者对于当下那些“精致的利己主者”来说,都是特别无法理解的理想主义和家国情怀。一个未曾经历战乱与离散,未曾亲历苦难与耻辱,未曾置身硝烟与炮声中的人,确实难以理解诗人的情感与抉择,难以理解这种爱的广袤与崇高。
“穿越野人山”可能是穆旦此生所经历的最深刻的战争与死亡教育。然而,当战争的“劫难”终于平静地进入诗歌,穆旦便显出了他的丰富与深刻。他不仅胸怀“国之大者”,更重要的他还胸怀“人之大者”。亲历了战争的穆旦从不满足于英雄主义的豪迈,相反,他的战争诗篇里充满着对人类、人道与人性的反思。“那每一伫足的胜利光辉/虽然照耀,当我终于从战争中归来,/当我把心的深处呈献你,亲爱的,/为什么那一切发光的领我来到绝顶的黑暗,/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隐现》)战争带来了“胜利的光辉”,为何又领我来到“绝顶的黑暗”呢?因为,一切战争都站在人性和文明的对立面。这里所遵循不再是战斗的“胜利的逻辑”。穆旦的深刻在于,他不愿让个体的死亡让位于更为崇高、更为本质的“胜利”目标。他看到的是战争对生命的“推毁”,是战争宏大叙事下个体的生命也面临的“不幸”。因此,他穿过“野人山”,感叹的竟是“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战争结束后,他呼唤“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这一切,都赋予了穆旦诗歌以一种巨大慈悲或悲悯的力量。王佐良先生评论说,“穆旦对于新写作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应当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普世化的悲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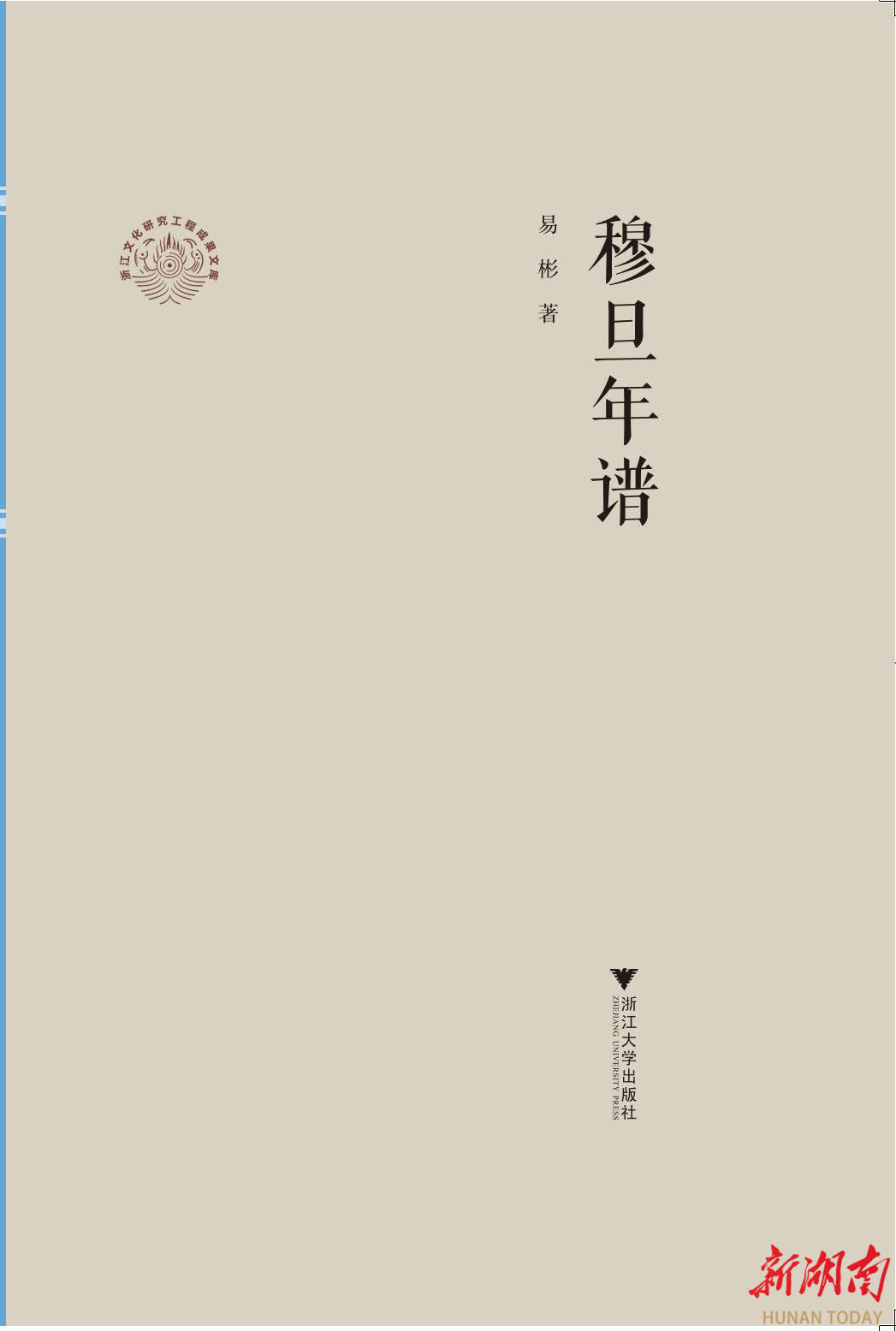 《穆旦年谱》(2024)
《穆旦年谱》(2024)
或许是出于对“人”和“人性”的尊重吧,穆旦那些记录南迁的诗歌里总能看到国难中具体的“人”的面孔。那里有中国乡村的贫困:“一个煮饭瘦小的姑娘,/和吊在背上啼哭的婴孩……”(《小镇一日》),那里也有中国现实的漠然:“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哂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那里看有中国历史的凝重:“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与失望压在他身上/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赞美》)……
第三,穆旦将新诗审美的法度建立在国语现代化的基础之上,他追求新诗的口语化,同时又特别注意对西方诗学的启蒙与借鉴。一方面,中国新诗的百年发展,吸收了自《诗经》《楚辞》以来的古典传统,但是,新诗之“新”意味着它有着与古典诗歌异质的审美标准。无论古典诗学的传统何其悠久,新诗的语言、节奏也不可能是传统韵语表达的现代性转化,新诗必然融入整个世界的诗学体系。那么,新诗如何表现时代、如何表达自我,如何在小我与大我、文学与政治之间建构起它的主体性,应当说穆旦以其作品显示出他在中国新诗现代化方向上作出过巨大努力。1940年代,周珏良在评价穆旦的诗时就说过,他“用极近口语的文字写出了庄严的诗,在白话文已被提倡了二十多年的今日,而每有大制作还是觉得此种文字不够典雅非用文言不可的时候,这种成就就是特别可注意的。”(周钰良:《读穆旦的诗》,《益世报·文学周刊》第48期,1947年7月12日)另一方面,纵观中国新诗的百年发展,其勃焉兴焉皆与西方现代诗歌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分。“五四”新潮之于现代新诗的促进,新时期西方文化的涌入与“朦胧诗”的兴起,都是新诗与世界对话的明证。
为了揭示百年新诗发展的这种开放性,易彬对当年穆旦所在的南开中学、西南联大的课程与专业,不乏面向世界的立体分析。更重要的是,穆旦当年在流亡南渡的路上,在湖南南岳山间就曾受教于英国教授燕卜荪,从那里获得过现代诗启蒙,后来穆旦又受读到叶芝、艾略特、奥登、狄兰等著名诗人的影响,对惠特曼《草叶集》爱不释手,晚年穆旦更是在孤寂中译出了长诗《唐璜》等。应当说,发生在穆旦身上的这一切,无不昭示出中国新诗发展融入世界诗学谱系的重大命题。
三、幻想尽头的生命延伸
 易彬。
易彬。
易彬援引穆旦晚年的诗作《幻想的尽头》作为书题。我以为,“幻想”一词道出了诗人的生命真相。诗人有意不说“想象”,而说“幻想”,并以“幻想”作为他对生命的告白。“我已走到了幻想的尽头,/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智慧之歌》)。在这里,“幻想”更令人联想起人生的“如梦如幻”。人生忽然,“幻想”不定;天地永恒,春秋代序。
“幻想”也不同于“理想”。“理想”似乎隐含着某种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理想”很可能瓦解生命的痛苦而将生命引向形上关怀。与“幻想”相比,这种“形上理想”很可能失之简单与肤浅。穆旦一生,确乎有太多奔向“理想”的举动。最大的理想之举,应当是24岁辞去大学教职而投身异国战场,35岁风华正茂时又携生物学博士的妻子从美国芝加歌大学取得学位后回到“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这些异于常人的重大选择背后,无疑是诗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表现。但这种爱,更多出于生命本能或文化自觉,诗人似乎并不愿意人们将它纳入某种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的阐释之下。换言之,穆旦的人生选择不可能以凭借那些“观念标签”去作类型化看待。《穆旦传》里提到,穆旦妻子周与良多年以后回忆起穆旦当年执意回国的场景:“(他)经常与同学们争辩,发表一些热情洋溢的谈话,以至有些中国同学悄悄问我,他是否共产党员。我说他什么也不是,只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抗战时期他亲身经历过、亲眼看到过中国劳动大众的艰难生活”(周与良:《怀念良铮》,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132页)。应当说,“他什么也不是”的情感才是最朴素、最真诚的。穆旦对祖国和人民的情感,如同赤子。他的回国,应与与战时南迁路上见到的那些土地、那些苦难无法分开。1950年代以后,穆旦当年参加远征军的壮举竟一再要求当作“历史问题”予以交代和检讨。党派之间的政治敌对在政权鼎革之后却成个人生命的撕裂和毁灭。这是穆旦未曾想到的。在诗人心里,35岁回国选择,与24 岁的参加远征军都出于他内心的“良知”。
令穆旦始料未及的是,相较于三四十年代,1950年代以后社会文化语境,将严重止息他的诗才。1957年,他在《葬歌》中写道:“你可是永别了,我的朋友?/我的阴影,我过去的自己?/天空这样蓝,日光这样温暖,/在鸟的歌声中我想到你。”诗人在告别旧“我”,或许也在告别关于新诗的理想?
然而,穆旦并未真的告别与放弃。他发表于《人民文学》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显然带着“歌颂”的预期,但他并未因此而丢失三四年代以来的“抒情”方式。这时候,他也不未像老诗人艾青、卞之琳那样,采取一种“今昔对比的视角”来表现“新旧社会两重天”。相反,穆旦从那奔腾的水浪里看到了历史之于生命的淹没:“又像这古国的广阔的智慧/几千年来受到了压抑、挫折,/于是泛滥为荒凉,忍耐,和叹息/有多少生之呼唤都被淹没!”(第440页)历经那么多“思想改造”,穆旦依然坚守着文学与政治的边界,他丝毫未曾在肤浅的歌唱里丢失“诗之为诗”的那独特性,相反,他始终坚持将自我的“压抑”、历史的“挫折”嵌入逝者如斯的“河水”之中。这正是中国百年新诗建构中的生命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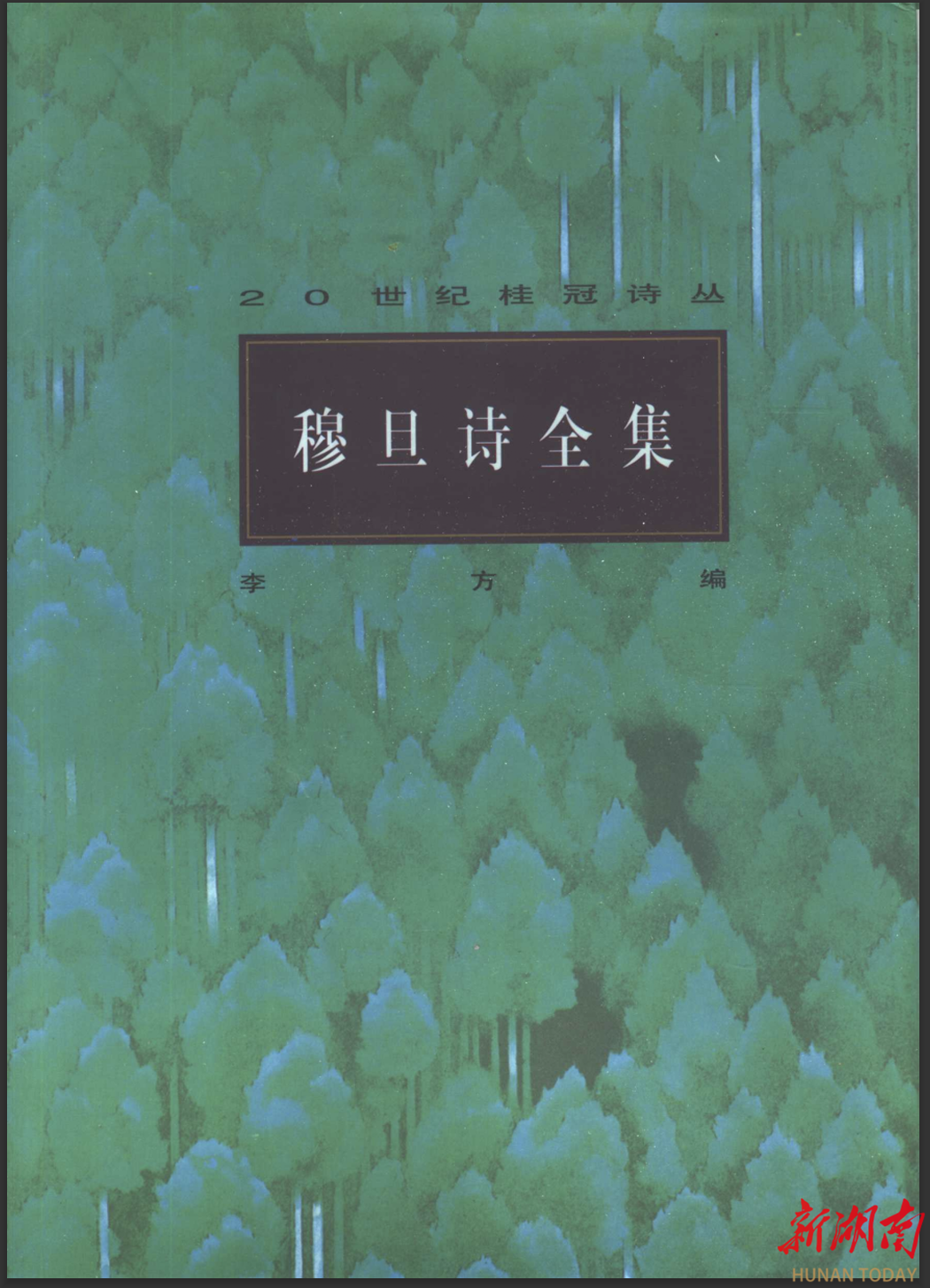 《穆旦诗全集》
《穆旦诗全集》
于新中国的诗坛“昙花一现”之后,穆旦于1958年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判处管制三年,从此被赶下外文系讲台,到图书馆“监督劳动”,日常编写英文目录与打扫卫生。无休无止地“交代”之后,“文革”中等待穆旦的更是劳改、抄家、批斗等更大的精神折磨。
《穆旦传》集中援引了来自穆旦档案文件里的《我的思想自传》及《历史问题交代》。读这些档案文字可以想象穆旦当年所承受的外在压力,我们不得不一再感叹穆旦及一代知识人的精神命运。在巨大的人生起落中,知识分子的苟安与脆弱很可能让人最终直面思想的“原罪”,他们甚至完全丢失原有的语言。这正如陈徒手所说,“人的愤怒容易被转移,疑惑很快被抵消,不快渐渐被化解,往往又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来对待运动……”(《人有病,天知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31页)。然而,相对于其他被整肃至死的知识分子来说,穆旦的境遇和结局远并不是最惨的。他的悲情在于,在其不到六十岁的年龄里,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天才诗人的诗,更是他作为诗人的“未完成”;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青年、一个教师对于安定生活的渴望,是一个战士、一个“小职员”的一生所经历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更是“幻想的尽头”在诗人与每个人的生命深处延伸着。
(原载《书屋》2025年第10期)
责编:廖慧文
一审:廖慧文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