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8 18:02:23
文/何石
回望我的创作之路,那份“和着泥土的芬芳”、对“群山一样真性情的乡里乡亲”的深情,始终是我作品的灵魂。
作为一名从武警部队走出,最终回归湘西崀山这片文学沃土的写作者,我的笔始终追随着故乡的脉动。从《大山的儿子》《那山那村》,到刚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驻村冻江源》,我笔下的人物在变,故事在更新,但对土地和人民的深情始终如一。今天,当“新乡土文学”或“新地域写作”成为文学界讨论的热点时,我想结合《驻村冻江源》的创作实践,分享我对新时代地域写作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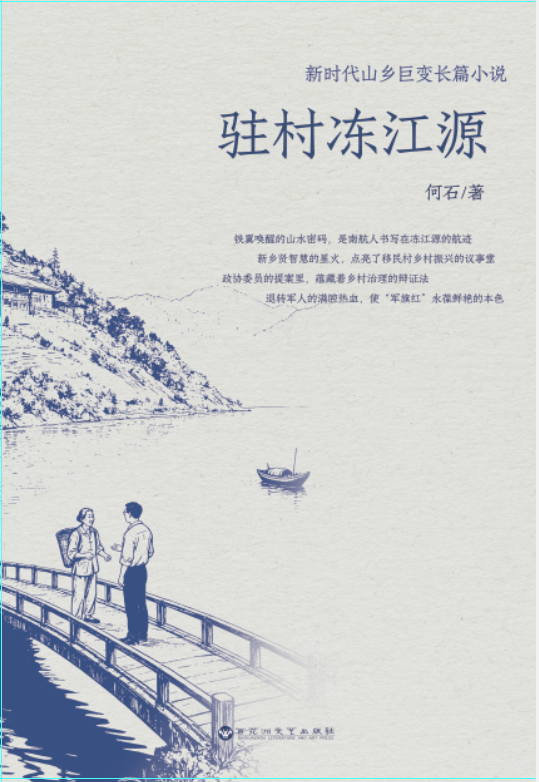
一、我的“地域观”:地域不是背景,而是主角
新时代的地域写作,首先要摒弃将“地域”视为一成不变的风光背景或奇观展览的旧观念。地域,尤其是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乡村,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呼吸着的、有性格的“主角”。我写《驻村冻江源》,初衷就不是为了描绘一幅静止的“溪山如画图”,而是要记录下冻江源头大塘村(在书中化名为“袋子田村”)这个生命体如何在时代的激流中挣扎、阵痛,并最终破茧重生的全过程。
在《驻村冻江源》中,我以那座摇摇欲坠的鸭婆桥作为开篇切入点。这座狭窄的木板桥,承载着村民们的生计与希望,也成为制约发展的“肠梗阻”。桥东是传统的圩日集市,桥西是亟待开发的沃土,桥上是村民日复一日的艰辛往返,桥下是奔流不息的冻江水。这种具象与象征的交织,让读者直观感受到乡村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
我所理解的“新矛盾”,正是这个“主角”在成长中必须面对的考题。鸭婆桥的阻塞、村小的衰落、黄半仙的“风水执念”、初期产业探索的失败……这些都不是我凭空设置的戏剧冲突,而是我在多年走访、蹲点中,从湘西无数真实村庄里“听”来、“看”来的。它们是中国乡村迈向现代化时普遍性阵痛在“袋子田”这个具体地域上的投射。
我的任务,不是居高临下地批判这些矛盾,而是怀着理解与同情,去展现地域内部如何孕育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力量。比如,曹劲松解决干旱问题的方式颇具象征意义——不是简单发放救济粮,而是运用南航的人工降雨技术。这既是对“扶贫先扶智”的深刻诠释,也是我对乡村人情社会运作逻辑的文学化表达。
二、我的“人物谱”:父老乡亲就是时代的主角
我笔下的人物,尤其是黄大牛、曹劲松、黄小牛这群人,常被评论家归为“新农民”或“平民英雄”。对我而言,他们首先是我无比熟悉的、可触可感的乡里乡亲。
驻村第一书记曹劲松的形象,其原型来源于南方航空湖南分公司驻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安山乡大塘村的第一书记熊劲松。这位来自南方航空的干部,没有高高在上的做派,而是真正把根扎在了大塘村的泥土里。在塑造这一角色时,我着力表现他如何将现代管理智慧与乡村实际相结合,例如他与村民黄半仙的“山路之争”中,既尊重乡规民约,又善于用现代法治思维化解矛盾。
黄大牛这一角色则代表了我对“新乡贤”的理解。他从广州返乡创业,带动村民发展特色农业,体现了新时代农民敢于追梦、勇于担当的精神。我刻意保留了他作为农民特有的质朴与狡黠,这种现实主义笔法让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在人物塑造上,我特别注重刻画黄小牛、蒋丽这样的“回归者”。因为我看到,乡村振兴的希望,绝不只在于外部的“输血”,更在于能否吸引本土的、有见识的年轻人回流。他们的“回归”,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带着城市文明的成果(如蒋丽的自媒体技能、黄小牛的“大桥经济”视野)反哺乡土。我写他们,就是想告诉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广阔的乡村,同样是实现人生价值的精彩舞台。
在《那山那村》的创作中,我就尝试避免将人物塑造得“高、大、全”。扶贫干部们也会有苦恼和迷茫,也会有家庭矛盾,这种本色化的人物书写方式赋予英雄以丰满的人性血肉,更加立体,更加感人。
三、我的“语言术”:让泥土气息与时代节律同频
语言是文学的肌肤。我始终坚持,地域写作的语言必须有根。这个根,就是鲜活的地域语言。《驻村冻江源》里大量的方言俗语,如“打扁担”、“斗啵”、“扳栗树门槛”,不是我为了增添风味而刻意撒上的“佐料”,而是袋子田村民自然而然的生活语言。我用它们,是为了让读者能真切地“听到”这个村庄的呼吸,让人物一开口就带着崀山的味道。

▲《驻村冻江源》主人公原型——南航湖南分公司驻湖南新宁县大塘村第一书记熊劲松深入群众嘘寒问暖、问计索策。
但仅有方言是不够的。乡村振兴是国家级战略,它自带宏大的叙事场域。因此,我也有意识地让曹劲松等干部角色的语言,带有一定的“公文感”和节奏感。这种语言与方言的交织,恰恰真实地反映了当下乡村的语境:传统的生活逻辑与现代的治理话语正在这里碰撞、融合。我的尝试,就是让文学语言既能“接地气”,又能“接天线”,真实反映这个复杂而充满生机的时代现场。
在《那山那村》中,我已经开始这种语言实验。例如《退票》中描写马小牛俯瞰园区时的场景:“漫山名贵的油松,在春寒料峭的季节,舒展着银白色的针叶,挺直了腰杆,仿佛一个个傲霜斗雪的戍边勇士,冷凛凛地目不斜视着”。通过生动的用词、巧妙的比喻,将眼前的油松幻化成戍边的勇士,在写实中赋予诗意的升华。
四、在地域性中寻找普遍性:我的创作方法论
优秀的乡村题材作品应当既有宏观视野,又能微观切入;既要展现国家战略的磅礴力量,又要刻画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在《驻村冻江源》的创作中,我尝试通过 “袋子田范本” ,展现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在具体地域的实践过程。
作品中的“南航模式”取材自南方航空“航空引领、产业带动”的真实帮扶模式。在现实中,南航推动成立5家农业合作社和电商平台,打造千亩油茶林、206亩脐橙园和扶贫工厂,2020年通过消费扶贫实现销售额超千万元。我将这些真实案例进行文学化处理,通过曹劲松这一角色,展现了“国家队”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
我特别注重表现乡村振兴中的辩证关系。作品没有回避发展中的阵痛:修建水库导致良田淹没的历史遗留问题、撒胡椒面式扶贫的局限性、返乡青年与留守老人的观念冲突。这些矛盾的呈现非但没有削弱主题,反而让乡村振兴的叙事更具厚度。在描写黄小二与文三妹的婚姻时,我既写出“老牛吃嫩草”的世俗眼光,也展现新时代农民婚恋观的变化,这种复杂性处理显示出对乡村肌理的深刻理解。
五、结语:做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书记员”
有人问我,《驻村冻江源》算不算成功?我认为,一部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是否真诚地记录了这个时代,是否塑造了能让读者记住的人物。对我而言,写作就像当年在部队站岗一样,是一种职责。我所站的这班岗,就是为生我养我的湘西大地,为这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立此存照”。
在《驻村冻江源》书稿全面收官的时候,已是春和景明、草长莺飞的乙巳三月。我站在新修的鸭婆桥头,看着库区灯光次第亮起,民宿的灯笼红艳,路灯昏黄。我忽然明白,大水江水库的风景,不止在山水之间,更在人与水的共生共荣中。五十多年前,人们用汗水汇聚出这片水域;五十多年后,这水域反哺着人们的生活。
乡村振兴不是标语,而是黄大牛的山歌、蒋丽的短视频、徐友华的米酒、移民新村的广场舞。是鲜活的日子,在水的倒影里,静静流淌。
“劳声互答,人影绰绰,鸡犬相闻”,这是我向往的、也是正在逐步实现的乡村图景。袋子田村的故事,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故事的缩影。我的笔不会停歇,我将继续行走在崀山的山水之间,用我的文字,去书写更多“黄大牛”“曹劲松”们的英雄传奇,去描绘“新时代”“新农村”更加壮阔的未来图景。
这,就是我这个“老兵”和“老作家”所能尽到的、最微薄也最赤诚的责任。
【何石,男,湖南新宁县人;退转军人,文化传媒工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曾获省级文学征文奖、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与中国小小说学会联合征文奖等奖项多个。在武警部队主编的小说集《武警传奇•死囚在追踪》及多个年度选本,《小说选刊》《湖南文学》《湘江文艺》《广西文学》《延河》《奔流》《三月三》《散文选刊》《红豆》《芳草》《湛江文学》《北极光》等书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200多万字,已出版《极目南国》《笑傲潇湘》《大山的儿子》《那山那村》《驻村冻江源》等专著多部。小说集《那山那村》被选入新闻出版署2022年农家书屋推荐书目。】
责编:周洋
一审:戴鹏
二审:曾佰龙
三审:邹丽娜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