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联 2025-07-17 09:1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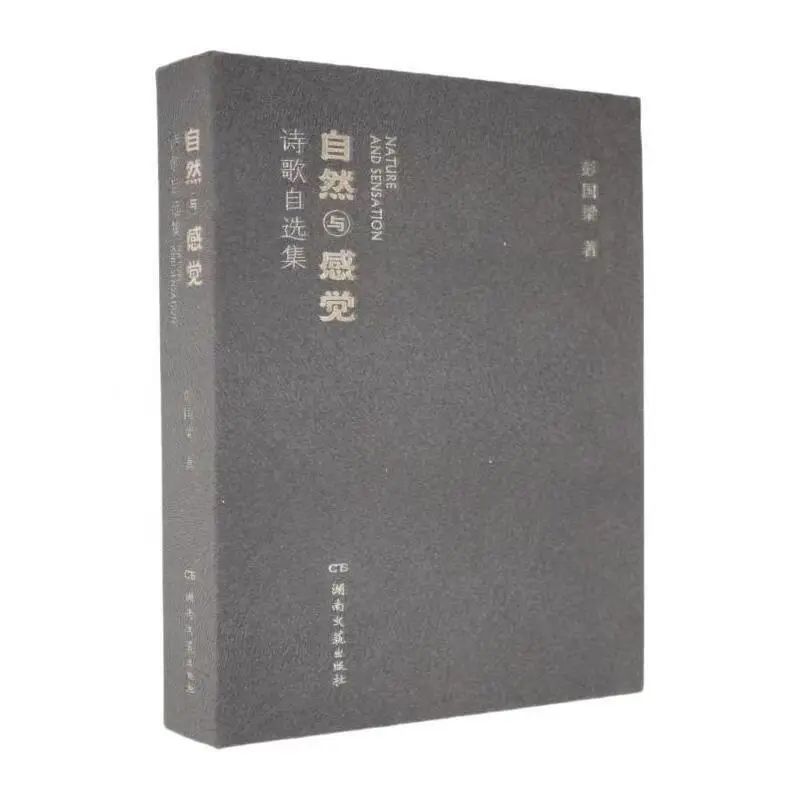
根系湘土,诗写沧桑——读彭国梁的《自然与感觉——诗歌自选集》
文|杨金
翻开彭国梁的《自然与感觉——诗歌自选集》,一股泥土般的质朴扑面而来。作为湖南新乡土诗派代表诗人,彭国梁的诗集并非是对田园牧歌的怀旧,而是以现代意识烛照乡土经验,在泥土深处挖掘诗性光芒的创造。
乡土基因的觉醒
彭国梁的诗歌,首先令人动容的是对自然的那份纯粹而深沉的热爱。《自然与感觉——诗歌自选集》共收录诗人从1980年至2024年四十多年来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芙蓉》《湖南文学》《诗歌报》《飞天》《绿风》《诗林》等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及专业诗歌刊物上的诗作二百五十余首。这些诗饱含生命质感的意象,以惊人的通感能力,让万物皆成为诗人灵魂共鸣的琴弦。
在《吊脚楼》中,他写道:“小镇上的人一个一个/都被你熏陶/因此小镇上的人/有水的柔情/有岸的剽悍”……瞬间让事物拥有了血肉与声带。这是在时代变迁中对文化根性的确认,对乡土智慧的礼赞。即便后来从农家子弟到求学在外、工作于城市,“离乡”的经历非但没有切断他与乡土的联系,反而赋予他“双重视域”:城市生活的喧嚣与异化,成为他反观乡土价值的镜鉴;地理距离的拉长,则发酵了乡愁。如,《在城里 在乡下》这首诗,就是一首以小见大、充满时代感和生命体验的作品。它用“金字塔古森林/长江黄河”与“摩天大楼立交桥”并置,形象刻画出城乡风貌、文化特质的差异,诗性表达了对乡土传统在现代转型中的阵痛与坚韧。
新乡土诗派的自觉构建
新乡土诗派区别于传统乡土诗歌的关键,在于它跳出了“田园牧歌”的浪漫化书写,“回到土地本身”,以平视的视角捕捉乡土的原生状态与生命肌理,实现了与人类情感的共振。如,《老猎人与狗》以冷峻的叙事笔触和仪式化的场景,对人狗关系进行倒置重构,诗中提到“老猎人像一棵枯树/弯在路的尽头”,这就是将“老猎人”沦为“枯树”般静止的背景;“猎狗是等老猎人睡了之后/从墙角那个窝里爬出来的”“它知道马上就要死了/它死也要爬到山顶上去”则颠覆了将狗作为工具符号,让狗成为了动态叙事的驱动者。这种权力关系的逆转,重构了更平等的乡土生命伦理。另外,《大和小》中的“大海”与“蓝天”,既是具体乡土自然元素,更被升华为承载情感的容器;“海角”“天涯”的地理距离,通过“思念的咽喉”瞬间转化为亲密联结,这些都让乡土成为情感共振的磁场。
新乡土诗派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日常性”的坚守与发掘。彭国梁的诗歌总是将镜头对准乡土生活中无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场景,如夏夜婆婆子在小巷里的家长里短、燃烧的稻草堆旁农夫坐在田埂上抽旱烟时的沉默等等。这些场景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却蕴含着自然界最本真的生命力。
诗意栖居的精神皈依
在《自然与感觉——诗歌自选集》中,彭国梁娴熟采撷方言的鲜活韵律,赋予诗歌浓郁的地域气息,却又能挣脱地域的藩篱。如,《野店》中提到:“想住就住下来/草鞋和伞丢在门弯里/热了吹山风/冷了烤蔸根火/竹筒里流下的/是后背山里的温泉水/抹一点到脸上/就晓得/人不留客水留客”,其中“门弯”“蔸根火”“后背山里”“晓得”等方言,赋予了语言粗粝的泥土感,却以现代诗学提纯,用“人不留客水留客”的澄澈意象,使方言突破了地域局限。
尤为珍贵的是,彭国梁以诗人的赤子之心与哲人的深邃目光,在自然物象与生命感觉的交汇处,重构了一座安放现代人乡愁的精神家园。他笔下的物象,拒绝宏达叙事,转而在卑微中构筑神圣空间,常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物质与精神的桥梁。如对一株老树、一片峡谷的凝视,最终升华为对消费社会物欲异化的诗意抵抗。他的诗行,在时代洪流中,为所有漂泊的灵魂守护着那片可以“诗意栖居”的沃土,那片根植于“自然与感觉”深处的精神原乡。
彭国梁的《自然与感觉——诗歌自选集》,是其诗歌艺术的一次集中展现,也是其生命轨迹与艺术追求熔铸的结晶。他以现代性的目光重新审视自然,以凝练克制的语言,承载着澄澈的意境,为我们在喧嚣的当代语境中,提供了一份沉静而又充满生命韧劲的精神慰藉。
责编:周听听
一审:周听听
二审:蒋茜
三审:周韬
来源:湖南文联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