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边的玄想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5-07-14 08:27:07

参不破,永州的表和里
■梦边的玄想
永州这方水土,是块被时光反复捶打的铁。表面瞧着,是山是水是草木,骨子里却凝着些不肯软的劲,像深潭底下的石头,水再清,也照不透那层沉郁的黑。

阳明山杜鹃。本文图片均由通讯员摄
春日里,阳明山的杜鹃开得野。那红,不是温室里养出的娇柔,是从岩缝里挣出来的血,是挨过霜雪,才敢在料峭里把一冬的憋屈,泼成漫山遍野的疯。万寿寺就藏在这火海般的花丛里,黄墙黑瓦被花影浸得发暖,晨钟撞破雾霭时,倒像给这泼天的红,按了个沉稳的印。游客和香客的脚印叠在石阶上,和花瓣混在一起,分不清是来求佛的,还是来赴这场花劫的——佛说众生平等,许是也容得下这花的疯,人的痴。
草丛里是有异蛇的。黑质而白章,伏在腐叶间,像一段拧着的铁。柳宗元写过它们,说“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可比起当年“苛政猛于虎”的世道,这蛇的毒,倒显得直白些。它不伪装,亮出獠牙就是了,不像有些东西,披着光鲜的皮,吃人时连骨头都不吐。

云冰山
冬来,云冰山的雾凇挂在枝丫上,像谁撒了把碎银,冷得扎眼。冰挂垂着,尖顶朝下,对着土地,仿佛要扎进什么深处去。千年鸟道上,候鸟拍翅而过,黑影掠过冰面,是逃这苦寒,还是奔更未知的远方?说不清。只晓得,这冰,这鸟,都比人活得明白,该硬时硬,该走时走。
潇水与湘水在这儿挽了个结,像两条浸了墨的带子,绕着城郭流。水是活的,载着柳宗元的墨香,带着怀素的酒气,裹着陈树湘的热血,也漂着女书里那些缠缠绵绵的字。你站在河边看水,水里也在看你,看你是不是带了这水土里长出来的犟脾气。萍岛是个渡口,一头拴着“表”的热闹,一头系着“里”的沉郁,船来船往,载走些故事,又带来些新的,只是水还是那水,流了千年,没见它喘口气。
永州的松树,是该提一提的。它们长在石缝里,枝干虬曲,像被什么东西拧过,却偏不肯弯腰。风来,不躲;雪来,不避。陶铸说松树有风格,不择地而生,不畏寒而枯,把一切都献给人类。永州的松,大约就是这性子,没什么好姿态,却有副硬骨头,站在那里,就是对这天地的倔强回答。
李达是个真正的人。这“真正”二字,在这年头,比金子还稀罕。他在永州的泥土里扎过根,思想却像松针,刺破过时代的雾。不装腔,不作势,认准了的理,九头牛也拉不回。他的文章,不是花拳绣腿,是实打实的钢,敲下去,能听见响。这样的人,像永州深山里的矿,看着不起眼,炼出来,却是好钢。
柳宗元当年蹲在这儿,写了些山水。《永州八记》里的小石潭,水是清的,鱼是“空游无所依”的,可细想,那清里藏着多少化不开的闷?柳子庙的香火,一年年续着,敬的是他的文,也是他那股在绝境里不肯烂的劲。碑廊的石碑被摸得发亮,檐角的风铃摇着,像在重复他没说完的话——这世间的苦,原是写不尽的,却偏要有人写。
怀素的字是疯的,是野的,笔走龙蛇,像在纸上打架,又像在哭在笑。他用蕉叶练字,把文静的叶子都写得带了火气。周敦颐说莲“出淤泥而不染”,可宋朝的永州的泥到底多深?能养出这样的莲,生就有这样的花,在脏水里把腰杆挺得笔直。宁远文庙的柏香,混着大成殿的檀香,绕着孔子的牌位转,那香气里有股执拗,像在说:文脉这东西,饿不死,也打不烂。零陵武庙的关公像瞪着眼,青龙偃月刀泛着冷光,与永州文庙的沉静对峙着,倒像是给这城安了两颗心,一颗藏着礼,一颗憋着勇。
浯溪的石头是要说话的。元结把文章刻在崖上,颜真卿拿笔去劈那石头——不是描,是劈。笔锋像砍柴刀,一刀下去石屑纷飞,字里全是筋骨,是安史之乱后,一个文人对着江山喊出的疼。《大唐中兴颂》哪是颂中兴?分明是把盛世的疮疤剜开,血淋淋晾在太阳底下。千百年风吹雨打,字口磨圆了些,那股狠劲却嵌在石缝里,像没拔干净的刺。
东安的沉香寺藏在更深的山里,渌埠头边上,被岁月磨得没了棱角。青苔爬满了山门,像给庙门戴了顶旧毡帽。香火不温不火,佛前的灯却总亮着,昏黄的光里,老和尚敲着木鱼,嘴里的经咒混着山风,倒像是在跟树说话。寺后的塔林,石佛的脸被雨水啃得模糊,偏那双眼,还望着湘江第一湾两岸的人间,像在问:苦么?还熬得住么?
陈树湘的血,该是渗进这土地了。断肠明志那一刻,他眼里的永州,该不是什么山清水秀的模样。是枪林弹雨里的石头,是泥泞里的草,是拼了命也要往前拱的决绝。他的勇,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硬,像阳明山的杜鹃,非要在最贫瘠的地方开出最烈的红。
蒋先云是条汉子。黄埔三杰的名头,不是吹出来的。他手里的枪,笔一样准;嘴里的话,刀一样利。在那风雨如晦的年月,他像支火把,烧得很旺,照亮过一段路。可惜,火把太烈,容易被风灭了。但那点光,总有人记得,像黑夜里划过的流星,短暂,却把“忠”字刻在了永州的天上。
建文帝的传说,是永州披的件隐身衣。谁也说不清龙袍是不是藏在哪个岩洞深处,只知道这山水容得下落魄帝王,也容得下砍柴樵夫。它不声张,把秘密裹在雾里,像老母亲藏起给孩子的糖,不叫外人看见。历史这东西,说得太明白,反倒少了嚼头,永州懂这个理。
上甘棠的老墙,是被烟火熏黑的脸。龙家大院的飞檐翘得再高,也高不过头顶的天;李家大院的青砖砌得再齐,也砌不住墙缝里钻出来的草。这些院子像蹲在时光里的老人,看日头东起西落,看子孙来来去去,嘴里不说什么,心里却明镜似的——再光鲜的门楼终要被青苔爬满,再显赫的姓氏也敌不过檐角的一滴雨。
九嶷山的舜帝陵,三分石的影子,都浸在雾里。千百年了,来的人去的人,都想从山里讨点说法。是孝?是忠?还是那点说不清的“道”?石碑上的字被雨水冲得模糊,倒像故意不让人看真切。有些东西,看得太透反倒没了滋味。

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
瑶寨藏在山褶里,像被时光遗忘的角落。长鼓舞的鼓点敲起来,不是热闹,是从远古传来的暗号。舞者戴着头饰,旋转时银饰叮当,像把星星撒在了地上。那舞步里有狩猎的勇,有迁徙的苦,有对祖先的敬,每一个腾跃都带着山的魂。盘王大歌唱起来,调子苍凉又绵长,从天黑唱到天明,歌声里裹着山风,裹着兽骨的腥气,裹着一代代人没处说的苦与盼。他们把历史绣在衣襟上,把心事织进腰带里,不识字,却把日子过成了诗,比刻在石头上的字更经得起磨。
女书是奇的,一群女人在男人看不见的地方,造了自己的字。那些笔画弯弯绕绕,像缠脚布,又像解不开的结。是怨?是诉?还是在闭塞天地里给自己开的小窗?她们把话写在布上藏起来,倒比刻在石头上的字活得更久些。
这永州,寺里的钟与山里的风,文庙的香与武庙的刀,异蛇的冷与杜鹃的烈,都在较劲,又在和解。你若夜里走过柳子街,能听见柳子庙的风铃和万寿寺的晚钟撞在一起,像两个老头在说悄悄话,说些关于苦,关于熬,关于那些死了还活着的东西。这表里的滋味,原不是给闲人尝的,是给那些肯把心沉下去,在黑里摸过,还敢抬头看天的人预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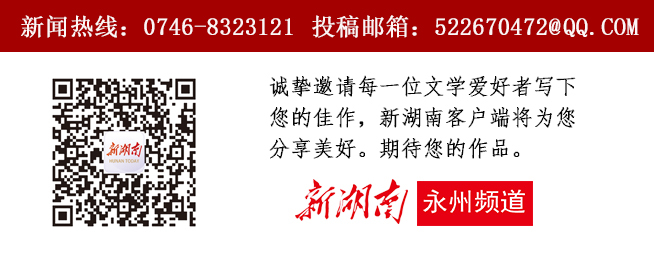
责编:黄柳英
一审:黄柳英
二审:严万达
三审:李寒露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