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双石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5-07-11 09:48: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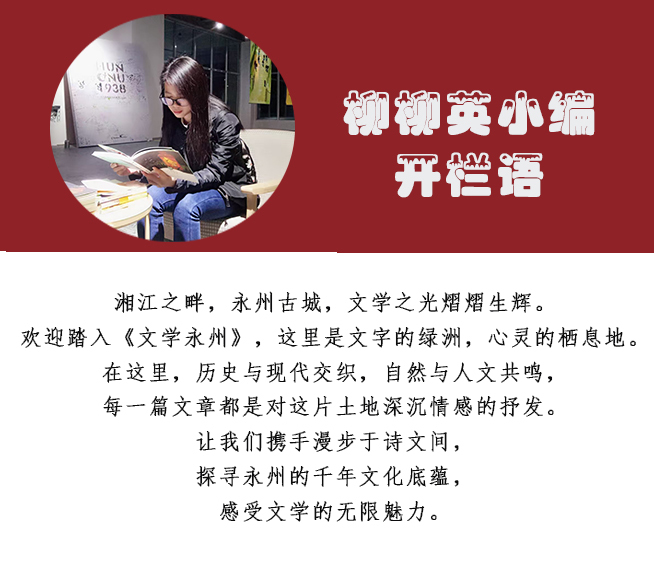
■魏双石
在唐宪宗元和四年的深秋,潇水瘦得只剩下一线,柳宗元乘着一叶扁舟,漂到了永州。船靠岸时,几只乌鸦从芦苇丛中惊起,呀呀叫着飞向灰蒙蒙的天空。他站在船头,望着远处低矮的城墙,忽然想起长安的朱雀大街,此时该是银杏叶落满地的时节了。
西山脚下龙兴寺的和尚给他开了偏门。厢房漏雨,墙角长着青苔,夜里能听见老鼠在梁上跑动的声音。母亲病倒在床,咳出的血染红了帕子。请来的郎中把过脉,摇摇头走了,只留下几包草药。那年冬天特别冷,他在寺后荒地上掘了个浅坑,亲手埋葬了母亲。新坟上的黄土很快就被冻硬,像块生铁。

柳子庙
永州的官吏们躲他如避瘟神。只有刺史韦彪偶尔差人送些米面来,却从不肯露面。柳宗元常常整天无人说话,便研了墨,在纸上写信。墨冻住了,就呵口热气化开。信是写给长安旧友的,但往往写到一半便揉作一团——这些字句若被有心人看见,怕是又要惹祸。
元和八年的春天来得早。柳宗元在城西发现一处荒废的菜园,用积蓄买下后,在园中建了三间草屋,取名"愚溪草堂"。草堂简陋,但总算有了自己的栖身之所。他在溪边种了十几株柳树,又在屋后辟了片菜畦。每日清晨,他提着陶罐去溪边汲水,水面时常漂着几片柳叶。

永州的山水渐渐成了他的药。钴鉧潭的水清得能看见潭底的鹅卵石,石上附着青苔,像老人的眉毛。他常常在潭边一坐半日,看游鱼在石缝间穿梭。有次兴起,脱了鞋袜把脚浸在水里,凉意顺着脚底直蹿上来,倒把他逗笑了——这是被贬后第一次真心实意的笑。
西山不高,却颇有些险峻处。他沿着猎人踩出的小径攀爬,在半山腰发现一块平坦的巨石。坐在石上眺望,能看见远处的湘江如一条白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山上的石头多是青灰色,被雨水冲刷得圆润光滑。他常捡几块揣在袖中带回去,摆在书案上当镇纸。
永州百姓起初对这个北方来的贬官充满戒备。后来见他平易近人,渐渐敢与他搭话了。有个叫郭橐驼的驼背老农,种得一手好树。柳宗元常去他的果园,听他说些粗浅却实在的道理:"树要长得好,就得顺着它的性子来。根要舒展开,土要松软,水要适量。最忌整天摆弄,今天摸摸树干,明天摇摇树根,好好的树反倒给折腾死了。"柳宗元听着,忽然想到朝廷那些扰民的政令,不禁莞尔。
元和十年的春天特别暖和。溪边的柳树早早抽出了嫩芽,柳宗元在树下摆了张矮几,开始写《永州八记》。笔尖蘸着新磨的墨,在宣纸上沙沙作响。写着写着,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心境变了——钴鉧潭的水声不再让他想起长安的笙箫,西山的云雾也不再勾起对往事的追忆。这些山水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那年夏天,他收了个当地少年做学生。孩子姓蒋,家里是开药铺的,聪明伶俐。柳宗元教他读《论语》《孟子》,偶尔也讲些长安的见闻。少年听得入迷,眼睛亮晶晶的。有天傍晚下课,少年突然问:"先生想家吗?"柳宗元愣了一下,指着愚溪边的柳树说:"此间亦有春色。"
永州的冬天依然难熬。草堂四处漏风,他不得不裹着厚被子读书。墨汁常被冻住,要呵半天热气才能化开。但比起初来时的心境,现在的冷清反倒让他感到安宁。有时夜里醒来,听见雪粒打在窗纸上的沙沙声,他会想起长安的繁华,但已不再心痛如绞。
元和十四年,朝廷的诏书突然到了。柳宗元被召回长安,旋即又贬往更远的柳州。离开那日,永州下着小雨。蒋姓少年一直送到城外十里亭,临别时塞给他一包自家配的药丸:"南方多瘴气,先生保重。"柳宗元摸摸他的头,什么也没说。
船离开码头时,他站在船尾,望着渐渐远去的永州城墙。十年光阴,这座小城已经刻进了他的骨血。钴鉧潭的游鱼,西山的云雾,愚溪的柳树,都将随着他继续漂泊。而永州,因为他的文字,从此不再是无名的边城。
后来柳宗元在柳州病重时,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愚溪草堂。溪水潺潺,柳枝轻拂,阳光透过窗棂,在书案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但永州的山川风物,早已通过他的笔墨,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千年后的一个秋日,我站在愚溪桥上,望着同样的流水。导游指着溪畔一块石头说,那是柳宗元常坐的地方。石上长满青苔,看不出任何特殊之处。但当我翻开《永州八记》,那些文字便活了过来——钴鉧潭的水声,西山的云雾,小石潭的游鱼,都清晰如昨。
永州何其有幸,得遇柳宗元;柳宗元又何其有幸,得遇永州。这场跨越千年的相遇,让一片蛮荒之地化作文脉绵长的文化圣地,也让一个失意文人蜕变为光照千古的文学巨匠。永州这座小城记住了柳宗元,柳宗元也重塑了这座小城。就像愚溪边的老柳,地表上看是十丈红尘,地下却是千年盘错的根须。文人的失意与山水的相遇,最终在时光里酿成了文化的印记——苦难沉淀为力量,孤独结晶成永恒。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命运给你的磨难,恰恰是成就你的机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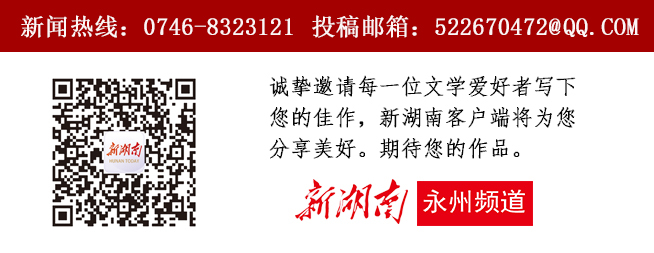
责编:黄柳英
一审:黄柳英
二审:严万达
三审:李寒露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