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联 2025-07-10 09:37: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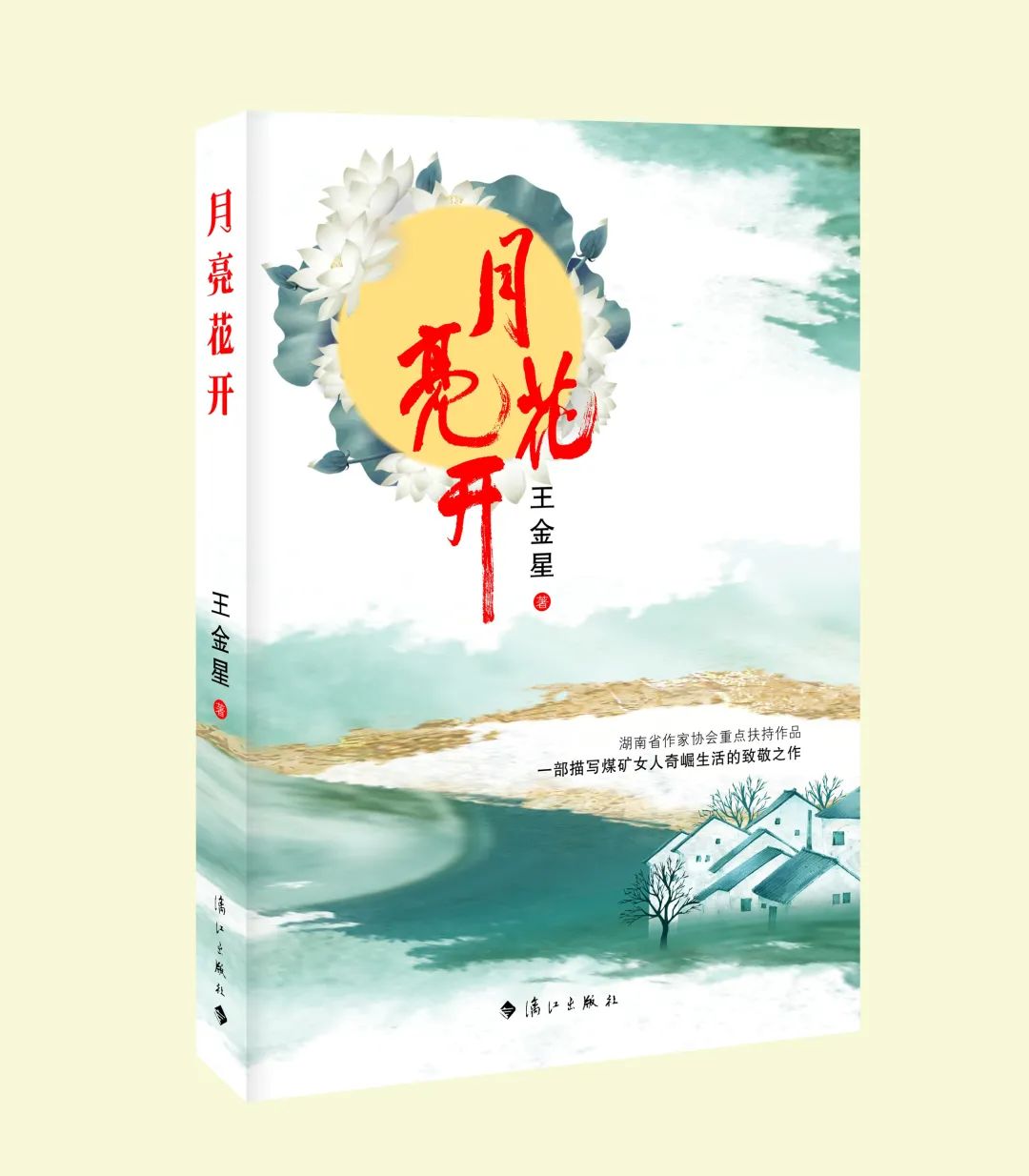
月光照彻的矿井——王金星长篇小说《月亮花开》的人性勘探
文 | 刘 朝
就工业题材文学而言,煤矿女性的身影长久隐没于历史的烟尘。国家一级作家王金星的长篇小说《月亮花开》,如一盏深井矿灯,骤然照亮了这个被遗忘的角落——湘南矿区的女人们顶着煤灰与泪水,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倔强绽放。她们是工亡家属、单身母亲、矿区劳动者,在命运的夹缝中活成一片星群,让这部国内首部聚焦煤矿女性群体的作品,既成为一曲悲怆的时代弦歌,更是一面映照底层尊严的文学之镜。
翻开书页,我们跟随王淑珍、朱淑芬们踏入南方矿山的褶皱深处。这里的生活粗粝如煤矸石:丈夫殒命矿难后的孤儿寡母,在冷眼中攥紧微薄抚恤金;守寡女子深夜偷读琼瑶小说时悸动的指尖,泄露了情感荒漠里隐秘的渴望。这些克制成审美化的情欲描写,既避免低俗又直击灵魂。而茶桌上“白茶如孩童,绿茶如少女”的含蓄暗喻,更让矿区男女间欲说还休的情愫在氤氲水汽中震颤。王金星以三十年矿脉浸泡的阅历,将这些边缘生命的辛酸史淬炼成钢——王淑珍放火烧房、酒后致人死亡的冲动劣性,朱淑芬借“抓小偷”博取社会认可却暗藏报复私心的虚伪,无不暴露人性在极端环境中的复杂。但她们在不幸婚姻中挣扎,却始终未失“铮铮傲骨与淑女风范”;她们被苦难压弯脊梁,却仍以昙花般“黑夜积蓄力量”的韧性,在矿井边缘开出一簇簇名为尊严的花。
书中流淌着湘南矿山特有的血脉。矿工“顶着阳光下井,出来只剩眼睛眨巴”的日常剪影,祭祀仪式中的袅袅香火,围炉煮茶时的方言俚语,共同织就一幅浸透汗与泪的风俗长卷。这些细节并非闲笔:当国企改制浪潮席卷矿山,女工从“矿工遗孀”沦为“下岗职工”的身份裂变,正是通过矿难善后赔偿的博弈、再就业歧视的冷眼等具体场景得以具象化。正如矿工唐爱军所言,小说为南方煤矿留存了“不可复制的文学史诗”,那些褪色的工装与锈蚀的矿灯,已然成为工业化进程中一枚枚灼痛人心的历史标本。
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将苦难熬成廉价的鸡汤。朱淑芬们并非圣洁的殉道者,她们有恨有欲、会怯懦也会算计:王淑珍为子女生存放下清高的挣扎,张跃进从痞气矿工到担当男人的蜕变,都透露出人性在极端环境中的复杂光谱。而男性角色的矛盾性同样深刻——流氓毛阿利转型慈善家的荒诞,矿长夫人马云操纵权力决定他人命运的腐败,共同构成矿区生态的浮世绘。这种“大慈大悲的朴素书写”,使作品超越悲情叙事,升华为对生命韧性的庄严礼赞。正如评论家吴树梁所言:“《活着》展示个体在人性与兽性间的挣扎,而《月亮花开》则呈现群体在黑暗中追寻光明的集体韧性”。这正呼应书中“月亮花”的隐喻:无需阳光施舍,她们以微弱荧光在黑暗中自证存在。
王金星的笔触兼具诗性哲思与冷峻真实。他写朱淑芬抓贼后受表彰的荒诞——英雄称号掩盖了其报复私心;写王素珍犯罪却未受法律制裁的法制缺失。这些情节并非猎奇,而是对社会病灶的精准解剖。当小红因矿长夫人打压积劳成疾、最终跳江自杀,作者以“无声的死亡”拷问权力异化的代价。而饮茶场景中“绿茶似少女”的轻盈诗意,又为沉重叙事注入喘息之隙。这种虚实相生的叙事张力,使小说既如矿灯刺破黑暗,又如月光抚慰伤痕。
当然,这部矿山史诗仍有未凿透的岩层。某些情节的戏剧性冲淡了社会变革的纵深透视——如毛阿利从流氓到慈善家的突变被指缺乏心理铺垫;对女性群像的浓墨重彩,也使刘铁伟等男性角色沦为功能化符号。但瑕不掩瑜。当文学日益沉迷于都市幻影与虚拟迷宫时,《月亮花开》以“深挖一口井”的笨拙勇气,让消失的矿区记忆重获血肉。它延续了周立波《暴风骤雨》的现实主义血脉,却将笔锋从农村转向工业腹地,填补了煤矿文学中女性叙事的空白,在机械轰鸣中打捞起一曲被时代湮没的女性生命交响。
放下书本,矿井深处的光影仍在心头摇曳。王金星以笔为镐,凿开的不仅是文学题材的疆土,更是一个社会曾被遮蔽的良心。当“月亮花”在书页间次第绽放,我们或许该记住作者这样的提醒: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在于钢铁洪流的奔涌之势,而在于能否珍视每一朵开在命运裂缝中的卑微花朵——这些女性“以柔弱的根须紧抓岩壁的姿态”,正是民族精神最坚不可摧的底片。她们在体制漏洞与性别压迫的夹缝中,用血肉之躯刻写下超越时代的启示录:尊严之花永不凋零,纵使长夜如墨,月光终将照彻矿井。
责编:周听听
一审:周听听
二审:蒋茜
三审:周韬
来源:湖南文联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