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 2025-07-08 11:32:16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网络文学是当前最热门的大众文化现象之一。6月17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发布的《2024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2024年,新增网络文学作品200万部,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5.75亿。读者性别结构均衡,男女比例相当。女频(女生频道)头部付费阅读平台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文学网站以性别分类作品,是其迥异于此前文学传统的重要特征。近几年,女频网络文学变化显著,“女性成长”主题突破题材限制,从言情到悬疑、科幻、现实等题材全面开花,不断拓宽边界。
 许苗苗。通讯员 摄
许苗苗。通讯员 摄
6月30日至7月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网络女作家在长沙参加由全国妇联、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2025年全国网络女作家培训班。培训班引导女作家深刻把握时代主题与创作方向,为她们的创作提供坚实的思想根基与创作遵循。
在业务技能培训上,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教授许苗苗以“突破‘大女主’:网络文学如何探索女性形象表达”为主题做了分享。她透过当下流行的网络文学“大女主”人设的表象,从角色扁平化到人格多维化,从情感套路到女性形象塑造的方向深入剖析了网络文学中女性形象书写的困境与突破。
许苗苗已研究网络文学20多年。20多年来,网络文学发展迅速,自身概念、作品形式、文本对象等不断发生变化,已经不限于当代文学、通俗小说、青年文化或亚文化领域。而其中“女性写、写女性”的网络文学,反映出新读写方式对女性写作的改造与促进。女频的叙事也折射出女性现实的性别意识及变化着的情感模式和价值取向。
专 访
短而精,新时代女性作者优势凸显
湘江副刊:网络文学分为女频和男频,但相较此前传统书刊上的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为何网络文学会形成这样鲜明的性别分野格局?
许苗苗:传统通俗小说也有目标读者,比如爱情小说主要面向女性,侦探破案主要面向男性。美国学者珍妮斯·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里就聊过女性读者群体和女性作者之间怎样互动、怎样阅读爱情小说。但严肃文学没这么明确的市场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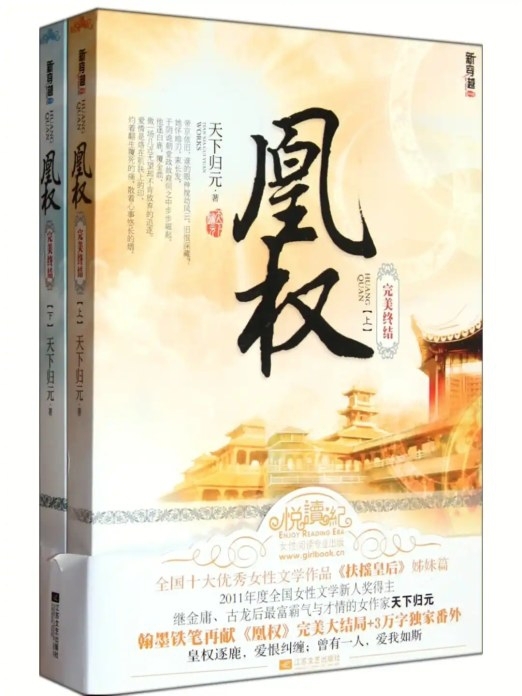
网络文学男频女频、男女读者群分得特别清楚,因为其本质是商业化的通俗小说,得靠收费活下去。怎么挣钱?做市场细分。性别分野除了直接面向读者市场,还方便作者和读者互相找到,这其实就是靠兴趣形成的“趣缘群体”。
虽说女频文主打女性向,但作者肯定不拒绝男读者,毕竟商业化写作都希望更多人看、更多人买单。有意思的是,网上的作者和读者不光通过文本联系,还会形成情感联结,比如“咱们都是女生,得互相支持”这种想法,慢慢就形成了有性别排他性的群体。所以有些作品虽说没明着拒绝男性,但内容明显更迎合女性,强化这种性别联结。
湘江副刊:网络空间对于女性写作者意味着什么?是伍尔夫所说的“属于自己的房间”吗?女性网络文学写作的优势在何处?
许苗苗:网络空间确实给女性写作者——其实也包括所有被传统文学体制排除在外的人——打开了新天地。但就像前面说的,对那些专门写给女性、讨论鲜明女性话题的作品来说,网络就像提供了一个“自己的房间”——一个独立表达、相对平等的空间。女强(女性角色强大)文的平权想象,也可以看作伍尔夫“莎士比亚的妹妹”在网络时代的舞台。但商业化的女性写作,更像是一个更大的平台和机会,让写作能被更多人看到。
不过“女性作者”和“女频”的概念不完全重合。特别是新时代女性网络写作,现实题材增加,关注领域更开阔,突破了类型限定。另外这些年来作协的扶植引导,对精品创作的鼓励等措施,更注重选题和文学性,并不会刻意强调性别。
以前网络文学靠类型化连载收费,得拼字数拼更新量。这种模式对男作者更有利,因为拼体力嘛。女作者普遍更讲究文字质量,不太爱在篇幅上硬扛。到了新时代,网络文学开始强调精品化,改编成影视剧的机会也多了,这时候女作者的优势就显出来了——她们写的东西改剧本有优势,搞精品化创作也更拿手,这两点正好契合新时代网络文学发展趋势。
“大女主”是消费文化的产物
湘江副刊:女性故事常被认为是以浪漫爱情故事或家庭婚姻故事为主,现在女频的核心叙事依然是言情吗?当下的言情有什么新变化?
许苗苗:言情在女频里还是主流,这可能也和女性本身情感更细腻有关系。但现在故事线拓展了,不像以前那么“死磕”感情线了。比如古代背景的有写破案的、当厨娘的,现代的也有展现女性在各种行业里拼搏的故事。虽然多少还会带点言情线索,但男主变成配角,给女主当事业搭档或者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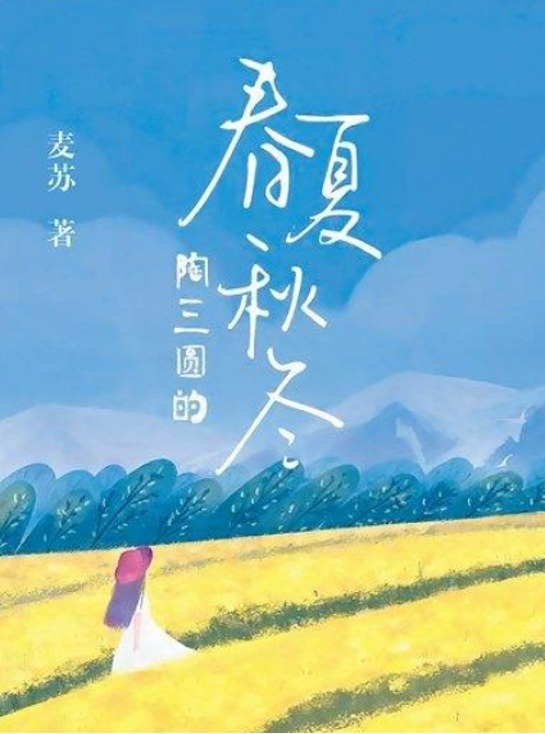
湘江副刊:在女性主义的浪潮下,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大女主”等词,伴随而来的还有鉴定“大女主”的“真”与“伪”,您如何看待?如何看待对“娇妻”的指责与对“爱女”簇拥?
许苗苗:网上发言挺容易情绪化的,有时候走极端。像说人家“娇妻”“婚驴”,我不认同。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提出“厌女”概念,网上又对应着冒出“爱女”的说法,去年晋江文学城的热文《女主对此感到厌烦》被看作“爱女文”代表。但其实这个概念并不清晰稳定,定义挺模糊的。
“大女主”说白了就是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想象和期待,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大女主”本质上是一个媒介和消费文化的概念。进入消费社会后,女性消费地位高,自然就冒出“大女主”这种迎合女性的形象。放到网络文学里,表现得更放飞、更极端一些,就有了女强、女尊这些类型。
现在网上对“真大女主”“伪大女主”的争论,大多是年轻读者带着情绪在辩,从学术角度看没太大意义。这些概念跟女性经济独立脱不开关系——要是没消费能力,谁会写“大女主”来讨好女性呢?
湘江副刊:很多女频作品被影视化改编,一些作品的人设和价值观在当时无争议,但是改编播出后却引起了很多争议,您如何看待?
许苗苗: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容易引发争议,说到底还是因为文字和影像压根是两码事。小说能用文字慢慢铺陈细节、深挖心理,但影视剧得靠强冲突、鲜明人设撑起来,就算网络文学本身人设够突出,文字里能写的细腻层次,镜头语言也未必能全说清楚。
而且两边的受众差异太大了:网络文学读者各有各的偏好点,可能冲着某个细节或人设追更,但影视化后得照顾大众口味,小众设定往往得改。比如天下归元的《凰权》《辞天骄》《女帝本色》等,原著都是女主更强,但改编的剧版最后还是往“男皇女后”的传统框架上靠了。
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开始往深处走
湘江副刊:您有印象深刻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角色和故事吗?
许苗苗:让人眼前一亮的女性角色不是那种从没见过的全新设定,而是在大家熟悉的类型里玩出新花样。
比如丁墨《乌云与皎月》的女主职业是网络文学作者,丁墨把自己和身边人的生活状态融进去了,人物塑造得特别可爱。长洱《天才基本法》,女主靠重生加奥数比赛改命,人设和剧情都挺新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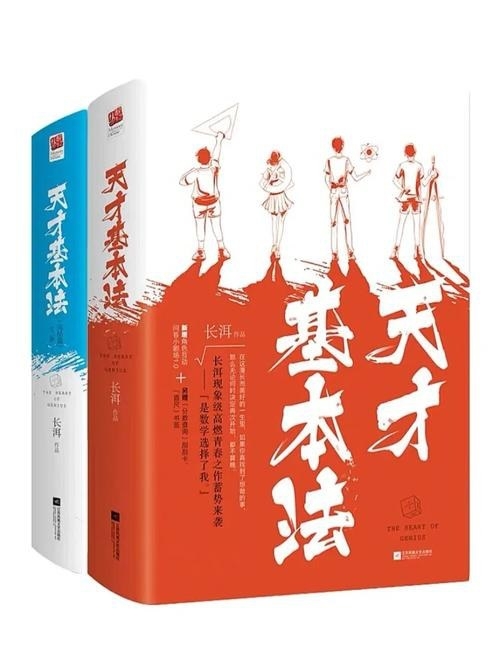
还有一些现实题材作品。比如麦苏《陶三圆的春夏秋冬》,胖乎乎、乐呵呵的乡村女孩陶三圆大专毕业后留在乡村当“家里蹲”,凭借稳扎稳打、从容不迫的努力,成为了最年轻的村委会副主任。她是个真实自然的乡村女孩,改变家乡面貌的动力来自于对亲人、伙伴的真实爱意,突出了个人与乡土命运的共生关系,这种将个人与养育环境紧密联系的写作方式在女性文学中具有代表性,说明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开始往深处走。清扬婉兮《有归》是一部描写未婚未育高收入女子老年生活的现实题材小说,描写出多样化的老年女性生存状态。现实题材要让读者看到自身阅历之外真实的人生经验,带来一种新的生命体验。女性作者比较敏感细腻,能够对当下关注的现象、容易引争议的话题给出多个视角的观察。
湘江副刊:以前女频流行的题材如宫斗和宅斗,现在没落了吗?
许苗苗:宫斗文这两年不算没落,但确实有变化。以前经典的像《后宫甄嬛传》,一群女的围着皇上转;后来出了《宫墙柳》,画风变成女性互助——皇上爱咋咋地,姐妹们互相帮衬着在宫里过日子,“岁月静好”。
宅斗文也分化了,好多跟悬疑言情或者基建文结合起来,成为展开故事叙述的手法之一。还有这两年流行的单元剧悬疑,像女仵作、女侦探、女杀手这类角色特别多,比如新出的《嘘,祝娘子她又在和尸体对话了》,写得还挺有意思的。
网络文学也要追求“真善美”的文学精神
湘江副刊:现在有些网络文学主角极端自私功利,您觉得弘扬真善美在网络文学中过时了吗?
许苗苗:真善美是永不过时的主题。之前有部作品创作手法优秀,但网上很多读者觉得不舒服——穿越到古代的主角确实冷静理智,丝毫没有“恋爱脑”,但这种为钱、为自保、为达目的牺牲他人的功利化做法我不认可。人生的美妙在于不确定性,而不是像穿越者一样走最短路径通关。文学本该给人全新的生命体验,而不是机械的选项。
湘江副刊:网络文学具有强烈的互动性,有时候可被视为作者与读者共创的文本,常以“爽”为要点,这是否会削弱作者的独立性和作品的文学性?
许苗苗:其实说到“爽文”,一般人先想到的都是男频那种打怪升级的路子,结构和逻辑都比较单一。女频里严格的“爽文”不算多,毕竟女性读者对情感更讲究细腻度。
互动性对网络写作确实有帮助。但成熟的作者不会被读者带着跑,作者动笔前就想清楚了“要讲啥故事,写给谁看”,只有那种短篇打赏定制的情况例外,比如知乎上有一类作者写作过程中会征集读者意见,比如问“女主和两男主,你们更喜欢哪一对?”然后根据读者意愿续写情节。这并不是被读者牵着走,想写好需要很高的人气和文字技巧,作者得有很强的控场能力才行。
互动性不会削弱作者的独立性和作品的文学性。既然选择在网上写,接受互动其实是件好事,能给作者提供更多思路,也多了和读者沟通的机会。好的作者愿意直面读者。
湘江副刊:您对女性作者的写作还有什么建议?
许苗苗:关于写作和形象塑造,我建议,想提升文学性就别老想着“我是女性作者,专门写给女性看”,毕竟伟大的文学从来不是为了迎合某类人。要是想走市场化路线,尤其是精准戳中小众网络读者的情绪点,那另说。但如果想成为出色的文学创作者,而不是单纯的文化产品生产者,就别被性别标签框住,可以突出女性独特的观察和感受力,但得让这成为优势,而不是限制。
应该为网络文学独立设立奖项
湘江副刊:目前学界重视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吗?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占比如何?
许苗苗:网络文学作为新兴现象,变化太快了,现在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有很多空白等着填补,特别欢迎年轻学者加入。在当下文学研究里,它占的分量不算重,但在网络文化里,它可是核心——毕竟影视剧改编、周边、二创这些,都是从网络文学故事开始的。所以研究网络文学得放到整个网络文艺的大框架里看。
现在学界把网络文学归到通俗文学里,觉得它偏商品化、取悦大众,对原创性要求没那么高。这不是说故事抄袭,而是手法创新,毕竟太新、太陌生、挑战大众审美就没法通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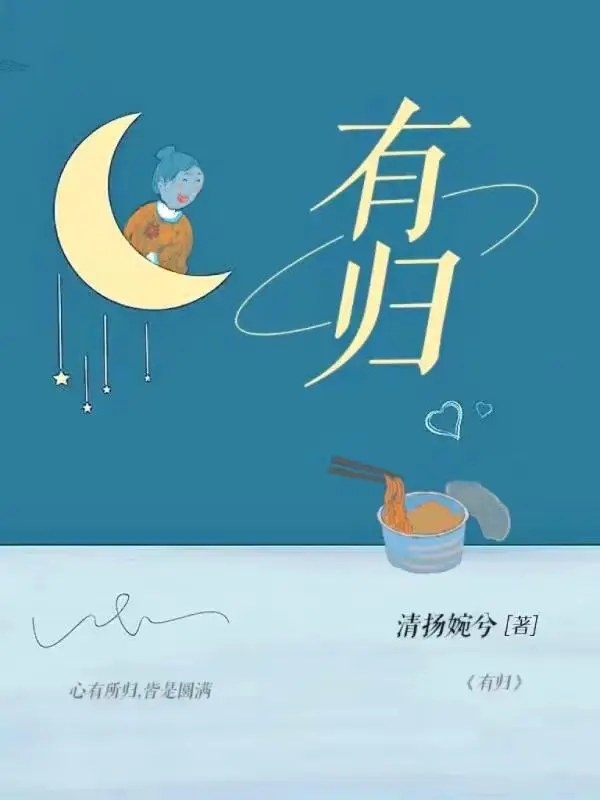
湘江副刊:现在很多传统文学奖项增设了网络文学赛道,评选标准和传统奖项有差异吗?网络文学应该独立设奖吗?
许苗苗:差异挺大的。比如茅盾文学新人奖更看重故事精彩度、社会影响力和传播力,而传统文学奖更关注作品的原创性、艺术创新和文学性。网络文学奖项确实需要单独设立,毕竟它和严肃文学是两码事,没法用同一套标准衡量。标准可以侧重这些:和当下生活的结合度、故事吸引力、社会影响力,还有媒介特性(比如互动性、衍生能力),不像传统文学只看文本本身。
湘江副刊:您之前提到要对网络文学开展交叉学科研究,还需要哪些学科介入?
许苗苗:目前从文学学科来的基本是当代文学和文艺学学者,除此之外,还需要媒介文化和传播学、文化产业等学者加入。特别是媒介的影响,对网络文学太重要了,比如创作过程中的互动、一部作品在网页和出书时的改名现象等,都和媒介特性有关,以前研究传统文学可没这么复杂。
责编:刘涛
一审:易禹琳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