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联 2025-05-19 15:13:24
艺评|张觅:红楼无限意——评潘向黎《人间红楼》
原创 张觅 湖南文联 2025年05月14日 17:13 湖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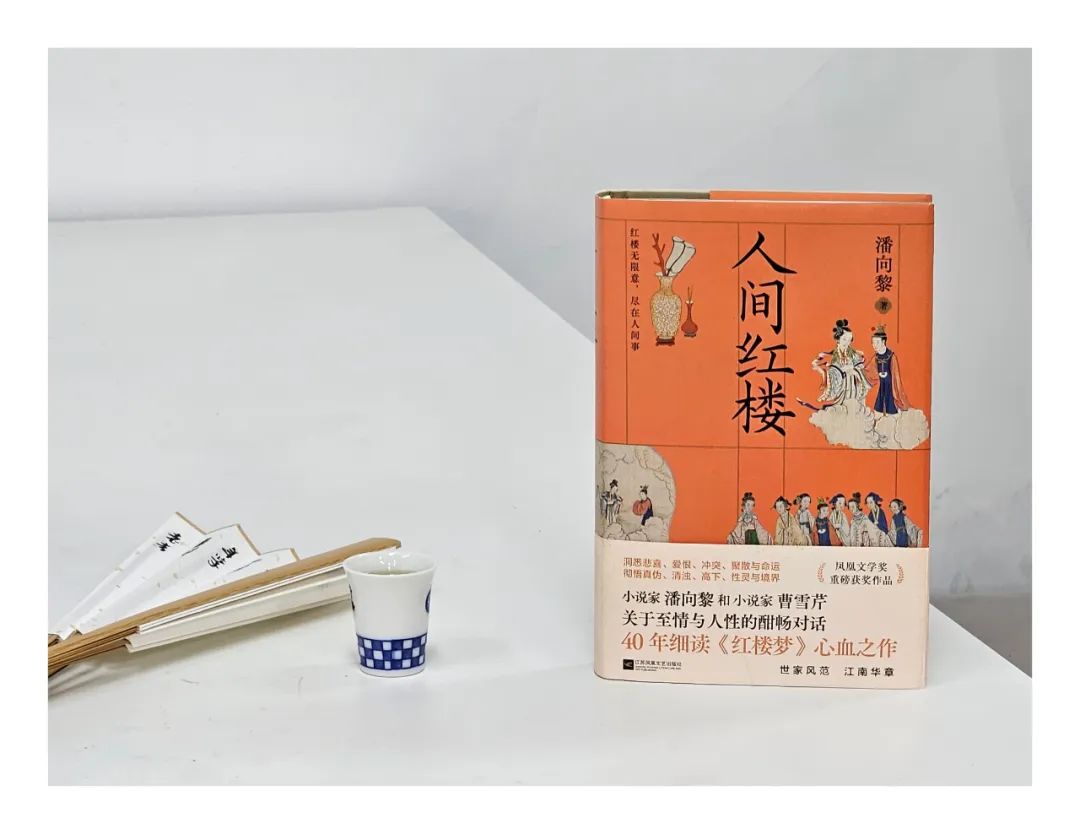
红楼无限意——评潘向黎《人间红楼》
文|张觅
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评论专著可谓是汗牛充栋,纪录片也不少,其中让人眼前一亮的却不多。而作家潘向黎的《人间红楼》,却是其中尤为光彩照人的一本。这本出版于2024年8月的书,仅四个月便印刷四次,并获了凤凰文学奖、2024年10月中国好书奖等诸多荣誉。我展卷读之,只觉颇有裨益,此书并非浪得虚名。
书中收录了潘向黎40年细读《红楼梦》的28篇赏鉴评论作品,共分为三辑,第一辑为“华年•情深情浅”,评论《红楼梦》中的情感;第二辑为“心眼•世事洞明”,评论《红楼梦》中的人性;第三辑为“天机•梦里梦外”,则是评论曹雪芹其人其事,以及红楼梦里的饮食、服饰及其他。作为小说家的潘向黎,她品评《红楼梦》的角度并非完全是学者的角度——尽管她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文学博士——她更多的是从性灵的角度、从感性的角度,以同样是小说家善感的心灵,来对《红楼梦》中的情感与人性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而非做各种考据和比较工作,令人阅读之时时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之乐,仿佛解疑了《红楼梦》中的情感谜团,解密了《红楼梦》中的人性密码。“好小说永远是贴着人物写的,伟大的小说更能丝丝入扣。”潜伏在《红楼梦》里幽微闪烁的光芒,被她敏锐地洞悉,准确地捕捉,并在书中做了审美化的呈现。书的腰封写道:“小说家潘向黎和小说家曹雪芹关于至情与人性的酣畅对话”,诚然如此,红楼无限意,尽在人间事。
这是一部满纸生辉之书,读起来丝毫没有枯燥与晦涩之感,语言更是如同山中溪涧一般生动活泼,便如她笔下所写,“胸中纯一团活泼泼的天机”,看到精妙之处,忍不住赞一声作者真是玲珑心璇玑轻巧思。潘向黎无意于掉书袋,而是带领读者走向了红楼深处,细细触摸曹雪芹的心灵世界,同时也是《红楼梦》的情感世界。潘向黎讲情讲得透彻,一针见血。她专门有一节,来论《红楼梦》中的钗黛之争,标题是“宝钗什么都有,黛玉只有眼泪”,看标题似乎是扬钗抑黛。但读下去,才知道是对黛玉的褒奖,以及深入分析宝玉倾心黛玉的原因。潘向黎指出,心灵和现实之间,感情和物质之间,曹雪芹坚定地站在心灵和感情这一边。潘向黎说:“曹雪芹不露声色、细细密密地写了宝钗多么懂事,多么周全,多么难得,宝钗拥有一切,但是宝钗和宝玉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她和他,曾经离得很近,但终究互相都不能走进对方的心里。两个并不相融的生命,宝钗拥有得再多,与宝玉有什么关系呢?”
我喜欢潘向黎对黛玉的品评,我认为她是懂得黛玉的。她写宝黛之间的默契与相知。黛玉一生的眼泪只为宝玉一人而流,在宝玉内心之中,这比尘世的一切都重要。“有了这份眼泪,足以让宝玉抵御此后人生所有的苦楚和人世间的所有荒凉。”她不停地为宝玉哭泣,其实她也不停地让宝玉欢笑。在对的人之间,“那能让你哭的人,才能让你真正的笑。”潘向黎写黛玉对妙玉的理解,也是十分到位。平日里黛玉对妙玉可谓谦和十分,被妙玉抢白也全然不放心上,在众人赏雪联诗时,宝玉去向妙玉乞梅时,黛玉不让人跟着,只说:“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这是因为她深知宝玉在妙玉心中的特殊地位。妙玉被身世和处境逼出来的别扭怪癖,同样心高气傲而寄人篱下的黛玉比别人更多一份怜惜,所以她待妙玉以敬重、欣赏、包容和温柔体贴。潘向黎说:“这才是黛玉的真面目。”
潘向黎对宝玉的评论也颇为独到。她认为宝玉最大的好处,在于他眼中有“人”,他识人的高下、清浊。他会脱离身份、等级、贫富、性别的标签去看人,而不会考虑现实利益与虚荣心。潘向黎认为,这是天生慧根,是心灵自由,是自我捍卫。在现实之中是价值观、审美与直觉的胜利。对比妙玉、黛玉、凤姐、鸳鸯对待刘姥姥,宝玉“这份不势利的纯良,是不容易的,弥足珍贵。”也是因为识人,宝玉才能多情而不滥情,因为他识得,像黛玉这样“奇”的女子,只有一个。潘向黎相当精准地圈出宝玉的深情之处,也一针见血地点出宝玉的薄情之处,即他的纨绔气,他的“局外人”态度,他的不负责任与避重就轻。对家族事业,他一切与己无关;他结交琪官,却在忠顺王府的人来要人时很快便出卖他;对金钏儿、晴雯这些女儿遭遇危难之时,他也没有求情和设法救助。
潘向黎的目光聚焦于宝黛身上,但也并未忽略其他人物。“《红楼梦》这本书是活的,就因为宝玉、黛玉、贾母、凤姐,直至平儿、晴雯、鸳鸯、小红,个个是活的,不同的人去和他们对话,他们会对你说出不同的话来。”她对袭人的评点不可谓不犀利,认为袭人耍心眼,是个小小野心家,关于她的半回都完全是一个大丫鬟企图控制主人的心机攻略。她对探春特别偏爱,“从贾探春到林徽因”一章,就对探春的困局加以思考,并将探春与林徽因进行比较,认为林徽因实现了探春的梦想:走出去,立一番事业。虽然过程艰难而曲折。书中还评论贾政对贾母的一片孝心,以及对宝玉的父爱;分析晴雯的活泼有生趣,也注意到她的无机心与不进取;解读香菱的单纯与良善,也批评她的头脑简单与逻辑粗暴……种种观点,均在平常人不甚注意的细微处用力,却往往翻出新意,令人醍醐灌顶,细细想来,却又无一不熨帖。
潘向黎对《红楼梦》极为熟稔,因此在谈到红楼种种时,均如数家珍,信手拈来,恍若云中漫步一般自在。我跟着她的笔调漫游红楼迷宫,莫名的就有种安心感。她认为大观园在南京又不在南京,是“一座位于南京上空的大花园”。因为写这本书是曹雪芹在追忆,而他最美好的回忆都在金陵。而《红楼梦》又不只是回望,它又充满了极具创世意义的想象和极具现代性的展望。“这样辽阔、恢弘、精微、空灵、痴心而变幻莫测、永恒而不停生长的世界,在回忆中建构起来,最初的原因是感情。最大的内驱力也是感情。”《红楼梦》中模糊又错乱的时间线,以及主要人物的年龄疑案,潘向黎亦自有看法,她认为这样奇特的时间流,不如说透露了曹雪芹重新规定时间的创世雄心。曹雪芹的心理时间,是情感主宰的内宇宙,其流逝速度是由曹雪芹说了算的。因为曹雪芹借黛玉之口说了,“我为我的心。”
潘向黎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情感与人性的层面,而是更深入到了审美的哲学层面。除了人物品评之外,她也津津乐道于书中的美食与服饰。她说:“《红楼梦》是无用之人写无用之人、无用之事的书,主打的就是一个无用。无用的人,无用的美,无用的眼泪,无用的心思、无用的相思、无用的雅致、无用的欢笑、无用的仪式和无用的趣味……满纸眼泪,满纸心灵,满纸伤痛和幻灭,也满纸尊贵、洁净与优美,满纸爱、自由和人生真味。无用而自由,无用而深情,无用而美,无用而深邃。”潘向黎认为,如果你把宝玉黛玉读进了心里,那么大观园也就时时刻刻在你心里。“读《红楼梦》的时候,它在你的面前,你在它的怀抱里;独步长路、穿越风雨的时候,它在你身上,在你背上。不,不是一个小小行囊,而是你身上长着的一对翅膀,小小的,隐形的,翅膀。随时张开,就会带你飞到风雨之上。”因潘向黎对《红楼梦》的珍爱与懂得,《红楼梦》中的审美情趣与性灵世界已经浸润到她的灵魂之中,给她以无限滋养。她也希望读者的心灵能同样获得滋养。
在读此书的时候,我能感到潘向黎对《红楼梦》的款款情深。唯其情深方成至文。潘向黎显然也读了很多红学书籍,在行文中有恰到好处的引用,但并不堆砌冗长。有的学者型作家的文字有学者的严谨,却失作家的趣味,而潘向黎是既得学者之博,又有作家之灵,因此下笔渊雅流美,令人齿颊留香,成就了《人间红楼》这一佳作。
责编:周听听
一审:周听听
二审:张马良
三审:周韬
来源:湖南文联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