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联 2025-05-19 15:0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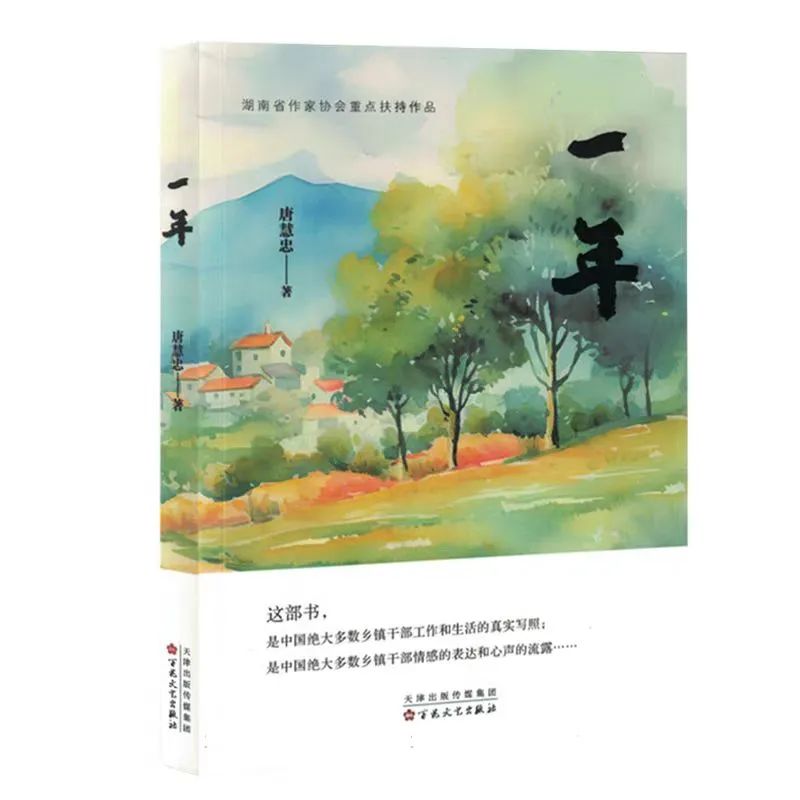
为乡镇工作把脉开方——读唐慧忠长篇小说《一年》
文|钟九胜
作为曾经长年在乡镇工作,对农业、农村、农民都非常熟悉的唐慧忠来说,用文字描写乡镇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举重若轻。长篇小说《一年》通过描绘主人公城关镇党委书记尹志刚在城关镇将近一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反映了乡镇干部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脱贫攻坚、扫黑除恶、计划生育、殡葬改革、信访维稳、反腐防贪等等,可谓历历在目。人物形象,如主人公尹志刚、“上访钉子户”何四岸、几进几出的“贫困户”何进水等,在各种矛盾冲突之中逐渐丰满,跃然纸上。
为基层工作“探脉”:一个 “难” 字
《一年》着重描写了乡镇干部这个集体群像,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基层工作的“难”。
这个“难”,首先体现在工作的繁琐。乡镇工作千头万绪,真是“上头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乡镇干部处在公务员队伍的最底层,他们的一举一动,直接关乎民生,关乎普通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认知,所以,大事小情,又不容出纰漏。对于各种防不胜防的突发情况,乡镇干部既“像个防火队员,哪里起火扑哪里;也像个浆纸工,哪里漏风补哪里”“乡镇干部是万金油,哪里需要哪里涂”。 他们“天天被琐事缠身,非常忙碌,从来没有哪个节假日能够让自己清闲自在地休息一天”。
基层工作的“难”,还体现在人心的复杂。屠夫何进水,收入可观,生活条件本来不错,尽管住的还是土坯房,那也只是因为他想修一栋全村最豪华的房子。这样一个“有钱人”,却因为个人的“小九九”,给自己投一票想要当贫困户,当了贫困户又坚决要退出贫困户,退出来以后,又想要再当贫困户。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惜向市检查组的曾组长“告御状”,害得镇干部因此受处分。乡镇干部直接打交道的是农民,农民有他们的生存法则,但近视和自私,是其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再加上人心不古、唯利是图的“时髦病”,干部工作的难度,不亚于登蜀道。
而以尹志刚为首的城关镇一班人,却吃苦在前,奋斗不息,努力当好“防火员”和“浆纸工”。当然,千难万难,趟过去就是好汉。乡镇是干部们的大熔炉,经过乡镇工作的历练,乡镇干部就成了一群“好汉”。
为乡镇工作之“难”查找病源
基层工作因为流于应付、大搞形式主义而“难”。小说第26章关于荒田复垦的描写,近乎闹剧。近百号干部带着记者去刘家坪村帮农民开荒复垦,“一是给领导看”“二是给群众看”“整个活动不到半小时”就“纷纷上了田埂,吃西瓜、喝水”“实际效果不大,宣传效果不小”,果然得到了县里的表扬。作品看似给主人公政绩贴金,实际上极具反讽意味。
基层工作因为“折腾”而“难”。关于殡葬改革,作品着重记叙了“三大战役”,在干部们圆满完成任务的背后,写满了“折腾”二字。土葬改火葬,本来就是某个领导心血来潮之举,“这项新布置的工作,实施之前没有考虑周全,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工作之中难免一些荒唐之举。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如果说传统的丧葬方式有一些违规的行为,加以规范与改正,是一定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的;可是一刀切的强硬措施,是不得民心的;而工作中的野蛮粗暴,更是把干部与群众置于尖锐的矛盾对立之中,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而这种损害,影响会相当深远。正像当年“乡镇干部在计划生育、催收农民粮款方面手段简单,方法粗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形成了定势思维”,以至于“基层政府和老百姓之间有什么事,矛头就指向乡镇干部”“这是在还历史的旧债”。
乡镇工作因为官僚主义而“难”。如市里下发的表格,要100%正确填写村民的个人收入这个有时连父母兄弟都不清楚的内容;如县里干部指挥村民种金银花、种西瓜来脱贫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如县委书记到广西考察回来,照搬照抄的殡葬改革;如香江市水污染事件对下游干部的处罚。特别是李志强那句“政治是不讲道理的”,是官僚主义者的标配。其实,政治是最讲道理的,它讲的是最大的道理——哲理。可是,官僚主义者只唯上,不动脑,懒政怠政,他们自己不懂道理,也不愿去弄懂道理,才认为政治是不讲道理的,他们自己做事“只做规定动作,没有自选动作”,让下面的人也“只有规定动作,没有自选动作”,这样,即便是一些利民便民的惠政,被这些官僚主义者一整也变了味,反而受到老百姓的批评和抵制。
基层工作“难”,也来自因基层干部抱怨升迁机制而产生的消极心理。一些勤恳干事、能力出众的人,往往只是“运气”不好,就升迁无望,甚至还会丢掉现有的乌纱帽。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好坏、职务升迁只能归结到“运气”二字,不是对那个工作环境、升迁机制的最大讽刺吗?城关镇农民网箱养的鱼被毒死,根源明明是上游水污染,受到处罚的却是城关镇和县里的干部,难怪钟益会感慨“只怪自己命运不好”,无奈之下提前退休。
治“难”的处方:健全法制为民生
法治社会,讲求的是民主,追求的是公平公正公开。上级政府推行的政策,会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老百姓有什么诉求,也往往事先做到有“理”有“据”。可是,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往往又不是某些规定能够一刀切的。于是乡镇干部们便像戴着“紧箍咒”的孙猴子,施展不开手脚。正如副乡长陈旗总结的那样:“上面的政策是钢圈,乡镇工作是橡皮圈。如果乡镇工作也像钢圈一样,不走形,不变样,没有一点弹性和回旋余地,那乡镇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在钢圈与橡皮圈之间如何做到游刃有余?作者开出的药方是“民生至上”。对于民生的重视,既应是乡镇干部工作的出发点,也应成为衡量其工作得失的一把尺子。
何四岸是一个老上访户,他感冒了,尹志刚自己掏腰包给老人去看病,这个“上访钉子户”意外死了,尹志刚没有半点幸灾乐祸;刘家坪村不通公路,村子成为全市的“三最”村(最贫困市里最贫困县的最贫困村),尹志刚想方设法帮村里筹集修路资金;为了社会的稳定,为了民众的利益,对黑恶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无情的打击;香江上游的污水排放,毒杀了城关镇老百姓养的鱼,城关镇 “按照市场价格,政府买单,对养殖户进行全额赔偿”,等等,作者笔下的乡镇干部,虽然因为工作的繁琐、责任的重大、百姓的不理解,而不免有一些牢骚,但是,他们有担当,能干事,会干事,千方百计完成上面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即便是身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干部,关键时刻他们还是会为了百姓的利益舍生忘死,如李铁前带头扑救山火而牺牲。因为民生至上,他们成为全国千千万万乡镇干部的缩影。
作者开出的另一个处方是:堵住法律的漏洞。 “刁民” 是什么?“刁民”就是善于钻法律空子的人。“刁民”不犯法,正因为这样,法律拿它没有一点办法;也因为这样,他们的过分诉求才“难”住了干部。
何四岸作为一个刑满释放者,居然打着抗美援朝英雄的幌子惹是生非,可从政府部门到社会舆论,居然没有追究、指责,反而采取姑息的态度,能将就就将就,拖一天是一天,最后竟靠其病故才“解决”问题。一个镇每年“用于信访维稳的工作经费,有几十万”。这是一种病态。老百姓有困难找政府,有事情去上访,本没有错。可不少人的上访完全是因为人性的恶在作怪。对于这种近乎病态的上访,作者开出了“信访终结机制”这么一个处方:“对那些重复上访户,可以由政府多个部门,比如说政法、公安、检察、法院、信访、乡镇等职能部门,还可以包括人大、政协、纪检等监察部门,组成一个‘信访终结机制’审理委员会,对某次信访事件做一个终极审理。凡是政府部门的责任,由该政府部门予以纠正并落实;凡是上访者本人的责任,由上访者负起该负的责任。这也是设计一个容错机制,终结审理之后,上访者如果再次非法上访,政府就给予重拳打击。”
不论是看病,还是开处方,都是需要深刻地思考和独到的见解的。正是因为这些思考,让《一年》这部作品的思想得到了升华,提高了其内在的价值。
责编:周听听
一审:周听听
二审:张马良
三审:周韬
来源:湖南文联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