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电波 版面责编 黄煌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5-05-16 10:17:00

文丨谭电波
中药的起源发展和我国的历史文化一样久远,中药既疗病也疗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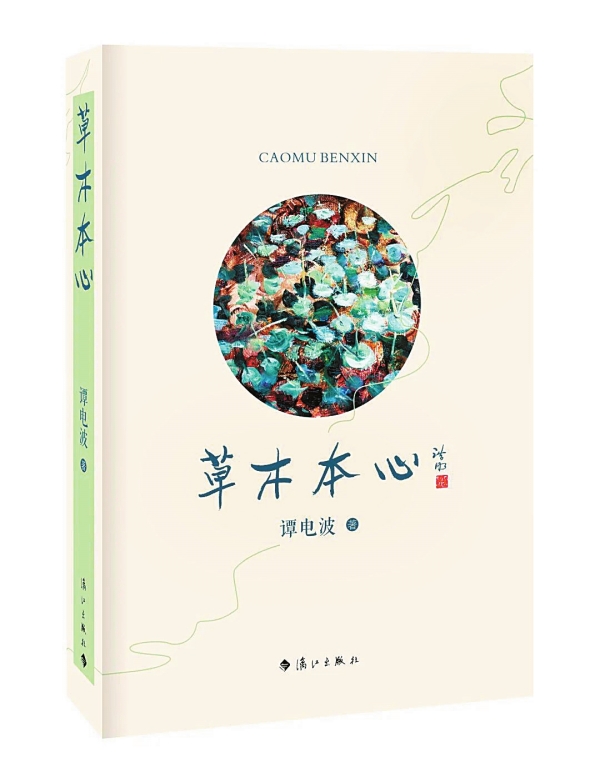
1
仅仅知道中药疗病是不够的,仅仅知道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药名是不够的。
我们与中药的距离,要远远大于人们与春天的距离。春雷一响,闪电一耀,人们与春天的距离,便只隔着一朵花,一场雨,一条丰盈的河。而人们与中药的距离却隔着无数个日夜、多年的泥泞,比如七叶一枝花需要漫长岁月的“慢煮细熬”,方可瓜熟蒂落。
如果说人在世间是一场又一场的邂逅,邂逅林中的雨、邂逅山边的风……那么,我与那些中草药又何尝不是一场又一场的邂逅。
2
说起来,我与中药相识也有50多年。在这不短的时光里,我认识它们:菊花、车前草、夏枯草、夏天无;我还认识它们:蝉、蚂蚱、蚂蚁、蟋蟀。秋天柿叶落光,柿子如灯笼般映红秋霞,我知道柿蒂是可以做药的;蟋蟀躲进了危墙里,把霜叫进了月光,而我知道蟋蟀是可以做药引的。
我写中药诗是出于对中药世界、对人世、对天地万物的膜拜。这世间不缺落叶和飞花,也不缺那声清鸣和叹息,我并无去饶舌的必要,这些诗,只是我对草本的呢喃。
我始终相信,一个地域的富饶与当地中药材品质有莫大的关系。一根人参就能够打开关于长白山的所有想象,它的沉默和高傲,忧伤和孤独,都是大地富饶的一部分。
中药不缺少阳光关照,风雨滋润与抚摸,它们深入万物内部,它们量过天高,量过地宽,量过水深。但我文字简陋,反而掩盖了中药之美。
3
中药,我赞美,用尽一生。我曾试图用一些现代种植栽培技术,为它们去挡风。然而,地道的中药材多半野生,自生自灭,甚至误入“歧途”。但其实,误入歧途的是人,我们一错再错。
很多人缺乏中药专业知识。但若不拘囿于文化意义上的交流,把药性视为人性,把药理视为事理,那么人即本草、本草即人。这也就是我认为“为什么写”高于“写什么”,“写什么”高于“怎么写”。
我写我的一时思索,也写半夜里的哽咽。
书写时,我交出耳朵、眼睛和良心,去观察、去理解我所处的草木世界以及肉眼之外的可能。试想,身边有多少我从未知晓的真实存在?又有多少我言之凿凿其实差之千里的所谓真相?
我下笔犹豫,时常戛然中断或突然反转。中药历史久远,文字发明之前,这些中药本草就存在了。也许,人类历史在浩瀚宇宙中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而诗说中药的意义也是虚无。
4
近10年,就我波澜不兴的人生来说,我吃了足够的苦,这也丰富了我的理性。诗、我、中药,三者互不掩饰,不担心谁来剥夺自由和尊严,这或许也是年老赋闲的宿命——简单纯粹。
若有美梦,我把它分成三份,一份给中药,一份给诗,一份给流水。到了小结一番的时刻,于是,就有了这本诗集。
缺乏感情,写作便成了轻浮、玩弄文字的游戏。上年纪之后,说得越来越简单朴素,但愿我能把中药说成白开水,把复杂的事,以及由此产生的感受,讲得明白简单朴素一些。
单纯即美。如同微笑。
本草世界那么美妙,让人感动。
责编:廖慧文
一审:周月桂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