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5-05-06 11:5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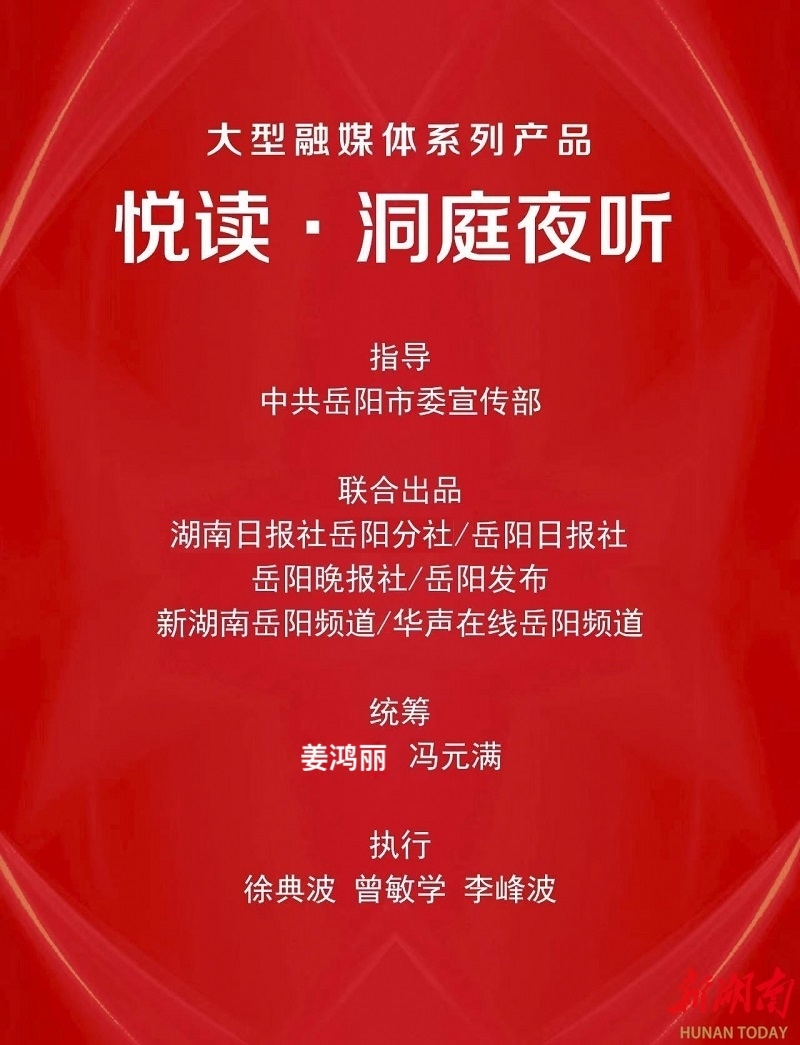
【开栏语】
一段美文、一首诗词、一个佳话。
像溪流拂过草叶,像厚重的石门被缓缓推开,像山峰拔节吱吱生长。
你听到的不只是空气的流动,还是一座城市、一方水土的书香氤氲,书声琅琅。
由中共岳阳市委宣传部指导,湖南日报社岳阳分社、岳阳日报社、新湖南客户端岳阳频道、华声在线岳阳频道、岳阳晚报社、岳阳发布倾情联手,全新推出“悦读·洞庭夜听”融媒体系列产品,讲述美好故事,温暖烟火人间。

【好声音】
【美文】
悦读·洞庭夜听。您好!今天和您分享作家王志龙的作品《我与巴金先生的一段奇缘》。
《海的梦》是巴金先生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在作品中巴老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背景,塑造了里娜——一位对自由与平等无限向往,对国家与民族无比忠诚的时代女性形象。她有着“星一般发光的头发,海一般深沉的眼睛,铃子一般清脆的声音”,犹如一束光照进了阴霾的天空。在精神领袖杨的感召下,里娜毅然投身于建立“自由国家”的革命洪流中,以柔弱的身躯承载起民族的希望。
写出这样的文学作品,巴老犹如擎起烈焰熊熊的火把,照亮了黑暗,温暖了人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真理而斗争,为正义而呐喊。重读这部小说,我和其他读者还有不一样的亲切感,那就是我和文坛泰斗巴老因此书的一段奇缘。
那是1991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封来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巴金全集》编辑组写来的,询问我是不是八十年代初收到过巴金先生写来的一封信。这让我太奇怪了,当时既没有现在这样无所不能的大数据分析,也没有如今的人脸指纹识别系统,他们怎么知道我给敬爱的巴老写过信,特别是还收到了巴老的亲笔回信。
这封函件一下把我拉回到1980年代。
尽管我当时是一个物理专业的理科生,但是却非常喜爱文学,不仅扑在学校图书馆里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还跟刘绍裳、从维熙、尤凤伟、戈悟觉、邓建永等作家有书来信往。特别是读巴金先生的《海的梦》,觉得这部小说非常适合搬上银幕,于是冒昧给巴老写信,希望能将《海的梦》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由于不知道巴老的地址,信便请《收获》杂志社转,因为巴老和靳以先生是《收获》的创办者,巴老也一直担任《收获》的主编。很快我就收到巴老的复信,告知小说已有吉林的一位同志在改编,但如你要尝试一下也不反对(见《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
那是一个理想与激情放飞的年月,也是一个纯洁与真诚的时代。我这样十八九岁的愣头青,居然不知天高地厚敢向名满天下的巴老写信,巴老礼贤下士竟然给我这个不足挂齿的小辈亲笔复信,这在今天可能是难以想象的。看看网上吧,巴老手书的一页信笺有人售出了万元以上的高价,即使一册巴老的签名书也拍卖到数千元。
开头我说同巴老的奇缘,奇就奇在我那时是以草菲的笔名给巴老写的信,而且这个笔名也仅仅用了这一次,以后发表文章从没用过了。特别是1982年7月从岳阳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我变换过四个工作单位,我本人也放下了当初狂热的文学爱好,一心一意执着于中学物理教学和教育研究。那么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金全集》编辑组的老师是如何找到我并且来信的呢?这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知道主持《巴金全集》编辑工作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大家王仰晨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的这封征集信落款署名编辑组,其实也就是王仰晨先生的亲笔信。在众多的巴金作品编辑中,王仰晨先生是巴金先生十分敬重的一位,正是由于他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热情相邀,巴金才同意出版《巴金全集》。《巴金书简:致王仰晨》一书,收录了巴金致王仰晨的三百多封信,足以证明两人之间六十多年的深厚友谊。
说到王仰晨先生,还应提到他的另一件轶事。王仰晨还曾做过《茅盾文集》的编辑工作,与茅盾先生也有着多年的交往。有一次,茅公在谈话中向他提起,自己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曾认识一位名叫王景云的同事,是当时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可惜,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王仰晨默默地听着茅公的讲述,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就是王景云的长子,不想把工作关系扩展到人情关系,他只愿踏踏实实地把编辑工作做好,做一个合格的编辑。什么是大家风范,王仰晨先生如此处世谦逊,行事低调,居功不傲,这就是大家风范的标杆。
为了将巴老给我的信收入全集,为了大海捞针般找到我这个籍籍无名者,不知王仰晨先生和编辑组的老师们千方百计、百计千方,费了多少力、吃了多少亏。他们这种苦心孤诣、恪尽职守的严谨、高度负责精神多么令人感动,这种甘为人作嫁衣裳,不留名更不谋利的编辑职业精神多么令人景仰!难怪连巴老都发自内心的赞誉王仰晨先生:“是你默默地在给我引路。”
巴老曾经说:“我们的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种传给别人。” 《巴金全集》煌煌二十六卷,书信集是其中的三卷,“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 《雾》《雨》《电》,还有《寒夜》《憩园》《还魂草》等众多的中短篇小说,都蕴含着对人性、社会、历史深刻的洞见。巴老把一颗“燃烧的心”捧给读者,给了千千万万 文学青年莫大的心灵滋养,巴老是几代人的人生导师,我就是读着巴老的作品成长的。巴老耄耋之年笔耕不辍,撰写了五卷《随想录》,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直言过去“太不重视个人权利,缺乏民主与法制”,尤其是痛定思痛后大声疾呼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国人猛醒。
回忆这段往事,让我深切缅怀敬爱的巴金先生,深切缅怀缘悭一面的王仰晨先生。巴老人品和文品的高度统一,既显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高度,又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作品的字里行间都闪耀着人格光辉。他常常说:“不要把我当作什么杰出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这种感情。”今天我不仅要继续读巴老的作品,更要学习巴老和王仰晨先生,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对正义良知葆有真诚信仰和悲悯大爱情怀的人。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对于这个人们经常问到的问题,巴金先生的回答是:“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光明。”先生还有更简单的一句话,“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巴老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文学巨擘,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他的文学始终站在最底层的、最弱小的人一边,有非常伟大的利他主义精神。老人家给我亲笔回信不正是体现了这一点么?
我深知自己轻贱如草芥,在人生旅途中,有幸遇到巴老、王老这样的大家名师,有如阳光普照,雨露滋润,让我平凡的岁月也能散发出些微的光芒,让我多少也铸就了几许士人风骨,更让我感到生活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绚烂、何等的欢愉!
您听到的文章,是作家王志龙的作品《我与巴金先生的一段奇缘》。
作家、编辑、读者,这三者共同编织了文学薪火相传的生态链。步入数字时代,这种互动模式更显珍贵,它呈现的是一种文明传承的范式:文学的价值不在喧嚣的追捧,而是代际的接力;文化的力量不在个体的闪耀,而是静默的播种。
当文学成为桥梁,文明的基因便在共读中流转,个体的孤独与挣扎,也消融于集体的精神原乡。文学,于是让人类变得更好,
讲述美好故事,温暖烟火人间。悦读·洞庭夜听,我是吴穷,感谢您的收听。

吴穷,岳阳市华容县职业中专高级讲师,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岳阳市中小学语言文字名师工作室团队成员。
朗读者/吴穷 音频制作/韩苗苗
作者简介:王志龙,昵称巴陵君,籍贯岳阳县,1961年生人,中学物理高级教师,省散文学会会员、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有散文、随笔、文艺评论若干散见于《文学报》《湘声报》《雨花》《书屋》《湘江文艺评论》等报刊,所著《法治的天空》一书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公开出版,并主编《千年名邑》《洞庭名郡》《巴陵戏史稿》等文史书刊十余部。
责编:王相辉
一审:吴天琦
二审:徐典波
三审:姜鸿丽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