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联 2025-04-30 11:17: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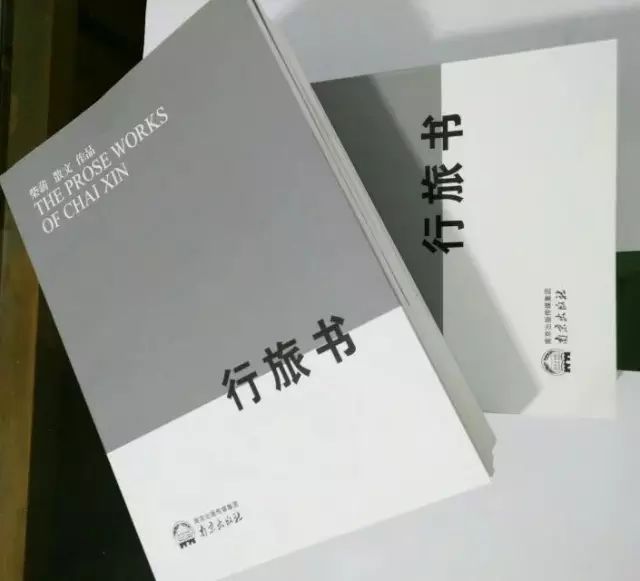
遥行千里 一路芬芳——读柴薪散文作品集《行旅书》
文 | 曾利华
多年来,作家柴薪将自觉地远行作为生存的一种方式,其足迹遍布新疆、青海、陕西、甘肃、四川、山西、重庆、内蒙古、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名山大川、草原戈壁乃至荒漠。《行旅书》中收录的108篇计16万字的散文作品,真实记录了其行走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每一篇作品,都散发出迷人的芬芳,捧读,令人爱不释手,回味无穷。
美景前的诗意叙述
语言,是文学的外衣,亦是评判作品好坏的直观标准之一。文字,则是架构语言的基石,关乎意境,关乎情感,也关乎思想。用最简单的文字,营造出唯美深远的意境,表达炽热强烈的情感,是增强散文吸引力的必然手段。柴薪驾驭文字的能力,似乎与生俱来,他的散文,文字诗意盎然,空灵唯美,活色生香。柴薪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那些看似简单的文字,便是他手中的道具,通过精心编排组合,文章的语言,瞬间芳香四溢,意境也更为深远。他写春风写秋阳写黄昏写芦苇,超出了常人的想象,令人眼前一亮。“春天来了,风细了,瘦了,圆了,长了。丝丝地吹着,若有若无,仿佛来自灵魂的缝隙。”“秋阳下,梁山愈发平静且透出深沉,行走在梁山的古栈道上,我像一剪被阳光剪辑过的孤影,渐渐融入其中。”“秋天的太阳跌到了江的那一边,黄昏,像一株植物在江面上生长……”“若是在早上,它们的叶尖,就会像刺刀一样,挑着晶亮的露水,让每一个经过芦苇丛的人,脖子里感到一阵阵的沁凉。”
行走中的深度思辨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纪红建曾说过:必须理性地认识到,行走固然重要,但行走的广度与深度,不是取决于作家走多远,而是取决于作家认识与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或者叫思辨。柴薪是行旅者,也是思辨家,他曾坦言:“我只是想在行走的过程中,获得一些与他人不同的思想。”因而,在他的眼里,山,水,路,桥,古树,村庄,河流,瀑布,白云,草原,荒漠,寺庙、野茔,等等,都不仅仅是简单的事物呈现,他更注重透过这些事物的外在表象,进行自我发问,开展深层次的思考,从而提升了文章的思想深度。
譬如,面对一棵枫树,他会发问:人和人不一样,树与人会一样吗?当经过一个铁路小站时,他会反问:前方一定还有无数个和这个一样的小站,而人生的旅途,不就是由无数个小站组成吗?在《树篱围绕的小房子》中,他写道:“比如围墙挡住了一些危险,也挡住了一些善意。”“人的心总是比人跑得远,有的人,他的心跑远了,那个人也跟着跑远了,再也不回来了!”“一切在时间中变得有价值的事物,最后还会在时间中变得一文不值。”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柴薪目睹遭受破坏的山山水水时,表现出一个作家应有的深深的忧虑,其流露的生态环保和生态危机思想,在《忧伤或忧郁的江河》《枯死的胡杨树》《残破的土塔》等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如果将这些散文划归生态散文,自然是毫无争议的。
回望时的情感表达
散文之美,何以触动人心?毋庸置疑,是以情动人。著名学者季羡林曾说: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柴薪的行走,并非信马由缰,而是有选择性的,他期望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个家园。然而,这种期望在现实中,却又是矛盾的。因为他纵马千里,终又系于一缰。这缰,便是柴薪无法割舍的乡情,亲情,友情。《行旅书》中,不仅记录了其行迹,而且字里行间,显露出真挚的情感。其中有对故乡的深深眷恋,有对亲情的无尽怀想,也有对童年的深情回望。
他以伞寄托对母亲的思念,母亲的一句“带上它,遮遮路上的风雨!”让他一生再也不会忘记带伞。当他远离故乡,坐在另一座城市的书房时,他想起了故乡的大樟树,想起了父亲说过的“倘不如意,还是回家吧!”于他而言,故乡的一条小河,一座水碓,一缕炊烟,一条黄狗,一些农具,一些人和陈年旧事,一点都没有流逝。而不管行走到哪里,他总不会忘记,自己是在江南的一个小镇长大。住在蒙古包里,听着外面的风雪呼叫,他会想起故乡的美景,故乡的山河。就如他在《像水花四溅的记忆》中写的那样:因为故乡小镇已渗入了我的骨髓,故乡小镇的意义,已缩小为我生命中的一个点,但是它又超出了一切!
责编:周听听
一审:周听听
二审:张马良
三审:周韬
来源:湖南文联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