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5-04-22 21:21:09
近日,湘西州青年作家欧阳文章散文集《湘西足履》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获得读者的广泛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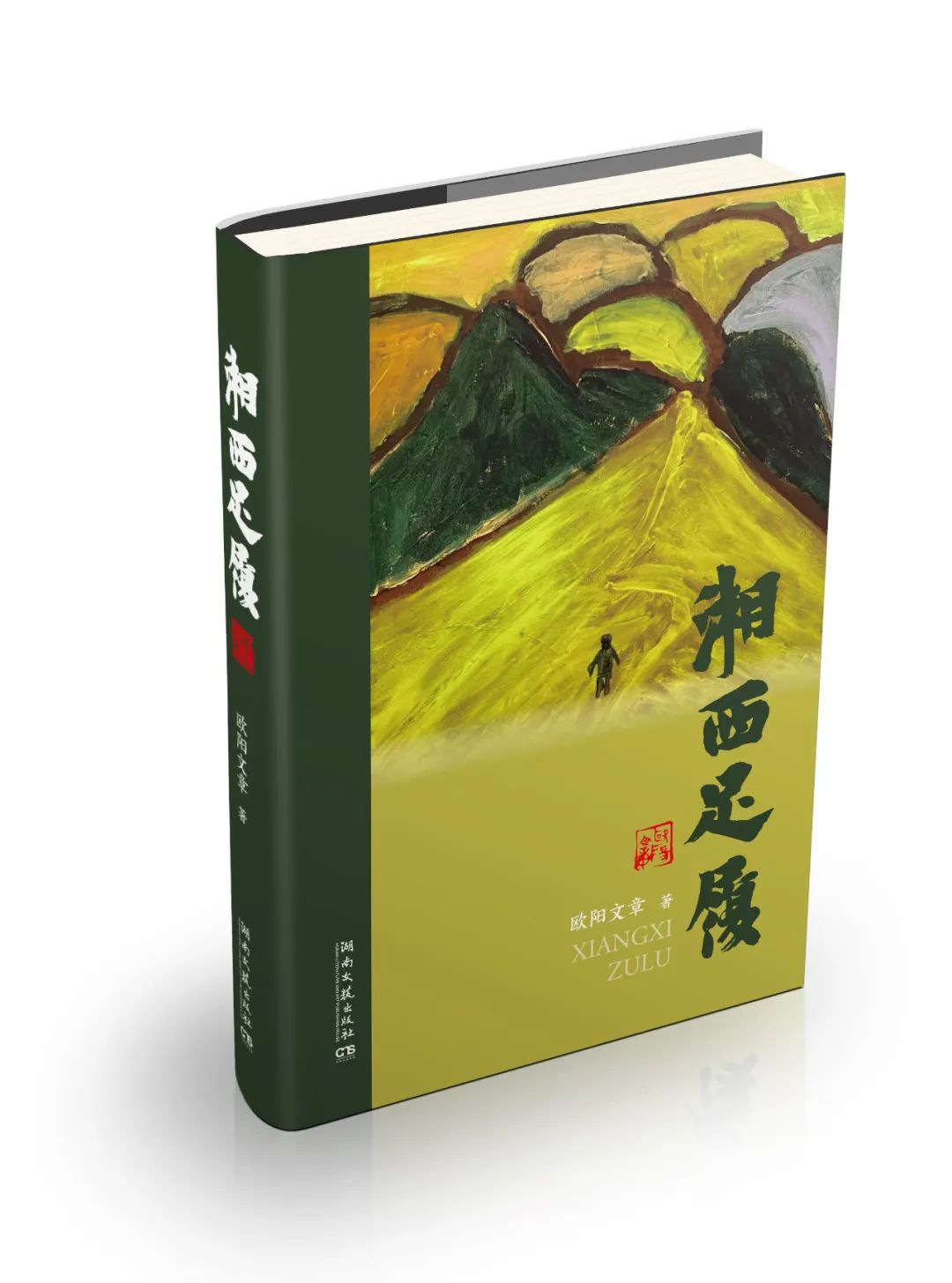
《湘西足履》一书收录了作者近年创作的40篇散文作品。全书分“山河、古镇、村庄、风物、人世”等五个篇章。作者以一个“外来者”的独特视角讲述在湘西走过的山河古镇、感受到的民俗风物、经历的人情往事,多维度展现湘西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人性温暖。该书得到龚曙光、蔡测海、张建永、刘年等国内知名作家、学者、诗人的推荐,称赞该书“不失为近年阅读湘西,体验历史的一本好书”。州内书法家田一烁为该书题写书名,青年画家刘云帆作封面,画家彭奎华作插图,书法家陈建平刻印,书法家陈振华书法设计,好友彭顺昌摄影,让《湘西足履》一书增添了浓浓的艺术品味。
作者介绍,在湘西24年,《湘西足履》一书既是作者行走湘西的足迹,更是他对湘西“第二故乡”的深情致敬。
作者简介

欧阳文章,湖南娄底人,19岁来湘西就读于吉首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在湘西工作至今,先后当过高中语文教师、党报记者,现就职于湘西州委网信办。在工作之余,他坚持文学创作,在《诗刊》《山花》《边疆文学》《文学界》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30余万字,湖南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他的访谈录《对话名家》(合著)、文艺评论集《湘西文艺汇评》、散文集《湘西足履》等多本著作。
【名家推荐语】
没有对湘西土地的生命楔入,断不会有如此深沉而慷慨、痛切而超迈的人性歌哭;没有与湘西文化的生死纠缠,断不会有如此专注而丰沛、朴拙而灵异的审美书写!
——龚曙光
欧阳文章,文如其名,会做文章。他将经历的湘西,一眼千年,一行千山。湘西的历史、现实,风景、风情,风物、风俗,在他笔下,行文有致。他写人物,写朋友,足见赤子之心。他对人对物,对自然和时间,温柔以待,善意的叙述。对所有著文者来说,对世界的善意是必须的。
——蔡测海
《湘西足履》一书文字情真意切,意蕴纵横捭阖,既有他者的独立眼光,又有自我的情感底蕴,既有湘西探幽之神韵,又有个体生命迎遇历史之快意,读来畅快淋漓,不失为近年阅读湘西,体验历史的一本好书。
——张建永
欧阳文章笔下的湘西,和沈从文忧伤的自我的以水为中心的阴柔的湘西不同,《湘西足履》里,我读到的是一个全景式的严谨而客观的山区的湘西,一个历史厚重而又充满了活泼的现代化生活气息的湘西,他的文字基调是质朴的、刚劲的、阳光的。
——刘年
【序言】
田茂军
学生当中,欧阳文章的名字取得好,易记。且因文笔出众,确实应了“人如其名”的说法。印象中,在吉首大学读书期间,他就是一位文学青年,是校园文学社的活跃分子,学校举办首届校园小说竞赛,他便获得一等奖,初露才华。毕业前,湘西文联主办的《神地》杂志“新世纪作家”栏目推出他的专栏作品,他的几篇短篇小说写得像模像样,展现出一位作家的良好潜质。当年,在吉首大学文学院,前后几届,泰然、林铁、永涛和文章,是我颇为看好的几位文学才俊。
大学毕业后,学生们大多天南地北,奔山赴海。文章作为一名外地人却留在了湘西,先在永顺一中从教,当高中语文老师,教出不少优秀学生,为人称道。后到团结报社工作,除写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外,更是写了大量文学作品,还做了一些大型文化活动策划,影响一时,成为大家公认的“名记”。现在到党政机关工作,同样干得出色。每到一个岗位,他都能做到得心应手,不得不说,角色的转换,难能可贵,这大概都得益于他对文学的热爱,练就了硬扎的“笔杆子”之功。
去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文章的《湘西文艺汇评》一书,获得大家的好评。今年,他的散文集又要出版,着实为他高兴。他的勤奋执着,令人钦佩。我一直关注他的文学创作,他的诗歌、散文、小说、评论都写得不错。最近这些年,他利用在报社工作的便利,几乎走遍了湘西的山山水水,写了不少散文作品,他把散文集的书名定为《湘西足履》,也就意味着,这部散文集聚焦的便是湘西这片土地。
湘西是一片文化热土。两千多年前,伟大的诗人屈原曾在湘西五溪一带行吟放歌,播撒浪漫主义的文学因子。百年前,沈从文先生通过《边城》《长河》《湘行散记》等经典著作,构筑了一个“湘西世界”,享誉世界。可以说,一代代湘西作家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表达湘西,建构他们所处时代的“湘西世界”,让湘西这片土地充融着文学艺术的独特魅力,也见证了时代的足迹。文章是当下湘西作家中的一员,也是一位湘西大地的忠实书写者。
相比较而言,作为在湘西工作的“异乡人”,文章对湘西的书写往往有着“他者”的独特视角,这使得他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能保持一定距离来“审视”湘西。他在文章中总有两个叙事者。一个是外叙事者,即作者本人。一个是内在叙事者,是作者的采访对象,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两种叙述视角,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我常常迷失和兴奋于对内在叙事者的历史探讨与密码猜想之中,与他一起去拜访那些历史的见证者。如《筸军的背影》中的陈启贵、《日暮亭子关》中的李祖兴、《舒家塘的密码》中的杨秀河、《最后的卫兵》中的杨光生,等等。文章在书写湘西的时候,自觉地将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避免了散文写作的单一化和平面感,这一点,是很多作家缺乏的。
文章散文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形式多变。他写了不少文化类型的散文,他的这类散文往往善于将文学的抒情和历史的反思融合到一起。比如,《沅水听涛》《遥远的距离——从沈从文故居到沈从文墓地》《巍巍南长城》《辰河突围》等作品,既有对历史的深情回望、理性思考,又有着源于当下情感共鸣引发的浓郁的抒情。历史与当下、理性与感性常常能很好地融为一体,使得这些文章充满文学诗性的力量,同时亦不乏理性的思考高度。《书中自有“史金玉”》《那些渐行渐远的伙伴》《别刘年》等这些写人记事的散文作品又呈现出另外的风格:简洁、洗练,往往通过白描的手法,来书写人情往事和生命痛感。《苗族银器:闪烁着月亮光泽的民族史诗》《毛古斯:歌接远古之音 舞抵癫狂之美》等作品,又有着新闻的纪实性和强烈的画面感,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特别让人意外的是,《王跃文先生话酒》《书痴杨云磊》《戒酒记》等作品,文言白话相互夹杂,诙谐幽默、活泼佻达、文气激荡,读之令人击节赞赏。从这些不断变化的散文表现形式中可以看出,文章在散文创作上一直在不断思考、尝试。可以说,《湘西足履》这部散文集,既是作者在湘西行走的“足履”,也是他在散文创作上不断探索的“足履”。
文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在《老屋》《我与孙健忠老师的三面之缘》中的几次流泪,让人动容。《别刘年》这篇文章,写了他和刘年的交往,早已成为圈内的佳话。他为人真诚友善,处事机敏而不迂腐,他谦虚谨慎的品行,更为大家所认可。我和文章交往二十余年,无话不说,亦师亦友。这篇序言,除了给他点赞,更多是一份师生情感“足履”的回顾与记录。
很喜欢这部散文集中《断章》这篇随感文章,摘录其中一段,送给文章,送给自己,也与读者共勉。
“骨子里安静了,才能从容,从容了,对这个世界就有了理解,有了包容。拥有了这些品性,再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便有了定力,便能静下心来做他所认定的有意义的事情,不再为世俗所扰。”(《断章》)
的确,生命需要从容,人生需要定力,世界需要理解!
读后感言,谨以为序。
【后记】
欧阳文章
弹指一挥间,在湘西已经二十四年,走过的路程,经历的爱恨,多半已经深埋于记忆的汪洋大海,倒是曾经用文字书写的这些东西,依然铿锵有力地把过往定格在那里,这或许就是文字的力量。我把这本散文集的书名定为《湘西足履》,便是想要用这本书记下我曾在这片土地上行走的足迹。这很重要,因为,这二十几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炙热的爱、奔腾的心、美好的青春,一切恍然如梦。人到中年,感觉什么都在走下坡路,越来越有苏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悲凉。这不是矫情,或许是写作者对时间、生命的敏感更甚于常人一些。
湘西,在世人眼里,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神秘的文化符号,人所皆知,也人所未知。百年前,湘西在世人的眼里,是蛮荒、“不受王化”之地。湘西的落洞花女、放蛊巫娘和赶尸匠更增添了其神秘和诡异的色彩。半个多世纪前,湘西在世人的印象里,则是“中国盲肠”和“土匪窝”。记得高中毕业那年,我要报考吉首大学,几个亲戚特意跑来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来湘西。可见,湘西被世人误解之深。好在,当年,年少的我,因为沉浸在沈从文先生的小说世界里,早已被湘西这“世外桃源”所迷醉。来湘西读书四年,且留在了湘西。如今,湘西于我而言,已成为情感深处的“第二故乡”。在湘西的这些年,一直不停歇地在这片土地上行走。特别在当记者的那几年,在《团结报》时任社长刘世树先生的主导下,我和报社的同仁们一起,策划或参与了“寻找湘西古村落”“走进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对话名家”“浦市寻梦”“神秘湘西 文化寻根”等一系列文化报道。一次次风尘仆仆的行走,带着对湘西文化的热爱,带着文化寻根的自觉,更带着一种想改变世人对湘西误解的强烈情绪,我们跋山涉水,与湘西风景相遇,与湘西文化碰撞,一篇篇湘西文化题材的散文作品便在这些行走过程中应运而生。这些文字,记录的湘西,既是一个美得令人心痛的地方,也是一个能让民族骄傲,给人荣耀,能让世人向往和敬重的神奇之地。所以,《湘西足履》这本散文集于我而言是对自己生命过往的一次回眸,更是对湘西这片土地的深情致敬。我想,大家读到书中湘西的长河、古镇,以及这里的风物、人情,必然会增添对湘西的好感与向往,这便是对我这个湘西书写者最大的褒奖。
写作是一份艰难的事业。于我而言,写作的最大困境就在于——明明知道目标就树在那里,却永远无法抵达。本质上,缺少生命的淬炼,便永远无法写出生命的真谛。拿散文写作来说,散文其实很难写,特别是书写文化题材的散文,如果文史材料用得过多,易成“文史体”。只停留在所见所闻,又会陷入“文旅体”。过于高高在上、装腔作势,一不小心成了“说教体”。太注重辞藻的流畅和结构逻辑的稳当,不觉间成了“作协体”。其实,真正的好散文应该有真诚的写作态度,应该遵循大道至简的规律,应该有充融的文学性和创造力,应该张扬生命的独特体验,应该传达对世界的深刻认知……这些对于散文写作的理解,我在《湘西足履》这部作品里做了诸多尝试与探索,但总体而言,远没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许,这是每一个写作者不得不面对的缺憾。我们的写作,和我们的行走一样,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前进,只能向前。《论语》有言:“往者不谏,来者可追”。诚然,《湘西足履》便是过往,我更渴望在写作上有一个崭新的自己。
感谢张建永、龚曙光、蔡测海、刘年四位我尊敬的师长为本书撰写推荐语,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感谢老师田茂军先生,交往二十多年,已成师友,更为亲人,他在序言中“毫不吝啬”的褒扬,显然带着浓浓的情分。人之一生,为人处世,都在修炼与成长,个人的缺陷、人性的弱点,都让人难以尽善尽美,前辈的包容与鼓舞,却是实打实的人间温暖。
特别邀请了青年画家刘云帆为我的散文集创作封面画,青年书法家田一铄题写书名,青年书法家陈建平刻印,青年画家彭奎华作插图,青年书法家陈振华题字,好友彭顺昌摄影,他们都是湘西文艺界的才俊,他们的作品为这本书增添了湘西元素,更见证了我们在湘西的情谊,在此一并致谢。
特别要感谢我的高中同学邓华,他为我这本书的出版奔走出力,令我感动。年少的时候,邓华也是一位狂热的文学爱好者,还曾获得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竞赛一等奖,是一位颇具潜质的青年作家。回想二十年前,我们刚刚大学毕业,他跑到湘西,和我一起徒步,行走湘西,我们到了花垣县茶洞镇,那是沈从文先生小说《边城》的原型地,三省交界处,清水江碧波荡漾,我们在河中畅游,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在吉首市德夯景区的天问台,我们爬上峰顶,两个懵懂少年对着崇山峻岭和漫山迷雾高声呼喊,仿佛与天对话。我们走过几个县市,最后,口袋里的钱用完了,我们只好坐火车逃票回家。多年过去,这些美好记忆和青春年华,或许一去不复返了——生命就是这般残酷!如今,邓华已走向经商的道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而我们也已人到中年。这本《湘西足履》里,或许就有我们一起行走过的路,一起在星空下互诉的衷肠,一起寻找过的“翠翠”,一起做过的文学梦,这的确是对逝去美好的一个温暖的慰藉!
宋人刘克庄在他的词作中写道:“少年自负凌云笔。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他对人生的书写简直残酷、真实到了极致,让人不忍卒读。
我更愿意相信:生命不息,行走不止。
是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走下去,好好走下去……
责编:封豪
一审:封豪
二审:王晗
三审:刘永涛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