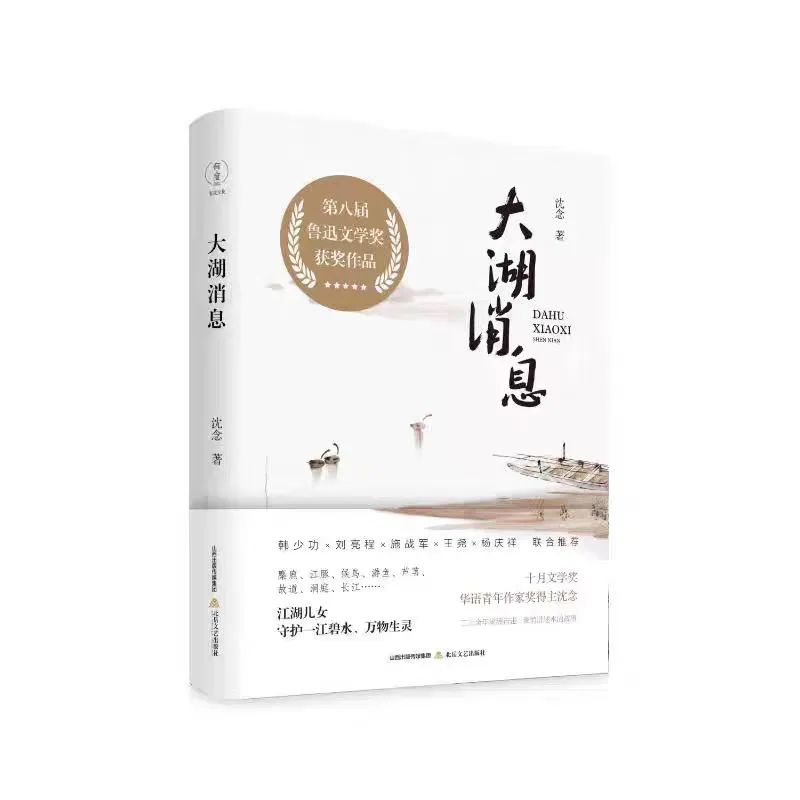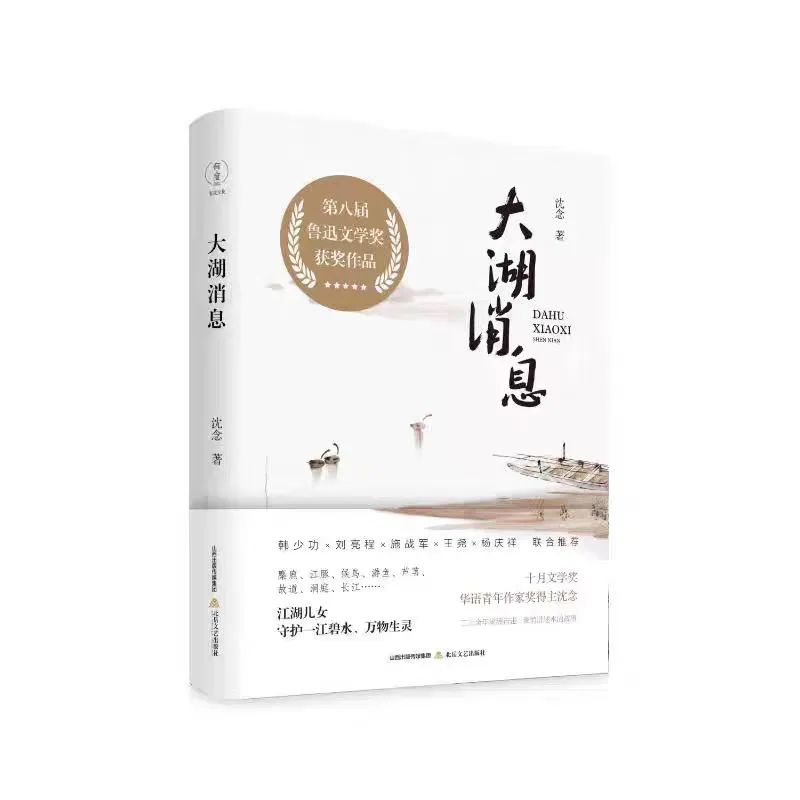艺评|崔雪悦:水中书——评《大湖消息》原创崔雪悦湖南文联2025年03月17日 12:00湖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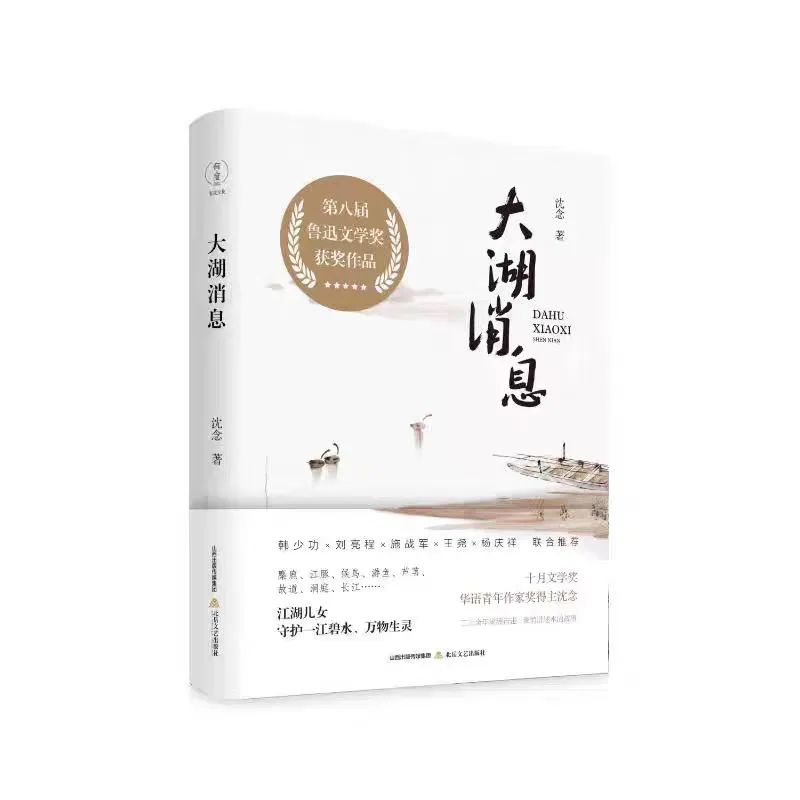
鸟的絮语、风和水的密谈,构成了洞庭湖的生态图景。顺着水流,作者一路追寻水的历史,当作者把笔触放置在水流中间,他的语言也像水一样,跟随着大地起伏流动,跟随着蓝天白云呼吸涨落。在作者笔下,世界上所有的水,都像人一样,具有记忆属性。作者从水的记忆中,考察伴水而生的人的历史、动物的历史,作者在文中说道“水里的人是不能离开水的”,揭示出人、动物和水的共生关系,何止是水里的人,水里的万千生灵都离不开水,洞庭的水在无形中滋养着这片土地,同时也塑造着这片土地。开篇,跟随着作者的视线,读者了解到洞庭湖的历史,站在长堤上,作者一再感叹,洞庭湖瘦了,尽管在《水经》《洞庭湖志》中,洞庭湖呈现给人们的,总是一副狰狞的面孔,它挟泥带沙,吞并着湖南的土地,万千百姓因为水灾流离失所。人定胜天,这是古代民众在面对残酷的自然时,发出的美好愿景,然而当人们借助科技的力量,真正实现了人定胜天时,留给人们的,却只剩下叹息,譬如作者笔下的洞庭湖。站在同一个空间里,通过阅读古籍,现代人或许能和古人遥遥对望,因而心有灵犀,写下相同的诗句。但站在不同的世纪,面对同一片湖水,和作者一样,读者只能在想象之中,还原出洞庭湖的原貌。那该是怎样一片水域呢,古籍里说“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到了作者笔下,洞庭湖已经瘦成了“几条分叉干涸的河流”。作者追问,是谁之过,答案也显而易见,是人之过。在物欲横流的年代,人心的欲望像一张大网,人心是不容易满足的,满足了温饱的需求,人们就想要更多,于是有了“围湖造田”,于是引进了一大批经济林木,洞庭湖年复一年地消瘦下去,再也不复当年的盛况。经济上的贪婪,催动着生长在洞庭湖周边的人们,有人带头,就有人效仿,于是人们纷纷入侵湿地,入侵湖水区域,仿佛这种经济上的成就能够带给人们莫大的满足。但真的是这样吗?在文中,作者提到“一个以水为生的人要怎么度过他的一生?”,没有了水,那些依水而生的人们又该如何呢?当人们双手握紧,什么也得不到,当人们把手松开,世界就在人们的手心间徐徐展开。于是有了人的撤退。欧美黑杨从泛滥成灾,到连根拔起,中间是无数人的努力,在科普宣传下,人们逐渐意识到黑杨对湿地造成的伤害,忍痛拔除黑杨,才有了慢慢恢复的水质。退耕退田,还林还水,村民需要付出多大的决心,才能走出故土,为湘水绕道,故都不再,但只要有水,一代一代的湘江儿女和洞庭儿女,会在这片土地上扎根,萌芽。从人的入侵到人的撤退,水的疆域在变化,人的生存空间也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只有滔滔不绝的江水,和伴水而生的万千生灵。在上篇中,几乎每个章节名称都是以动物命名的,起初,看着这些题目,读者会被作者引入一个“骗局”中,认为以动物为题目的每一章节,都是在写动物。其实作者不全是在写动物,作者是在写依水而生的万千生灵,在叙述这些生灵之时,作者也在讨论人、动物和水之间的关系。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好就是“从创伤到共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为了填饱肚子,总是需要将自己的生命,他者的生命,尤其是动物的生命,置之脑后,比起饿肚子,人们更愿意承受道德的审判,在面临血腥的尸体时,血淋淋的现实,饿肚子的现实更难令人接受。猎人老鹿,曾带领打鸟队,猎杀过一百八十七只白鹤;村民一点一点地侵袭洞庭湖,围湖造田,占领麋鹿的栖息地;老朱和许多同事,每天开着轮渡,机器的轰鸣声正在逐渐缩小江豚的生存空间。人、动物和水站在了自然界对立的两面,这种剑拔弩张的关系,使得三者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猎枪日渐磨损老朱的手掌;堆积的泥土减弱了洞庭湖调蓄洪水的能力;机器的轰鸣声不只影响了水里的生灵,也影响了老朱的身体健康。在这种关系下,人们越来越懂得和谐共生的道理。“只要人停止杀戮动物,给他们自由安定的空间,它们很快会忘记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血腥经历,而与人重归和睦。”动物是这样,水也是这样。当老鹿面对白鹤的哀鸣时,拿枪的双手无端地颤抖起来,他选择放下手中的枪,和心中的杀戮,救助受伤的白鹤,此后,白鹤和白鹤的后代一直盘旋在老鹿周围;当村民们从动物的栖息地中撤退时,越来越多的野生麋鹿、野生鸟类出现在洞庭湖水域,和人类共同享受水的恩赐;当老朱从机器的轰鸣中起身时,滔滔的江水就从老朱的身旁流过。人、动物和水,从创伤到共生,这期间,人在修补以前犯过的错误,大自然也在自我修补。看似是人在讲故事,其实是作为言说主体的水,在讲述人的历史,和动物的生命历程。作者说到“湖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和动物,其生命历程都是围绕水展开的。人的饮食、动物的饮食和洞庭湖水息息相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古老的俗语揭示了人和地域的关系,在洞庭湖生活的人,饮食习惯不免沾染上水的气息。大湖丰富的水生资源,赐予人们独特的美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洞庭湖的人,经常吃鱼,一年四季,鱼的身影总是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平日里,妇女们晾晒着黑背鲫鱼、翘白刁子,男人们喝着鲜嫩的鱼汤,过年的时候,年夜饭中的鱼,寄予了人们的美好期盼。大湖区域独特的气候,也在塑造人们的饮食习惯。大湖的水汽,总是在早晨和傍晚时,侵扰人的身体,于是依水而生的人们,选择喝两杯酒,拌着辣椒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驱除身体里的寒气。不只是人的饮食习惯,动物的饮食习惯也跟水息息相关。洞庭湖的麋鹿,喜欢吃特有的植物品种,狗牙根、芦苇、苔草、紫云英,江豚则喜欢二到三两的小鲫鱼、小鲤鱼,还有毛哈鱼等小鱼。在作者笔下,动物也有了自己的品位,它们会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对于其他常见的动植物,麋鹿和江豚往往不屑一顾。人的记忆、动物的记忆载体是水。“水认识所有人”,其实水认识所有的生灵。洞庭湖周围的人和动物,依托水而生,所以他们的记忆中,水无处不在。人的记忆依托水而生,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一首农民所作的诗,叫《哪里有路回故乡》。作诗的农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水域,洞庭湖水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离开洞庭湖,就相当于离开自己的根系。在诗中,这位老农民写到自己的悲哀,仿佛所有的记忆,都要跟随江水,一同逝去。动物的记忆也依托水而生,白鹤“飞飞”年年回到自己的栖息地,看望老鹿,江豚得知人类的善意,特意在捕鱼船周围晃悠。在作者笔下,洞庭湖是具有神性的,它会惩罚伤害自己的人们。在洞庭湖生活的生物也具有神性,白鹤会报答人的救命之恩,江豚会在阴雨天跃出水面,帮助渔民规避翻船的风险。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水的缘故,一切历史所无法言说的,就让水代替人们言说。责编:周听听
一审:周听听
二审:张马良
三审:周韬
来源:湖南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