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09 10:32:18
在可可西里更深处行走
——陈启文和他的最新力作《可可西里》访谈录
□张峥嵘
作家简介
陈启文,湖南临湘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文学创作一级。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大宋国士》、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中华水塔》《为什么是深圳》《中国饭碗》《血脉》《可可西里》《袁隆平全传》等30余部,作品翻译为英、法、德、俄、意大利等多语种在海外出版发行。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中国新闻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全国纪录片一等奖等奖项,2015年被国家水利部授予“水利文学创作特别贡献者”荣誉称号。

4月23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作家陈启文的长篇生态报告文学《可可西里》荣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该书是青海人民出版社和深圳出版社历经多年联手打造的重点出版物,是陈启文继长篇生态报告文学《中华水塔》之后的又一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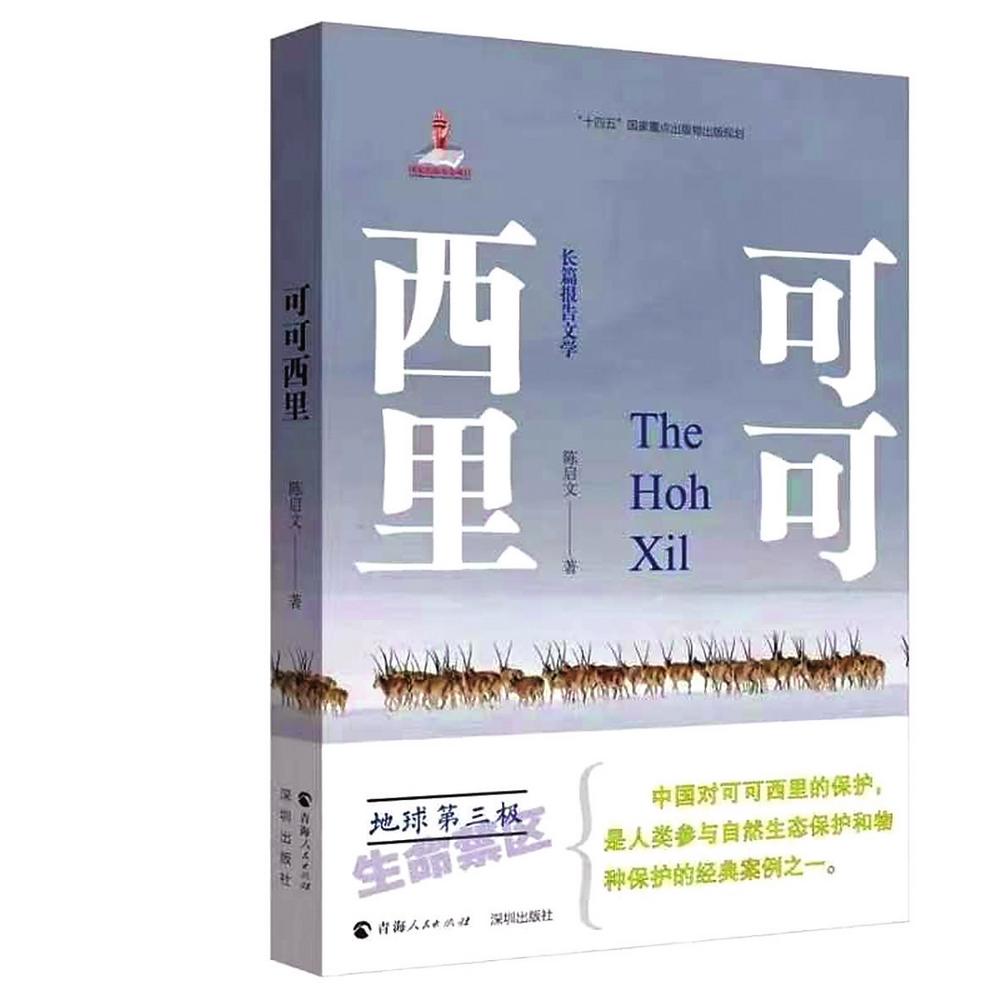
近日,陈启文携新书《可可西里》回到了家乡岳阳,举行了三场读者交流会。他向大家娓娓讲述了自己挑战生命极限、致敬生态文明的别样情怀和精彩故事。

一部致敬生态文明之书
可可西里,在蒙古语中意为“美丽的少女”,在藏语中意为“北部昆仑下那片荒凉的土地”。这是横跨青海、新疆、西藏三省区之间的一块高山台地,为世界三大无人区之一,也是我国最后一块还保留着原始状态的自然王国,无论从面积还是海拔高度看,这里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荒原。
2017年7月7日,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青海可可西里经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同意,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2017年8月29日下午,可可西里保护区内的索南达杰保护站正式开通卫星通信固定站,标志着可可西里成为中国四大无人区中首个接入互联网的地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可可西里的环境,不可一语而论。这里有湛蓝的天空,有洁净的阳光,有泛着银光的雪山,有野生动物的奔跑……这里是多么寒冷,空气是多么的稀薄,天地是多么的辽阔,水是多么的缺乏,天气是多么的恶劣,这是意义多么重大而多么困难的保护。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作家陈启文六上江河之源昆仑山,三入秘境可可西里腹地,以对高原净土的饱满热爱和为时代立传的责任感,调动全部的激情和才华,写就了报告文学《可可西里》,为所有人揭开了神秘可可西里的冰山一角。
这部作品生动地描写可可西里的生态面貌,直观地反映可可西里苍凉、博大、雄浑、神奇的地貌带给人的震撼;详细地记录了可可西里特殊生态环境下的生物和物产资源,揭示了可可西里高原野生动植物基因库的生态价值。它既是一部致敬生态文明之书,也是一部礼赞可可西里坚守精神之书。

挑战生命极限的采访
陈启文以其坚强的意志力,几次前往高原,前往无人区,获取关于可可西里的第一手资料,这是重大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体现。
说到整个过程,很多事没有亲身体验,根本触不到皮毛。就像,我曾去过可可西里,也只是去过一样,仅仅路过,那是观风者。只有深入的交流,深入地探寻,才会有深入的认识与思虑,有深刻的反思。
陈启文谈到采访过程,仍然难抑自己内心的情绪。他说:“这本书是我采写时间跨度最长、难度最大的一部作品。”
当初,陈启文只想依据时间和可可西里保护的重要节点,找到合适的讲述者,用他们的工作故事、情感故事,也就是生命中最具艰险也最富有光彩的故事,延展出一部可可西里的当代治理史。但在追踪采访的过程中,他一直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视角,逐渐形成了越来越清晰的系统生态观。
2017年8月,陈启文第一次奔赴可可西里采访,青海人民出版社派出了曾在青藏高原当过汽车兵的沈师傅开车,还有年轻编辑小赵作为采访的助手。
那天凌晨四点多,在高原的寒光闪烁的星空下自格尔木出发,从昆仑山到唐古拉山,由北向南纵贯可可西里保护区,沿途采访了不冻泉、索南达杰、五道梁、沱沱河等四座可可西里保护站,最终抵达位于唐古拉山镇沱沱河沿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
抵达沱沱河时,天色已近黄昏,沱沱河保护站的两个小伙子二话不说,就带着他们奔向六十多公里外的长江源头。那是可可西里最温暖的季节,在夕阳的映照下冰寒刺骨。沈师傅、小赵和那两个小伙子都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但他们和陈启文一样都出现了剧烈的高原反应,一个个冷得瑟瑟发抖。
在这高寒缺氧的地方没有人敢留宿的,只得连夜赶回格尔木。途中,他们又累又饿,在经过索南达杰保护站时看见了灯光,这也是无边黑暗中唯一的一线光亮过来。多亏有几个馒头撑着,他们才能继续连夜赶路。回到格尔木时,已是翌日凌晨五点。
“这二十四小时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漫长的一天,对于沈师傅也是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在平均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连续驱车一千多公里,蹚过一条条崩塌的冻土层和泥浆翻滚的河流,终于把我们渡到了彼岸。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位当时已年近半百的老师傅是怎么挺过来的,我只记得下车时,腿脚都麻木得找不到一点感觉了。”陈启文说。
2020年8月,陈启文第二次奔赴可可西里进行补充采访,这次是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戴发旺陪同。他们在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租了一位牧民的越野车,由于连日暴雨,河流崩岸,道路泥泞,一路采访都不顺利。那位剽悍的牧民兄弟驾车就像骑马一样纵横奔突,让人提心吊胆,尽管一直不断提醒开慢一点,但在抵达五道梁后还是发生了车祸。还好,几个人都没有受伤,但也只能带着庆幸和遗憾提前结束了采访,返回格尔木。
2023年3月,可可西里还是冰天雪地,陈启文在老戴的陪同下乘绿皮火车穿越柴达木盆地,奔赴格尔木,对可可西里的保护者和长江源村进行了第三次采访。
三次采访,等于三次生死之关。不但遭遇了许多难以预测的困难,还有一个难题,可可西里的保护者都特别低调也不善言辞,大多不愿接受采访。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可可西里管理处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可可西里管理处副主任罗延海的悉心安排下,一行人才终于得以完成这次采访。
是啊,这只是第三次采访结束,可采访可可西里是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记录与述说,是一本永远也不能划上句号的书。
再现自然保护区波澜起伏的历史
闻名于世的可可西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也是地质构造运动托起于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的一块高原台地。
说起来,很多人觉得入藏出藏经常经过,没什么了不起,可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背后,是无数保护者、治理者和建设者共同谱写而成的。我们都知道这是片荒野的人类生命禁区,又是野生动物自由生息繁衍的领地,很多人却不了解,这片自然保护区为地球生态气候调节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懂了这些背后的付出,背后的悲壮,再拿起《可可西里》这本书,认真阅读这部作品,才可清晰地感觉到,一股豪情、一种英雄气、一种奉献精神充溢在字里行间。那些读来令人泪涌、令人感慨、令人激动的细节、场景、人物,使得可可西里波澜起伏的历史,具有了动人的温度和力度。
此书最大的特点是,着墨于人,并没有像小说虚构一样去写可可西里的爱恨情仇。他用他最擅长的细节,最精准的采访,最宏大的角度,通过不同的人物,或者群像描写,渲染出可可西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从而凸显出在这片荒野进行巡护、守卫和守望工作的不易。无论是英雄索南达杰的形象、性格、思想,还是扎巴多杰和他的野牦牛队在政策法规尚未建立健全的特殊时间段,所处的尴尬而又必须勇往直前的境况,都带着一种撼人心魄的精神力量。
作家基于理性分析的共情力,唤起读者的共鸣。
与陈启文其他报告文学不同的是,《可可西里》是一部无人区的人物群像,再现了可可西里守护者一代又一代人的形象,这更是一部时代的赞歌,记录了国家对自然保护区的重大决策与投入。作品传达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勇气、信心和智慧。一批批巡护队员、森林公安,一个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志愿者,以他们的行动、精神,甚至生命,将曾经屡遭伤害的荒野逐步治愈,以他们的责任和爱心重新护卫可可西里栖居生灵的安宁。这是一个复杂、艰苦、漫长的斗争过程,也是一个从社会治理方面逐步趋于规范有效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广泛凝聚共识、转变观念的过程。
作品中,可可西里的自然要素和特点,规范管理的难点和痛点,以及引起人们疯狂掘金和盗捕盗猎的原因、规模及后果,都有着详细的描述。这些描述,绝对不是作者为写作而为之,而是深层次的观察与深层次的思考带来的记录与感慨,也是作者内心深具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的体现。
他以理性的分析透视这个生命禁区的今与昔,真实还原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万物生灵的珍稀,以及这里生态系统之于我国、之于世界的重要性,表现了作者大格局的人文关怀。
选择报告文学承载使命
这是一部致敬生命之书。这个生命是广义的,它超越了狭隘的人类意义,是一种辽阔而博大的生命。
陈启文写完《可可西里》并没有如释重负,相反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只是可可西里的一个匆匆过客,一直在这个世界的外部打转,而这里的守护者,都是用生命在经受、在体验这高寒极地的生存极限。
面对这伟大的荒原、野性的世界和英雄的群像,“我深感文字的苍白与无力。而对于可可西里的未来,我更是一头雾水。”
这也许是每个从可可西里归来者的感受吧。
一年后,我迎着南方的暖风站在洞庭湖边时,可可西里的冰川仍在眼前,我仿佛听到一种呼唤,一种来自大自然深处共振的声音,一种人类与大自然相互尊重的尊严。我只能通过陈启文《可可西里》这本书,往保护区更深处行走。
“我是一个写作者,我已不止一次说过,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一个职业虚构者。当我从不惑走进天命,我感到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选择了报告文学这一更直接的、更有承载力的文体,来承载我业已认定的使命。”
陈启文,17岁那年通过高考走进城市,又从湖乡城市岳阳走进大湘西的山城张家界,再到珠江三角洲的发达城市广州、东莞。这一切激起陈启文无法抑制的呐喊欲望,让他再也无法淡漠地看着一切去沉默。
认定了使命,是一种担当,但真正担起来,需要的元素太多。时间的跨越,距离的跨度,采访的艰难,角度的把握,撰写的定调。更要心中有秤,称出它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这是作家的力度,这是作品的价值。
责编:王相辉
一审:周磊
二审:徐典波
三审:刘永涛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