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腊生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客户端 2023-04-23 17:53:29
文/江腊生
阅读凌寒的小说《暗河》,是一种挑战。其中既需要有足够的耐力穿越生命流脉的阻隔,又不能缺失一定的理论储备来融化思辨的块垒,还建立在深刻的生命体验与情爱理解上。
《暗河》的阅读中,我感受到的是其中难以释去的生活压抑与情感重负,却又在暗长的命运之河中屡屡迎头遇见一丝生命之光。小说中每一个家族个体都处在暗黑的生命困境中,承受与挣扎透出生命的韧劲与热度。他们在世俗生活的追求中不断寻找超俗的生命价值,却又留连于日常生命的起伏。其中既有作家诗性的生命理解,又有思辨的生活超越。
整部小说的精华之处,不在于家族小说的历史勾勒,而在于每一个生命个体存在背后的那个暗影。这些暗影闪烁着的正是作家对人生与命运的理解与思考。作家往往在此长时间的驻足停留,将每一个暗影连结成一条无形的命运之河。
生命困境的承受与挣扎。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身处困境当中,不管有意无意的逃离,都无法走出他们的命运之井。每一个人物的困厄之井,连结汇聚成一条幽暗漫长的命运之河。小说没有具体去写真实的时代,而是透过一个家族历史的框架,讲述每一个体遭遇的生命困境。几乎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将自己关注一个黑暗的空间痛苦地思考的经历,他们在黑暗中不断承受,在孤独中不断挣扎。
祖父在一次暴雨中采摘野果子猝死在河水中,祖母将自己关在阴森森的黑屋子里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巨大的悲剧让她在往日的记忆中不停地辗转,最终一头栽倒在地上,完成了一生的命运交付。祖母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楚,又挣扎着延续家族的血脉。她中风后,房间、窗外、天上、整个村庄都笼罩在黑压压中,给人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感。母亲的倒下,病弱的伯父又很快的去世,父亲变得沉默寡言,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难。他也是将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独自思索着未来的出路。他不再能够继续读书,而是选择出去当兵,亲自上过战场,在你死我活的枪林弹雨中“立了功”,最终分配到文化馆上班。周梅兰生下两个孩子后,丈夫在工地上意外事故,失去了生命。她无助、哀嚎,一个人躲在房里,拿着一点可怜的赔款,“老天爷你让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她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干着别人嫌累不愿干的活儿,独自一人将家庭撑下去。不料女儿因为耽误了看病而成为哑巴,儿子整天在外面疯跑。遇到一个喜欢她的男人杜月生,却又因为处境艰难,门不当户不对而无法在一起。同样,乔慧因为父亲周文海的意外车祸,而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她倒在书房的地板上,沉沉睡去。母亲改嫁之后,她不得不匆匆嫁人,“拿起角落的掸帚掸去房里的灰尘”。苏文慧在遭遇与周文海的爱情失败后,嫁给了一个她并不真正相爱的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功利和家庭暴力,又让她最终选择离婚,带着两个孩子独自生活。她默默承受生活带给他的重负,并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思索女性的命运。
这些家族个体有一个共性的地方,那就是遭遇生活的困境,而不断陷于孤独之中。他们在孤独中承受命运的安排,也在孤独中挣扎着前行。孤独是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气质,也是小说带我们的一种独特氛围。父亲周千秋与母亲之间,既无法打破婚姻带给他们的压抑与痛苦,还得在世人面前维持一个貌似完整的家庭。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空间里,又活在各自的生命空间。孤独既是世俗空间之中的无奈,也是他们哲学意义的存在。我与柳青的热恋之后,选择了独自一人生活,并在整理柳青去世后留下的文稿中找到生命的归宿。周梅兰在无法与杜月生走在一起之后,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在乡下生活。几乎每个生命个体都将自己关在一个黑压压的房子里,独自面对命运的安排,以填补人物内心的孤独空间。这些个体一方任由命运之手的安排,在日常的河流中寻找生活的出路,另一方面又往往将自己置于孤独的世界,将生命的思索上升到存在主义意义的层面。
在书写这个家族个体的孤独气质的同时,小说底层还涌动着一股生命的暖流。那就是温情的渴望与追求。当年流浪的祖父,两眼发黑,饥饿无力。祖母拿出大女儿出嫁换来的一点米,熬了碗稀粥让这个素不相识的外乡人喝下。祖父喝完拿起一只玉米剥了起来。在他剥玉米的时候,头顶阳光,像火苗窜入她的眼睛,窜入她的嘴唇。阳光、火苗既是一种人间的温暖,又是二人的情爱,在乱世之中支撑二人的生存,也成就了整个家族血脉的延续。周梅兰落难之时,杜月生从中相助,帮助患病的女儿到处找寻医生治病,并在生活中给予全面的帮助。苏文慧与丈夫的婚姻处于飘摇之中,周文海难忘旧情,前往帮助她走出困境。二人的旧情依旧灼人。这些人间弥足珍贵的爱与温情,缓缓流动在艰难日常生活的地层,化解了命运带给他们的困厄与痛苦,而构成了生命的希望。小说正是因为孤独与爱,黑暗与光亮、压抑与追求等相互融合,构成了文本内部难得的美学张力,让读者既有一种阅读的紧张感,又在其中得到温馨的慰藉。
世俗与超俗的命运逡巡。小说人物的生命追求,总是处于世俗生活与超俗境界之间的犹疑与困惑之间,任由命运之手的操控。这些个体一方面沉入世俗生活的底层,任由生活的浪花的拍打而上下浮沉。在日常的世俗世界中,他们追求生活的物质、欲望、财富,甚至是生存本身。父亲在其母亲倒下,大伯去世之后,独自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庭。为了生活,他种地、去当兵,冒着生命危险去上战场,最后侥幸活着复原归乡,并安排了工作。他在文化馆里会拉二胡、吹口琴,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他取了一个目不识丁的母亲,却又喜欢上一个艳俗的女人“杏枝”。在世俗的目光下,他一方面与娇艳的杏枝保持关系,享受着杏枝给他带来的轻松与热度,一方面又与自己的妻子维持破碎的婚姻关系,甚至留恋家庭的温暖与安静。他沉沦于世俗的生命世界,又带着超俗的生命力去寻找自己的空间。在这里,作家没有用世俗的道德话语去谴责父亲的婚外出轨,或者书写父亲的忏悔;也没有用纯粹的女性主义视角去张扬母亲的个性追求,或者表现母亲的软弱,而是用一种矛盾的心态去走进这一对夫妻的日常生活,书写世俗婚姻的艰难与个体追求的悖反。
周文海在妹妹牺牲自己读书的机会后一路奋进而渴望有出息,却在大学里学的是哲学专业。生与死、灵与肉、存在与虚无一系列的问题,经常充斥在他的头脑中。爱慕已久的同学苏文慧一心要与周文海在一起,但他却越过哲学世界的思辨,与志同道合的苏文慧分道扬镳,选择去北方读研究生。毕业后,他选择了与护士叶海湄组建家庭,事业上如鱼得水,家庭中有儿有女,过上世俗而又温馨的日常生活。然而,他又有情不自禁地去看望多年未曾联系的苏文慧,在与其离婚后走上文学道路的交流中填补了精神层面的空缺。他一方面满足于世俗生活的丰裕,又寻找超越世俗的路径。他看到苏文慧与丈夫的紧张关系,鼓励其离婚,却又无法给苏文慧完整的家庭了,只能在文学与哲学间寻找生命的结合点。同样,在我和柳青之间,由于文学世界的情有独钟,二人相爱相知,柏拉图式的爱的力量、爱的温馨成为小说引向生命世界的存在。然而,柳青却选择了一个艳俗的女人结婚,生儿育女,最后却又毫无预兆地跳进了一条河里,孤寂地一个人走了。命运之河的沉浮中,到底是追求世俗还是超俗,在作家笔下都是一种美的遗憾。
在父亲、周文海、柳青等个体身上,都处于一种世俗与超俗的撕裂状态中,他们一方面追求世俗生活的物质性、欲望性的一面,寻找生命存在的质感。另一方面又不断在孤独中极力穿透世俗生活的坚硬之处,走进自己生命的精神世界或超俗状态。二者相互撕扯,又存在一定的妥协,形成小说独特的精神张力。本质上,小说就在一个家族历史的建构中,既表达了时代话语与个体话语的相互融合,又体现了个体话语企图挣脱时代话语的努力。
同时,小说没有抽象地表达世俗与超俗的紧张与撕扯,而是通过不同个体的爱情对象选择,将其生动具体地置于欲望与精神、个体存在与价值飞升的迷惘与错位当中,孤独与痛苦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死亡则是体现超俗的决绝方式。于是整个小说呈现一种悲怆的氛围,笼罩在家族延续的暗河之中,具有了一定的存在主义思考的深度。
在小说叙事美学层面表现为家族生命的诗与思。小说在叙事艺术上打破传统家族叙事的节奏,而是以西方现代主义的叙述方式,融意识流、诗性叙事与哲学式的思辨等为一体,书写一个史诗般的长卷。作品通过对一个家族家族四代人物命运起伏的描述,以叙述者“我”视角以及一些碎片化的镜头,拼构成一条家族生命的幽暗长河。诗化的文本气质与哲学式的思辨相互融合,使文体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广博而苍凉的文体特质,耐人寻味。
比较而言,如果说《人世间》则是透过家族生活的变迁,意在关注家族以外的社会历史变迁,《暗河》则是一部聚焦家族内部生活与生命的史诗性叙述。《暗河》没有以小见大,从而企图折射一个国家民族的宏大命题,而是专注于个体生命内部,将其内在的生命史作为诗性的源头,书写一个家族个体的生命流动。家族历史的流动,并不在于情节的推进,而在于推进过程中,作家将目光投向每一个个体背后的缱绻。在他们的生活进程中,小说没有重在书写时代话语对他们的影响,而是走进他们的生命世界内部,书写他们在时代历史推进的节点时的驻留与困惑。于是,小说的情节得到了淡化,而家族个体的内心挣扎与撕扯感成为小说叙述的重点。作家没有在一个宏阔的历史图景中书写一个家族的生命轨迹,而是简笔勾勒人物的经历,相反,小说将重心放在人物不同时代经历背后的巨大投影,不断浓墨重彩地涂抹心理与现实的冲突与妥协,建构出一部独特的家族心灵史诗。冲突是一种生命突破压抑之后的韧劲,妥协却是世俗庸常无尽的悲凉。
同时,从文体形式上,小说除了通过意识流等大量的心理描写,还在叙述过程中插入一些诗性的意象叙述,直接打开了小说的叙述空间,呈现一个独特的小说世界。在写历经艰难之后的周梅兰老态中,作家将目光投向一头外祖母家耕作多年最终被宰杀的老牛。老牛与周梅兰的命运互为隐喻,形象地表现了生命世界的悲怆。“河,是万物的源头。蜿蜒的河流穿过沉睡的村庄,穿过死亡的幽谷,穿过斑斑驳驳田埂上,河岸边那些灰暗的无名之花,穿过一代又一代的恐惧和抵抗,穿过这爱与痛、这生的无奈和死的坚强,抵达归途。”小说大量这一类充满诗性的叙述,一方面为家族历史的叙述增添了许多柔软的想象,另一方面又直接将作家的理性思考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将艺术的空间做了诗性与理性的拓展,增加了小说叙述的厚度。
命运是人类一个宏大的命题,它既是个体日常生活中无法逃离的存在,也是人类欲望、爱情、生命价值等悲剧性的表现。每一个家族个体都在命运之手中陷入孤独、迷惘、困惑,甚至死亡。因此小说用了大量的思辨性的哲学话语,来表达这些个体不可操控的命运感。小说在家族叙述中,融入一些主观的思辨,并引用里尔克、伍尔夫、史铁生等文本中的思辨性句子,力图表现个体面对爱情、面对孤独、面对死亡时的生命沉思。在柳青死后,小说运用意识流的手法,融里尔克等人的思辨性语言,表达我和柳青之间爱的缠绵与幽怨。于是在家族叙述之后,大量关于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辨表达,为小说增加了人生命题的厚度与心理开掘的深度。
应该看到,小说一些地方在插入里尔克等作家文本中的思辨性语句中,并没有与个体命运思考真正契合起来,显得有些直接和生硬,缺乏美学的留白。我和柳青之间的叙述,由于插入太多的文本与心理流动,导致我的存在过于主观化,二人之间关于爱情、命运的表达缺乏足够性格逻辑,导致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并不凸显,柳青的跳河而死,我为柳青整理书稿的行为不够自然与畅达。同样,在周文海婚后去看望别离许久的苏文慧,二者之间重逢,直接演绎为一个哲学家与文学家的对话,缺失了人性中的欲望世界与情感世界的交锋与撕扯感。因此小说在追求思辨性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小说叙述的自然和生命呈现的丰富。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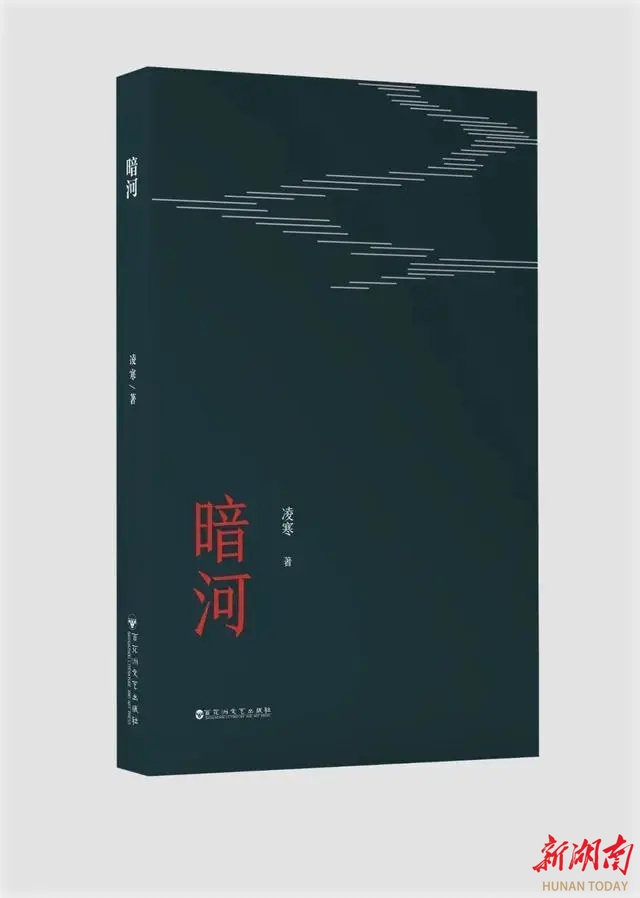
(凌寒,本名宋庆梅,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哲学教师。诗歌、散文、小说作品散见于《诗刊》《青年文学》《浙江诗人》《青岛文学》等期刊,已出版小说集《长夜将尽》、诗歌集《我从不悲凉之处寻觅》、长篇小说《暗河》等)
责编:李寒露
一审:李孟河
二审:莫成
三审:李寒露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