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10 12:25:37
古时候,糯稻一直优于普通稻米,早在先秦时期,糯米便已是中国南方的重要粮食。“诗经时代”的《周颂·丰年》中记载:“多黍多稌……为酒为醴”,这其中的稌(shǔ)米即糯米。
中国人被称为粒食之民,以“粮”为纲,要知道单独吞咽“粒食”,对咽喉和食道是个挑战,所以古人食必配饮,饭必有羹。人们还认为,所谓美食须“调以滑甘”。“滑”这个字,甚至被放在“甘”之前稻米里最滑的是“糯米”。
而糯米是糯稻的籽粒,乳白色,不透明,也有呈半透明。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是中国南方的重要粮食,在南方叫糯米,北方一般称之为江米。
舌头的选择是最不会骗人的,不管是爱吃甜还是咸,总少不了香甜软糯的一口“黏”。
其实,中国很多传统节日里都有糯米的身影:元宵、端午、冬至乃至民间酒席上的"八宝饭"……黏糊糊的它,总是能找到最合时宜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千姿百态。
不仅如此,在古代糯米还是建筑业的一分子,因为有它的参与,增加了楼房的强度和韧性,大名鼎鼎的北京故宫、明长城中,甚至地方上大户人家的祖墓,都有它的身影。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江南水乡——湘潭县易俗河镇踏龙村度过的。虽然地处鱼米之乡,但在那个"稻谷加稻草,年年要倒早"的年代里,有大米吃已是很不错了,糯米也就成了人们的稀罕之物,所以有糯米饭吃的时候,总是某些特殊的时候。
至今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湘潭县八中文科补习班复读,每月几元钱的菜金。一日三餐,不是一大盆冬瓜、南瓜,就是一大盆榨菜、海带开汤。繁重的学习,加之营养不足,每逢放月假回来,依旧是面黄肌瘦,气色不好。
母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记得有一次周末放假回家,母亲悄悄地在米框里匀出一些留作过年磨粉子做粑粑的糯米,用自煎的猪油炒了一锅糯米饭,趁大哥他们外出劳作的机会,让我饱餐了一顿。事后,我才知道,这乡下量米的老式"升子",一升米足足一斤八两,一顿狼吞虎咽下来,我竟然吃得连一点锅巴也没留下。
也许是中医认为,糯米“甘温补肺气,充胃津,助痘浆,暖水脏。”难怪老一辈的人都说吃糯米饭能让人中气十足,反正觉得那两天精神头儿都是棒棒的。
一年之间,每到秋收时节过后,母亲忙完了田里的农活,就会用自家刚收获的香糯来给我们做甜酒或糯米饭吃,记忆中的那个时节空气中总弥漫着浓浓的糯米清香。
若论清洁卫生,搭配合理,母亲的厨艺,在方圆十里算是出了名的。糯米蒸甜酒,早上再来个甜酒冲蛋,自是好吃极了,但工序复杂,而且受季节限制,所以最常吃到的还是糯米饭。当我带着央求的神情跟母亲说我想吃糯米饭的时候,她总会满足我的愿望。虽说从来都只是关心糯米饭做好了没有,从没太在意它的制作过程,但母亲制作糯米饭的程序现在居然记得清清楚楚,恍若昨日。首先,母亲会选自家种的上好香糯用水浸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沥干放入大铁锅中用猪油反复翻炒。选用肥瘦适中的猪肉剁碎,入锅炒熟爆香,然后选用颗粒饱满的红枣,品质上乘的桔饼切成的薄片倒入锅中加点盐翻炒均匀,最后洒上葱花,令人垂涎欲滴的糯米饭就做好了。白的米粒、红的枣、甜的桔饼以及青白相间的葱花,简单的食材却成就了我心中无上的美味。刚炒好的糯米饭太热只能用碗装着吃,常常一碗接着一碗,母亲常常在旁边提醒,”慢点吃、别烫着了“”别吃太多,撑着了不好受“”吃饱了别喝那么多水,糯米会胀出来,小心撑破了肚子“……那时候只专注吃,丝毫没有听到她的唠叨,但现在想来那唠叨那么的清晰。
记忆中的糯米饭就是如此的香甜和温暖,那是因为有了母亲呵护,也正是如此,我的青少年时代才会充满幸福的回忆。
考上大学后,参加了工作,后来又进了城。
糯米饭,糯米饭,糯米饭……
流动在街头巷尾的叫卖声像一抹暖阳般划开寒冬中凝固的空气,在湘潭这座千年古城缓缓地弥散开来。
虽然现在吃糯米饭已经很容易实现了,不过还是更怀念那时候的糯米饭,可能更值得珍惜吧。
文|楚国良
作者系湘潭市委党校退休干部,四级调研员。曾连续6年被评为《湘潭日报》优秀通讯员,其作品在《人民日报》《中国特产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县域经济报》《领导科学》等权威报刊上发表。先后主编或参编《晓霞之子》《今日梅林》《青山文史》《响塘文史》和《云湖文史》等多个乡镇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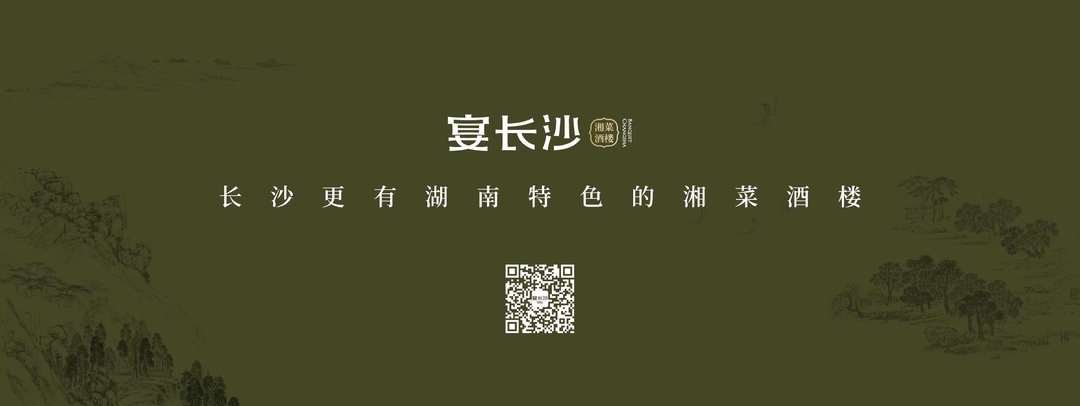
责编:蒋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