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论坛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2022-09-23 12:26:43
文/杨晓澜
文化知识全球化背景和当前快节奏阅读语境下,小说家们纷纷借鉴西方写作思想和叙事技巧,滑向文本创新和故事陷阱,却有一批中国作家始终创造性地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包括莫言、韩少功、阿城、贾平凹、张炜、迟子建、格非、何立伟等,他们用一个又一个传世作品,守护着中国传统小说的诗意、抒情、史传、言志和载道,守护着中国传统小说的语言、气血、情义、乐美和趣味。当然,以浓浓诗意和满满热情抒写民族地域生活的蔡测海,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从1982年发表小说《白云飘飘》《远处的伐木声》开始,到后面潜心建构的“三川半”系列,近四十年来,他一直守护着中国小说的传统,新作《地方》诗意生动,情义奔涌,“文学性”十足,饱含作者对湘西大地的无限热爱和对人文精神的终极追求,也给“地方性”和“历史性”书写,提供了更多阐述当下和回溯传统的可能。

一 诗意与情义的文学性坚守
评论家雷达先生曾言:“文学之日益与新闻、故事、报告、电视剧混为同伦而不能自拔,实属文学之大不幸。”当下创作环境,中国小说越来越成为故事的汇集和炫耀文本技巧的游戏,忘记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常识和精神。小说是什么?一部小说首先必须有小说的调性和异质,有足够的文学性,有独特的语言、文本、味道、基调,有丰厚的情感、细节、叙事、气韵。
一部作品如果语言有了诗的精练,叙事有了诗的节奏,人物有了诗的灵性,画面有了诗的内蕴,再怎么写,文学性也不会差。《地方》继承了一种古老的美,朴素的美,正在消逝的美。语言是诗意的。《地方》的文字唯美,含蓄绵密,富有哲理,一字一词一句,都经过反复的打磨锤炼,自然妥帖地安放着。“萤火虫怕这有星月的夜不够亮,把自己打扮成流星,把尾巴点亮。这个夜晚,有很多萤火虫的夜晚,是萤火虫大规模的爱情行动,它们放出一闪一闪的爱情语言。” “梵音领雪,先是一朵一朵地下,再是一团一团地下。路遮了,地盖了,树上挂满了雪,像一幢幢的雪帐。老虎,野猪,豺狼,一经染白,与白鸟争颜色。”“白马在崖上飞驰,它走过的是江湖,跑过的是界限。蹄踏过的是地方,飞跃的是高处。高低远近是白马的习俗。”此三处,寥寥数语,将星空下萤火虫的可爱、美妙,大山里雪花的纯洁、素雅,飞驰中白马的视野、经验,写得非常传神。叙述是诗意的。整体来看,《地方》是由62首短诗组成的一首长诗。62个章节的小标题诗意十足,如《阳光、歌谣、爱情和小虫》《当一条河成为一条河》《心踏雪》《猎日子》《盗名》等,仿佛一个个诗意莹然的珠子,作者巧手一弄,一串光彩夺目的项链就呈现在观众手中。“你一定会守在那里。”“漫天繁星,无比荣耀。”从第一章《守世》到最后一章《盗名》,叙述节奏极为舒缓,或长或短,或轻或重,或高或低,或急或缓,跟着山川自然、人物性格、湘楚故事,流水一样,徐徐倾泻着。河道有的一马平川,有的九曲回环,不管河道怎么变化,作者叙述的水流,总能道法自然,漫随河道,缓缓流淌。故事是诗意的。《地方》里的许多故事都具有朦胧的诗意和意犹未尽的味道。大山里的野人,朱家王朝和朱家花园,村长娘子雨的出走和归来,草药婆婆的秒术和四公公的斗笠,池塘里的蛙眼,三川半的河流与山洞,跳岩和桥,等等,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暗藏着更多悠远和幽微,令人憧憬,回味无穷。
小说除语言、故事、情节、人物,更应有饱满的情绪、真挚的情感、善良的情愫和担当的情怀。相对于时下流行的写阴暗、虚伪、暴力、血腥、破败、腐化、丑陋、荒芜、邪恶,《地方》更多地写明亮、真诚、宽容、温暖、新生、纯净、美好、繁荣、良善,小说对人的形象、人的关系、人的处境、人的心理、人的情境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丰富、到位,有情义、有能量、有担当、有亮色。作品的人物几乎都温暖善良,他们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守着湘西大山深处独有的素朴和纯真。杨二哥面对逃难的女人白翠花,给红薯给玉米,当对方提出以镯子换时,他说:“姑娘,我没见过玉,但我知道这是好东西……你觉得吃了亏,等你有饭吃了,你再取回去。” 饥荒年代,亦不乘人之危,不可不谓情义。草药婆婆给露治病,露提鸡蛋感谢;李克时走出大山后,情寄村庄, 建一〇八所希望学校。外来人,到三川半,落地生根,就是三川半人,知青也好,稻州来的女人也好,三川半人对所有的一切都满怀善意和友好。最为典型的是村长,村长说:“心里不长稗草,就不会有稗草。”在计划生育、阶级斗争、粮食生产等事情中,村长并没有照抄文件,使用强权,造成悲剧。向三妹违背计划生育政策,村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右派分子有小丁干不来重活,村长给他“特权”,让其写对联、念报纸、贴标语;为使城里来的学生缓解长居大山的寂寞,村长卖了村里的大肥猪,购买收音机,办起了广播站;每一个村民,每一份村事,都散发着村长来自心底的正直和温暖。万物有情,可以说,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条河流,每一棵树木,每一只动物,都满怀情义和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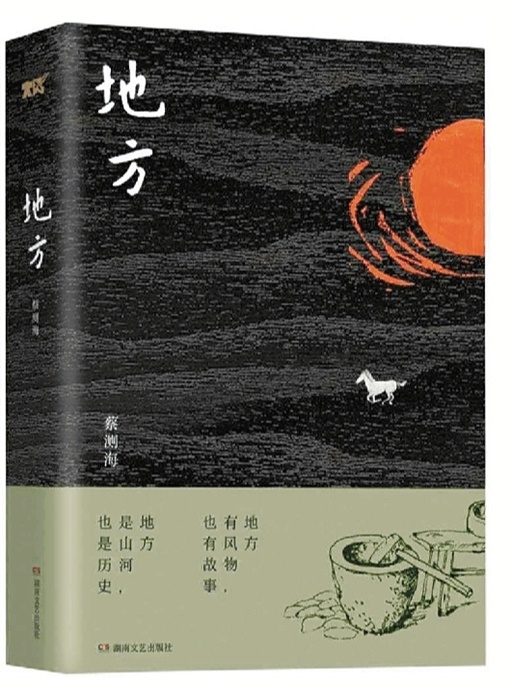
二 民族与神灵的地方性建构
文如其名,和书名“地方”一样,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质和神秘色彩,向读者展示着三川半独有的山川草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族特色、人物性格等多方面内容,是一部体现泛三峡地区独特地域里自然生命和人物命运交杂的地方志。
其一地域特征明显。“以前的那个人,到了一个地方,会给一个地方取名字,叫勺哈,岩冲,或者叫猛必,又或者叫乌鸦,洛塔,古里。”“三川半的集市,名头寨、漫水、百福司、里耶、洗车、民安、来凤城、恩施、涪陵、重庆,有大有小。” “岩冲、洛塔、百福司、里耶”等地名都是湘西真实存在的。“孩子们的秘密是关于事物的秘密。山里河里,是秘密藏有食物的地方。野山菌,竹笋,山药,他们在树林和草丛里藏好,等孩子们去找。鱼藏在深潭,虾藏在菖蒲草中,螃蟹在石头下面,约好季节,孩子们把那些秘密打开。”“村中房屋,为三川半固有范式,有窗,有门,有缝,有孔。门有大门、耳门、后门,窗有前窗、后窗、东窗、西窗。内窗房门,楼洞壁缝老鼠洞。一屋四通八面,风光如漏如泻。” “有打三棋,四字棋盘,得三为先,灭杀对方棋子,似围棋,不分黑白,拈来不同的两种短棍为棋子,随时随地可以对弈。还有五子飞,五子连为先,又称裤裆棋,牌是上大人,九十六张字符,和牌为胜,似麻将牌。”这些孩童记忆、房屋门窗、棋牌游戏承载着三川半独有的景致。其二富有民族特色。彭家婆的夫妻和气草:夫妇双方如果有了隔阂,吃了和气草,两人便和好如初,药方为 “天和地相连,是蜻蜓和蚯蚓交配,无风自动草是月光草,隔江柳相连是万年树。” 村长治嗓子的秘方:“若嗓子不畅,用一种叫地口袋的蜘蛛网烧成灰冲水饮用。……若嗓子有火,用草药开喉剑,此药难吃,一用就灵。”两味药都颇具民族特色。再如村人造屋:“先制木为排扇,先立起一排扇,人将排扇立住,同排扇一并举起,另一排扇也依法举起,上边人将两排扇对接,做成一间屋,再依法往两头延伸,排扇依次对接,做成三五间,成一幢屋。”典型的湘西苗族土家族风格。其三带有巫傩之气。三川半的马能飞:“扁马,像飞马留下翅膀,这些扁马行踪诡秘,才见好好地叠在马栏里,一转身一匹马已不见。在拴马桩那吃着草料,吃着吃着就不见了,只留下缰绳。”三川半的绣花鞋会说话:“声音是从那只楠木柜子的抽屉里传出来的。是抽屉里那只绣花鞋在说话。绣花鞋怎么就成了金口银口,成了会说话的女精怪。绣花鞋掀开抽屉,走出来,忽左忽右地往前走去,好像两只鞋在走路。” 三川半的人能来往于阴阳,吴家公公死而复活,从棺材里坐起;田聋子死了又活,活了又死。真是让人惊叹。
无论是地域、民族的多元,还是巫傩、湘楚的神秘,都体现着作者“万物有灵、万物有情”的写作观。在三川半,人神共生,万物皆有生命,整个世界皆有神灵,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草木花朵,土地、房屋、牛舍、菜园、庄稼,都和人一样,有呼吸、感觉和灵魂。以《蛙眼》这一章为例,蛙可以和鳖说话;蛙可以望天,看月色,看日头,看雨情、旱情。“人用功,蛙用自在。蛙眼四顾,那时天旱三年,东海之水不盈,池水过埂四溢,蛙命常在。”“三川半人不吃蛙肉,蛙是雷公的鸡,吃蛙肉会遭雷打。蛙腿似人腿,人不吃人,怎么会吃蛙?” 蛙和人一样,知天命,察命运,在人蛙共存的“池塘”,人是不能吃蛙的。《地方》里鸟蝉、虫鱼、蟋蟀、蚯蚓,仿佛都与人的五官打通,人与自然唇齿相依、血肉相连,构建了一个诗意、神性、和谐的“地方”。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地方”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是作者栖身生活的湘西故乡,也是精神版图上的“三川半故乡”。“地方性”是延续中国小说传统的重要特质,“地方”一词是地理上的名词,更是文化上的名词。蔡测海说:“各人的精神版图是不同的,鲁迅是赵庄,沈从文是边城,我是三川半。”从熟悉的现实世界,到陌生的小说世界,秉承传统文人精神的蔡测海都深爱着这片土地,这里流淌着他的情感,滚烫着他的热血。他播种、培土、施肥,日复一日劳作,《地方》是一次丰实的收获。

三 疼痛与温暖的历史性书写
评论家谢有顺有言:“小说是活着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学是记史,如《左转》《史记》《三国演义》等;中国优秀的小说更是记史,如《红楼梦》《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中国人重史,中国传统小说也始终贯注历史精神。“历史性”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根本性,写人事是写历史,写命运是写历史。无论是国家、社会几百年的“大历史”,还是乡村、个人几十年的“小历史”,“历史性”书写永远在中国小说家的笔下挥洒着。《地方》同样是一部写史的小说,书写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灾难和动荡,书写了三川半几十年的风雨和云烟。作者疼痛且温暖地记录着这一切,是亲历者的纪实,也是小说家的虚构。
《地方》着重描绘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三川半”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百态,这段历史是疼痛的,给三川半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三川半抓三件事,要抓粮食生产,要抓计划生育,要抓斗争。”“公社是一头黄牯牛的名字,合作化是一头黑母牛的名字,那头断了角的老黑牛叫土改,还有的牛,叫跃进、文革、批林、批孔,那头最不好使唤的牛叫四人帮。”《地方》的文字叙述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土改、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苦难时期、文革等特殊年代,尘世的一切苦难和疼痛都在三川半生长。有全村几年挨饿,妇女不育,甚至死人的。雨因为饥饿,带自己的女儿逃荒,被村长收留。公社书记为了救自己快要饿死的娘偷公社的粮食,但书记的娘最终还是饿死了。“灾年,禾不结籽,人不生崽。三川半的灾年,人愁,愁庄稼,愁日子,忘记愁自己的身体。人的生理变化被忽略。大姑娘不发育,干柴火一样。……村长得了水肿病,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水肿不是传染病。先是脚肿,然后是脸肿,最后整个人都肿了。饥饿年月,人人成了大胖子。”有卷入时代洪流,受“阶级斗争”“文革”等冲击,命运悲惨的。财舅舅因为新中国成立前是地主,被划为“四类分子”,要多多改造,多做额外劳动;艾中华成绩优异,本可以考上北京大学,却因为“文革”的到来未能参加高考,在三川半当民办老师;向世林因为出身地主家庭在高考政审时通不过,最终只能成为三川半的一名代课老师。除了物质的缺乏和人生的悲剧,让人更疼痛的是束缚在部分三川半人身上的心的枷锁和精神折磨。因为高音喇叭批判《水浒传》中的宋江,一位叫宋江的老师承受不起心理上的恐惧,上吊自杀了;向世林因为长期被家庭身份影响和精神压力,他拜宣传政策的高音喇叭为干爹,他埋怨自己的爹“怎么不去当红军?要当地主!”甚至宁愿自己的亲爹被反动派杀了;有小丁右派的神经一辈子紧绷,精神受到重创,一听说被摘帽了,不是右派了,“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像被雷吓痴呆了一样”,死了。以上这些足以说明三川半历史的疼痛书写。
除饥饿、逃亡、悲惨命运等苦难史,作品呈现了更多的温暖、亮色和对人文关怀的追求。首先,作品整体的基调是温暖、自然、恬静和美好的,主要得益于作者对自然、村庄、人物的诗性描写,在这种诗意弥漫的气息笼罩下,这些人间的苦痛好像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了。其次,作品中的人物大都给人温暖。叙述人物就是叙述历史,人事是村事,也是国事。人心带着温暖,人事组成的历史也是温暖的。使劲过着野人式的洞穴生活,村长收留了他,还把女儿嫁给了他;远方的草药匠、手艺人、逃荒的,村里一一给予安身立命之所;城里来的老号、小军、任蓉蓉、周涛、谭谦、林扑等学生,村人一一接纳;铁梅、程思思等知青下放到三川半,村长和村人照顾着;老书记弥留之际仍然想着“守土有责,造福一方。”“村长照应村里人,村长照应全村人有饭吃,村人照应土地和牲畜。村长照应那几个地主富农分子,照应右派,他们也是村人,也同村人一样过日子。不让他们多挨骂。照应那些知青,不让他们饿着,累着。他们有一天离开村里,不缺手缺脚,带上好身子回去见父母。”这种对村人、对外人的照应,就是温暖。甚至对村里的狗、马、小鸡、画眉等动物,筛子、石臼、斧头等器具,村人都是倍加爱惜。“舍不得吃,就放回画眉窝,你再扯三根头发放进画眉窝,蛇就不敢偷吃画眉蛋了。”吃画眉蛋,人可以变聪明,但为使蓝宝石一样的画眉蛋变成美丽飞翔的画眉鸟,善良的露和使劲不仅不吃,还加以保护。物尤如此,何况人乎!
疼痛和温暖的历史性书写背后,作者写史的角度值得注意。对于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1979年人口普查等时间段的大历史,作者采用真实、真诚的记录方式。对于这段历史、这些大背景下的人物命运,作者不做评判,而是客观记录,让人物、人心去说话,公道自在人心,无论岁月怎么突变,时间怎么流逝,历史永远是人心写就的。而对于个人史,作者更多采用民间史、口述史等比较感性、魔幻的叙述方式。村长娘子雨神奇地来神奇地走,六公公的斗笠故事,草药婆婆的采药故事,百福司卯洞崖壁上的仙人洞故事,母猪洞崖上的石刻文字故事,等等,都有民间和传记叙事特点。这种正史和野史,大历史和个人史的交替集合叙述,让作者的历史性书写更有魅力。
韩少功评价蔡测海“对小说美学有很好的直觉和很高的标尺”,蔡测海的小说是“美的传灯”。诚然,蔡测海的小说完美延续了中国小说的汉字之美、诗意之美,《地方》在传承中国小说传统的文字之美外,在文学性、地方性、历史性等方面,又有新的延续和突破,守护着文学的诗意,守护着人物的生动,是当下文学创作成果中不可多得的重要收获。在风起云涌、不断变革的新时代,小说创作不是一味“往前走”,求新求变,而是“往后看”,回到传统,回到文学本身,从这点看,《地方》作了非常有力的尝试和极其有意义的探索!
(作者单位:芙蓉杂志社 原文刊于《文艺论坛》2022年第4期)
【相关链接】三川半的喜与悲——读蔡测海小说《地方》
责编:李寒露
来源:文艺论坛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