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敏 中国绿色时报 2022-07-29 15:4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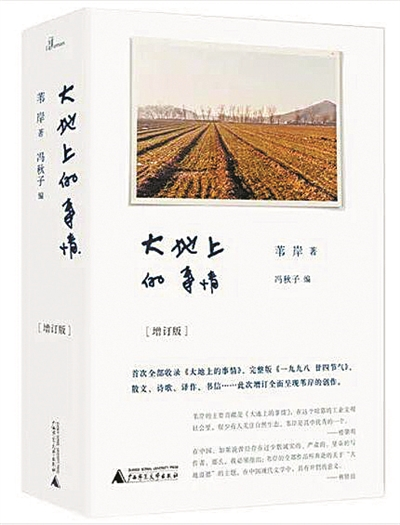
像周华诚在西湖边以节气记事,农家出身的诗人苇岸对田地亦有着天然亲近、割舍不断的感情,从立春到大寒,他在他的家乡——北京昌平一个叫北小营的村庄,用相机和笔记录了二十四节气到来那一刻的状貌、变化及与人的心灵联系,写下《大地上的事情》。这份庄重令我感动。
他眷恋着大地,眷恋着田野,看啊,“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麦田整整齐齐摆在辽阔的大地上,仿佛一块块耀眼的黄金。”他与自然有着无法切割的心灵联结。
对于每一个时令季候他都敏感好奇,扎根于时间深处,将视听定格在自古轮回的节气中,定格在立春时节万物萌动的气象,谷雨时分啄木鸟富有节奏的敲击声,夏至的田野里弥漫的麦秸的气息,小满来临的时刻布谷鸟和灰喜鹊悠扬的欢唱,大雪时分阳光照耀着无边的雪野……在他的眼里,四季皆美,“三月是远行者上路的日子,他们从三月出发,就像语言从表达出发,歌从欢乐出发。三月连羔羊也会大胆,世界温和,大道光明,石头善良。三月的村庄像篮子,装满阳光,孩子们遍地奔跑,老人在墙根下走动。”秋天结籽的草丛间,不时浮现出绚丽夺目的花朵,遍地的果实,露出善良的面孔等待采撷……苇岸说“我不能不为在这世上永不绝迹的崇高所感动,我应当走到土地里面去看看,我应该和所有的人一道去得到陶冶和启迪”。诗意,快乐,苇岸的内心明亮而又温暖。
他赞美一切原始朴素的事物,包括澄澈的初心和原始的信任,怀揣着诗意的心灵,万物在他的眼里便有了诗意,他的文字有光,有爱,质朴、和煦而又明快。他以诗人敏感的心对蚂蚁、麻雀这些貌似卑微细小的事物都给予了细腻的关照,因为他与它们息息相关。在他眼里,大型蚁筑巢像北方人那样不拘小节,“将颗粒远远地衔到什么地方,任意一丢,就像大步奔走撒种的农夫。”麻雀蹲在枝上啼鸣,如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高声喊叫,“这声音蕴含着依赖、信任、幸福和安全感。麻雀在树上就和孩子们在地上一样,它们的蹦跳就是孩子们的奔跑。而树木伸展的愿望,是给鸟儿送来一个个广场。”甚至他听出麻雀在日出前后的叫声都不一样,他为它们写下诗歌,表达内心的感动和喜悦,“它们仿佛是太阳的孩子/每天在太阳身边玩耍。”它们的“淳朴和生气散布在整个大地”。山中的栗树勾起他拟人化的想象,“如果没有人采集,栗树会和所有植物一样,将自己漂亮的孩子自行还给大地。”
大自然对他是永恒的感召。在《去看白桦林》一文中,他说:“我常常这样告诫我自己,并且把它作为我生活的一个准则:只要你天性能够感受,只要你尚有一颗未因年龄增长而泯灭的承受启示的心,你就应当经常到大自然中去走走。”他的明亮通透,大概也是来自大自然的启迪吧。渐行渐远的人们,最终还需回到大地的支点。
苇岸不失时机地在大地上游走,库车、嘉荫、且末、海日苏,从汤旺河到黑龙江,从黄河到长江,他随时随处用心搜罗大地的讯息。在郊外,在旷野,他邂逅翩飞迁徙的鸟群,目睹不同寻常的太阳,记录星星的出现时序,驻足于身边的小花小草。他被田间农妇质朴的家常感动,于不经意间陡然瞥见原初意义上的“生活”,他向往那样的生活,尽管人们正日益远离。他为高高的枝梢上鸟儿们星罗棋布的“家”动情,“我觉得这是一种世间温暖与平安的象征,是这个季节比雪与太阳升落更优美的景色。”看到1988年1月16日的太阳不同寻常,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大,他惊奇万分,让我联想到梭罗在《科德角》中也曾写到海上某一日非同一般的太阳,心系自然的人,对于大自然亦有着不同常人的发现。
历史是宏大叙事,也是世间凡常。那凡常的一切似乎更令他动容。他记下农妇的交谈,记下小学生的一页保证书,记下窗边筑巢的胡蜂……这些细碎之物,打动着他,也深深地打动着我。
他关注身边的小花小草,像关注自己的亲朋好友。遍地的植物都有它民间的“土名”,相对于冰冷、割裂、切断了与土地的天然联系,被研究者命名的学名,苇岸更喜欢前者,因其更富有活力和魅力。“学名是文明的、科学的、抽象的,它们用于研究和交流,但难以进入生活。它们由于在特征和感性上与其所指示的事物分离,遭到泥土和民间的抵触;它们由于缺少血液和活力,而滞在学者与书卷那里……俗名是事物的乳名或小名,它们是祖先的、民间的、土著的、亲情的。它们出自民众无羁的心,在广大土地上自发地世代相沿。”这让我想起前几日在北坞公园看到遍地开放的野菊花,难掩欣喜拍照分享,不料有花友纠正说这是“假还阳参”。面对这个名字我一脸木然。不解,亦无法接受,与我自小就叫的“野菊花”无法产生丝毫的联系,也对不上号。内心寻思:我还是叫它野菊花吧。而另一种可爱的小花,被花友叫作“土黄”,说是一味中药。我复木然。跟先生聊起,先生说小时候他们管它叫“老头儿乐”,花管是甜的,这种小花在书里被苇岸唤作“老头喝酒”,无论是“老头儿乐”还是“老头喝酒”,均联结着一代人欢乐的儿时记忆,相比于中规中矩而又陌生疏离的中药“土黄”,后者显然更为可爱可喜。民间自生的一切,与大地相连,无疑也更加地接地气。
苇岸说:“在科学到来之前,每个事物都有它自己土生土长的名称。这些名称身世神秘,谁也无法说清它们的来历,它们体现着本土原始居民的奇异智力、生动想象、无羁天性和朴素心声,与事物亲密无间地结为一体。科学是一个强大的征服者,它的崛起,令所有原生事物惊恐。它一路无所顾忌的行径,改变了事物自体进程。科学的使命之一,就是统一天下事物的原始名称。”当然,“各地的‘原生力量’也从未放弃过抵抗。”
他被万物感动,而他的感动又常伴着感伤。他看到,“在神造的东西日渐减少、人造的东西日渐增添”的今天,在蔑视一切的经济的巨大步伐下,鸟巢与土地、植被、大气、水,有着同一莫测的命运。“成人世界是一条浊浪滚滚的大河,每个孩子都是一支欢乐地向它奔去的清澈小溪。”然而,“孩子们的悲哀是,仿佛他们在世上的唯一出路,便是未来的同流合污。”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仿佛有着某种不可把控的力量,这力量,使诗人忧郁。面对欲望助推下人类对于自然的疯狂挤压,他的字里行间也透着隐隐的担忧,“今天,各国对地球的掠夺,很大程度上已不仅仅为了满足自己国民的生活。如同体育比赛已远远超出原初的锻炼肌体的意义一样,不惜牺牲的竞争和较量,只是为了获得一项冠军的荣誉。”
苇岸是通透的。站在昌平的家里,看着四周一幢幢不断耸起的高楼,看着田野不断地向远方退去,他的心中布满了忧愁。他知道,“全世界都在欢呼和促进这一进程,唯有可爱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和诗人,发出了与它对立的声音……这声音在强大的进程面前多么微弱,即使一声孩子的喊叫,也能将它淹没。”浮世的喧嚣中,诗人苇岸还在亲近着一棵树,一只鸟,一片云。“树木是大地的愿望和最初的居民。哪里有树木,说明大地在那里尚未丧失信心。”他希望终日奔忙的现代人,不在“追求幸福”的名义下迷失于毕生追逐财富的歧途中,认为“把幸福完全寄托在财富上,是人类无数错觉中最大的错觉。”
苇岸的文学、艺术观与此一脉相承。他崇尚文学艺术的简约风格,偏爱“为人类指明方向的作家”,他知道这样的作家不是某个时代的,而是永恒的。他特别提到了梭罗,认为梭罗承继了“人与万物原初的和谐统一”的精神传统,他的至爱之书《瓦尔登湖》将他从诗歌引向了散文,并且让他坚信散文——这种如E·B·怀特所说“作家与作品相对合一的文体”,从此将伴他一生。他崇尚和选择的,并非一种文体,而是极简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的价值、意义,他愈加坚定地要像梭罗那样,回到事物本原的意义,回到人生的起点和原点。
他要寻找素朴之源,抵达事物的核心与原质。那些没有具名的古老典籍进入他的视野,那是“古朴时期心智健全的人类整体精神的最高显现”。他看到古代大散文准确、清晰、简约自然、行云流水般不现媚痕的叙事风采。“这是一种以生气和力量做后盾的自信,坦荡直率地面对事物本身。”这些,与他的内在心性无不相契相合。
他在书中还谈到他的诗人朋友顾城、海子、黑大春,借此表达了许多自己的想望,他希望诗歌回到原初,恢复诗歌原始的声音性和吟唱性,他希望生活日趋繁复的进程中,文学艺术不再推波助澜,而是返璞归简。
在他看来,一生写一部书,二三十万字足矣。果不其然,他的一生只留下了一部书。他每篇的文字不长,却有着节制的美,就像他欣赏博尔赫斯的爱惜笔墨,《大地上的事情》每一节一两百字,简洁明快,单纯明亮。
他欣赏朝气蓬勃、质朴自然的写作,喜欢内心和精神有光的人,不喜欢自我深奥和封闭的文学与学术。
内心有光的人,文字必然亦是暖的。苇岸说:“我愿意光明地、信任地看待一切事物。我希望我的文字给世界带来的是善意和温暖,而不是相反。对于人类来说,我坚信有些东西是永恒的,而不是仅属于哪个世纪的。”他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质朴,“质朴即包含着文字的质感、朴素、简单和温度,以及一个作家对世界应有的爱与祝福。”
林贤治在序文中对苇岸给予了深刻的理解,他说人文精神的内核就是对生命的爱,是爱培养了苇岸的美感,人格与艺术的一致性要求,使他一次次回到历史的原点。大地使苇岸辽阔,亦使他谦卑,他主动避开主流和嚣音,沉静地居于心灵中间,开拓自己的内视野,以自己的行动做着保存人类精神世界原质的努力。
可惜啊,诗人已早早地不在。
他怀着深深的眷恋,在书中给我们留下《大地短诗》,那是他对大地的深情礼赞。在《结实》一诗中他赞美秋天,“所有结着籽粒的植物/都把充实的头垂向大地/它们的表情静穆、安详/和人类做成大事情时一样”。他写下《美好如初》向大地告白:
我还是应该单纯
因为这个世界
并不缺少复杂
我喜欢早晨
到田野的广场上去
等候太阳到达
当黑夜的列车停下
太阳踏上天空的站台
仿佛一个远方的朋友
微笑着向我走来
……
人生短暂,逝者如斯。然而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苇岸,依然需要大地的支点。(陈艳敏)
载于《中国绿色时报》(2022年7月29日 第04版)
责编:唐语韩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