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艺网 2022-07-19 09:17:10
《边城》里最动人的乡愁
文丨逆舟
边城是沈从文理想的精神家园,心中永远皈依的圣地;而桃花源则是陶渊明或者说古往今来许多读书人的精神家园,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所以很多人都会拿《边城》与《桃花源记》相提并论,不过在我看来,“桃花源”与“边城”其实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概念。“桃花源”是陶渊明想要“去”的地方,那里的人们自给自足,衣食住行样样不缺,不涉世乱战祸,人们精神境界怡然自乐,不受人世政权管辖……听起来很美好,但其实是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乌托邦式“理想之地”。但是“边城”不同,边城是沈从文出生地,是他生于兹长于兹的“故乡”,是他总想要“回”的地方。与想要“去”的地方相比,那心心念念想要“回”的故乡,才是让人更难以忘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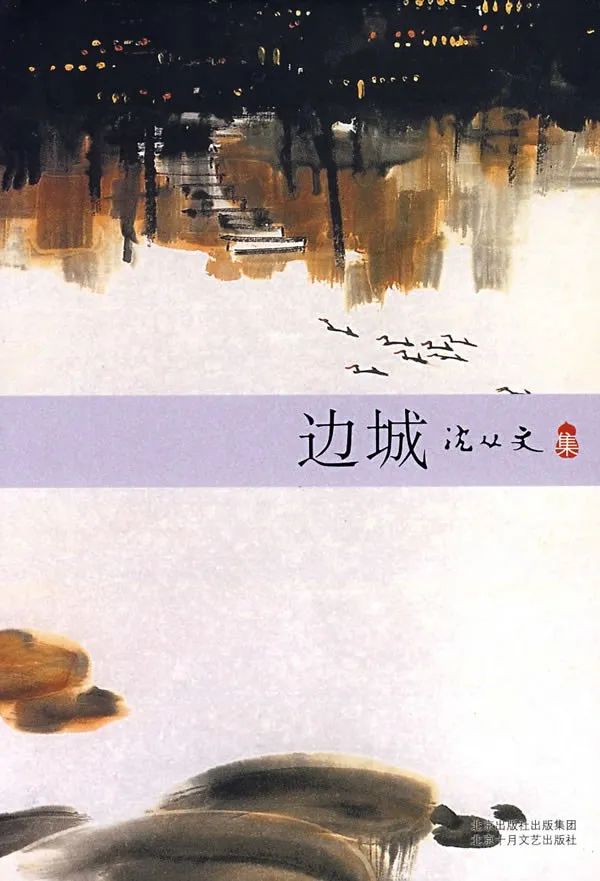
“边城”代表的是我们脚踏过的故乡实地,但当“故乡”的土地发生了变迁与变化,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于是我们便有了“乡愁”。乡愁是广泛的,可以与美丽动人的自然环境相关,也可以与人文情感、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相关。但不管乡愁与哪一种事物相关,它必定都是独特的,是对一个人的人生具有特殊的意义的。一个人不会对彩电冰箱、高档汽车、名牌衣服、高楼大厦有乡愁,也不会对节奏的生活和重复忙碌的工作有乡愁,更不会对自己银行卡存的钱有乡愁……
《边城》里的乡愁是“清澈透明、触目的青山绿水”,是淳朴的民风,以及同样淳朴的“爷爷”和“翠翠”。沈从文的文字,就好像是一部录像机,将记忆中的美好、透亮、纯真逐一记录下来。当我们看着文中的描写,思绪和记忆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回溯,想起童年,想起乡村,想起淳朴的乡人……于是便激发出了我们的“乡愁”。
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着她也教育着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小兽物”是可爱的样态,刚生下来的动物幼崽往往都具有一股天然可爱的样态,“小兽物”的另一层意思,大约是指“自然长养着也教育着”的那种纯自然态。在教育“减负”之前,常听得有家长说要给小孩子留点自由的时间和空间。一个“留”字,说明了小孩子缺失了某种自然的状态和“自然的教育”。因此,对于现代社会的人来说,即便“自然长养”还没有成为乡愁,但是,“自然的教育”已经成为一种乡愁。
同样的,小说中的“翠翠”是故乡淳朴、自然、纯净人性的化身。她并不是具体某个人的邻家小妹,因为一个人的邻家小妹只是故乡的记忆,但不是乡愁。“翠翠”身上既有邻家小妹的“过去时”也有“现在时”,“你的”邻家小妹与“我的”邻家小妹会有不同,但是,“你我”的邻家小妹的身上,却都能看到“翠翠”的影子。这个时候,“翠翠”便成了“你我”乡愁的一部分。
“边城”的爱情也是一种天性自然的爱情,唱三年歌即可。《诗经》的《风》中,也有这样的爱情。这种“自由恋爱”比现在人的“自由选择”要高一个等级。“边城”天保和傩送两兄弟商量用“走马路”的“抽签”方法来决定“结果”,商量妥当后,“一切安排皆极其自然,结果是什么,两人虽不明白,但也看得极其自然。”“爱”是人的事情,成不成是“天意”,他们分得这么透彻。谁都不会对“爱”患得患失,从恋爱到结婚,他们看来都是极其自然的纯净。
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
……
爷爷,你说唱歌,我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缠绵,我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得到了虎耳草。
傩送替天保走马路唱山歌。翠翠听到的歌是虚虚实实亦真亦梦,这就是翠翠接触到的爱情。“摘了一大把虎耳草,”一定是虎耳草,不能是在菜园子里摘了一把菜,也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因为虎耳草的梦想就是爱情的梦想。翠翠的爱情没有物质裹挟,也不是为爱情而唯美的爱情,是让爱情归还到爱情的原本,这不就是我们的乡愁么?
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
“摘虎耳草”的梦想,是多么微小,多么平凡,多么实诚、淳朴的梦想。“选顶大的叶子作伞”。翠翠都懂得恋爱了,还是这般的童真,童心、好奇。我们常说的,保持一颗童心,童心其实也是乡愁。
《边城》具有无穷无尽的属性,可以无穷无尽地去阅读,好比自然,好比生活,写不完读不完,常读常新、常写常新。乡愁也是一种极为宽广的思绪,一时有形、一时无形。但那一座边城,一条清溪,一根竹篙,一个如山泉般清透的少女,一段绝美的爱情,却为读者构筑了一段烟雨潇潇的梦境,引发了无数人共同的乡愁。
责编:周听听
来源:湖南文艺网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