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0-07-11 10:03:48

(中学时的青涩少年)
文/何云波
一
1977年,我在一个乡下中学,读高二。
突然就听说,过去推荐上大学的法子不灵了,要高考了。这于我等毫无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真是特大喜奔,好像天上突然要掉馅饼了。
不管这馅饼接不接得着,赶紧去准备簸箕啊!
然后,1977年那个冬天,中国积攒了10年的570万考生,甚至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那年,北京市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而一篇满分的作文,那开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
然后,1978年的春天,27万余人脱颖而出,走进了大学校园。也包括那位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父亲。
那时,高中只读两年。紧接着,就要轮到我们上战场了。
那个时候,每个公社(现在叫乡)都办中学,我在那个叫陶岭的“社办中学”,到初中到高中,已经“乐读”了快四年。尽管也有个别不错的老师,尽管我一直算喜欢读书、成绩优秀的学生,但那个时候实在没什么书可读(偶尔弄到一本《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之类,就是万幸了),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完全记不清是如何备考的,然后,在1978年的那个夏天,我也走进了高考考场。
如今回忆起来,完全不记得考了些什么,作文写的啥(查阅资料,说是将一篇《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文章缩写成500至600字,我却记得湖南考生好像写的是《心中有话向党说》)。稀里糊涂地进去,也不知道向“党”说了些什么,就懵里懵懂地出来了。
然后,成绩公布,文科五门(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我得了270多分。
那年,据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录取率大约6.5%。
而我,属于93.5%的“大多数”。
“大多数”就“大多数”吧,当不了“一小撮”也没什么。其实,在那个乡下中学,我已经算是“高考状元”。
那时实在太小,不懂事,来不及感时忧世。
那年,我15岁。
二
有人说,对那时的乡下人而言,高考就是唯一的“鲤鱼跳龙门”的机会,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分水岭”。
瘦弱的十五岁的少年,如果从此就在“广阔天地”中去“大有作为”,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何以“为”?
县里准备办复习班,突然来了通知,我等算“可再造”之材,然后就有了“回炉”的机会。
那个时候,全国人民奔“四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代表“科学技术”的理科受到高度重视,理科复读班在县一中,我们“文科班”却只能偏安一隅,被发配到城关镇边上的“城东中学”。不过,这里的师资、学习条件,已经比那“社办中学”好了许多。在复读班,我进去的时候,高考成绩算中等,一个多月,就考第一了。
第二个学期,“文科复读班”也终于被“插”进了一中,复读生与应届生被编成一个混合班。应届生基本上都是家在县城,复读生多来自乡下,于是,穿“皮鞋”与穿“草鞋”的,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
那时的高考,尽管录取比例很低,但似乎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压力。可能是因为反正比例低,“大多数”上不了大学,做个“大多数”也就没什么丢人的了。大人也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我就这样自由自在,悠哉游哉地备考,该干嘛干嘛,记忆最深刻的不是课堂,反而是跟着同学学骑自行车,还有某部新电影,如印度电影《流浪者》之类来了,同学委托我去电影院的窗口挤电影票,还有,冷饮店三分钱一支的美味的冰棒……
终于临到了考试,五门正科,总分满分500分。外语为参考,不计入总分。我们在初中时,正流行黄帅反潮流,张铁生交白卷,“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能当接班人”,老师要我们对学校提意见,什么课可以不开,我们便异口同声地说:外语。结果,那英文,除了课本第一课“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记得烂熟,其他就一概不知了。五门正科的考试都还觉顺利,最后一门考英语,卷子发下来,两眼一抹黑,考场规定至少半小时才能交卷。只有选择题可圈,凭感觉几分钟搞定,然后就干等着,半小时一到,大家呼啦一声都作鸟兽散。
等了个把月,分数公布,我考了345分(语文73,数学56,地理80,政治、历史忘记了,另外,英语作为参考分,蒙了6分),忝为全县“文科状元”。我等都可以做“状元”,那时的教育质量可想而知(这“状元”,主要还搭帮那没及格的“数学”,文科全班也是全县4人考上本科,我就是比另外三位同学数学多考了20分,结果我上了作为重点的湘大,他们有两个去了湖南师大,一个去了湖南财经学院)。
那年,本科线理科290分,文科300分。重点大学线文科340分。然后,就是填志愿,面临人生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志愿栏分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两类。重点大学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湘潭大学,一来湘大是1978年国务院钦定的全国十六所综合性重点大学之一(其他非综合性重点大学多为理工为主,俺们不受待见的文科生,可选择的实在太少),那时声誉正隆;二来,我那点分数,刚过重点,也没什么好挑剔的。于是,果断地,重点第一志愿填了湘潭大学,第二志愿,象征性地填个“武汉大学”,以做点缀。非重点第一志愿填的“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那是那时的我很想去的学校。也许,在那个时代,法庭、法官,代表的是威严,是权力,让我等心生敬畏,想想,自己有朝一日也带上大盖帽,想想就够美的了。
又是等待,倒也不着急,大学肯定是有读的了。结果,有一天,我在老家的那条窄窄的巷子里枯坐,有人拿来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你被全国重点大学——湘潭大学录取了,专业:中文。
首先是乡里轰动了,十里八乡,都传着大村何家出了个大学生,了不得。
再踏进县城时,一切仿佛也不一样了。在县一中教书、后来去了政府部门的姨夫,带我走亲访友,到处看到的是羡慕的神情,听到的是夸奖的话,还有人家暗示:家有小女初长成……斯情斯景,真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感觉啊!
然后,“草鞋”换成了一双“解放鞋”,一身新做的土布衬衣,一只木箱,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湘大,成了“七九中文”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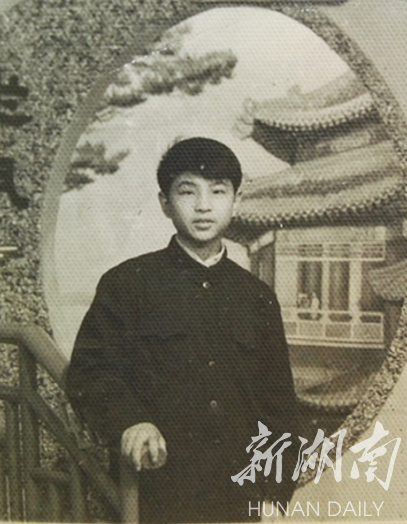
(我大一了)
到了湘大才发现,我在班里,高考成绩算最低的之一。我的那些同学,三百五、六十分的是常态,最高的377分,据说那年北大的文科线也就375分,武大350分。那时湘大政治地位高,招生有特惠,凡本省考生,志愿里有湘大的,都由湘大先挑,结果我的不少非第一志愿的同学,就这样被“抢婚”了。然后,我便自我安慰,我与湘大,算自由恋爱,两情两悦,虽然自忖“姿色”差了点,既然湘大不弃,那就好好努力吧,争取未来做一个合格的“湘大人”。
翘首望君成,莫负断肠人。
这是同学桂老毕业时给我的留言。
三
毕业了,在大学教书,再次与高考发生关联,是参加高考阅卷。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教汉语,那时的高考阅卷,由湖南师大负责。于是,有几年暑期,都会在师大校园里待几天,为祖国选拔人才。
记得1990年的夏天,我再一次走进师大校园。我负责语文卷中作文的复评。那年的考试是一篇材料作文:
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去玫瑰园,一个女儿告诉母亲,“这里不好,每朵花下都有刺”,另外一个女儿告诉母亲“这里真好,每个刺上面都有花”。根据这一材料展开描写,写一篇议论文。
然后,每天看几百上千篇的同题作文。大部分学生都是从看问题要一分为二的角度立论,由此联系现实,虽然有种种不如意之处,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作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中规中矩,仿佛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使你无法不给他一个该得的分数。但“真理”被重复一万遍,也难免令人生厌。百无聊赖之下,有一天,忽然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女生,先从自己的坎坷经历讲起,父亲如何早逝,生活如何艰难,生活的磨炼,让她如何不断地调整自己,重新认识人生,最后结题:
生活本来就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生活才构成了完整的生活,就像玫瑰有花就会有刺一样。
见此作文,眼睛顿时一亮,一个中学生,有如此的悟性,真是难得。但一看初评老师给的分数,低得让人大吃一惊。我给铁道另一位负责复查的老师看这作文,他也觉得好。我心里有底了,去找负责初评的“判官”,是位中学老师,我问这作文写得很好,为何给它一个那么低的分数。那位老师回答:第一,此文不合材料作文的格式,有跑题之嫌;第二,这位同学的思想表现得太消极。
然后,我跟那位“判官”说,你看,文章虽然前面没复述材料,但结尾不是点了题吗?第二,一个中学生,能够看到生活的不完美,还能正确对待,其实已经够“积极”了啊!
那位老师听了我的话,觉得也还在理,把分数改了过来。满分30分,由不及格变成了“24”分。复评老师有3分的权利,然后,我又把“24”改成了“27”。
这一改,仅仅一篇作文,前后得分就差了十几分。不知道那位女生是否因此考上了大学,因此改变了她的命运。

(40年后,回首来时路)
有时,觉得人生真的很奇妙,时代造就人,而有时,冥冥中,你的作为就可能跟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有了关联。
就像我的高考,你的高考,我们的高考……
责编:曹漾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