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晨报 2019-01-19 08:0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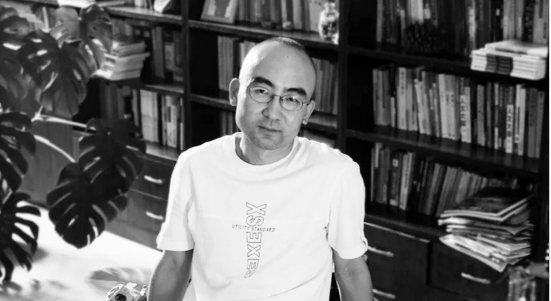

“半圣”曾国藩,这一称呼极有意味。
一个“圣”字是后人对他的推崇,而一个“半”字又略显迟疑。
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对他的评价皆褒贬不一,更佐证了曾国藩的复杂性。
他既被认为是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圣人标准的人,又有冷酷无情“曾剃头”的名号;他的家书被捧为后世家教的“课本”,他的视野和胆识被后人高度赞扬,但七次科考才中秀才的他,也曾是一个爱抽烟、爱看杀人、爱看美女,脾气大、心气高,早上起不来、晚上喜欢出去“浪”的“顽劣”青年。
研究过乾隆、朱元璋、吴三桂、慈禧的历史学家张宏杰,将最多的笔墨给了曾国藩,从《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给曾国藩算算账》到最近出版的《曾国藩传》,二十多年与曾国藩的“交往”,他用更平视的目光写下了这位湖南乡下普通青年的“逆袭”之路。这一路并不顺畅,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自尊被踩在脚下,他与内心欲望艰苦斗争,与清末王朝腐朽制度的来回“较量”,充满了一个人的挣扎、徘徊、妥协、战斗和坚持。
“在中国的古人中,我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最高的,我认为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正面的东西最多,负面的东西最少。”但从青年时期就开始关注到人性复杂性的张宏杰说,“但我也并不避讳地说,他也有非常残忍的一面。像你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头没有一个纯粹的好人,也没有一个纯粹的坏人。”
撰文/记者 赵颖慧 实习生 易百卉
“射手座”曾国藩:“顽劣”的青春
今天,无论是画像还是文字里的曾国藩,都给人稳重、坚韧、深谋远虑的形象。“据说按‘星座学’来说,这是土象星座比如金牛座人的特点。但是曾国藩的生日显示,他居然是‘像风一样自由的’射手座,活跃外向,坐不住。曾国藩的青年时代恰恰如此,他是一个非常爱交朋友、非常爱串门、非常爱聊天、非常爱开玩笑的人。”张宏杰说。
当他遍读了曾国藩留下的日记、手稿、奏折等一手资料后发现曾国藩“顽劣”的青春。刚进京到翰林院,每天就是串门聊天饮酒下棋。他住在城南菜市口附近,附近就是刑场,隔三差五就和朋友们一起去看杀人。他成天烟不离手,三十岁之前戒过两次烟,都没有成功。
他还爱看美女。31岁的时候知道朋友纳了一个妾,长得很漂亮,于是借故到朋友家聊了一会天后,再强迫这个朋友把小妾领出来让他看。他见了小妾,又和人家开了几句玩笑,调笑了几句,回家又写日记“骂”自己“狎亵大不敬”。
他也会逢场作戏。一个叫黎吉云的朋友来拜访,拿了一叠刚写的诗,请他点评,他本觉得这诗写得不怎么样,但一开口,却言不由衷地夸奖起来。他还有一身傲慢之气,听不进不同意见,脾气暴躁。一次跟刑部主事郑小珊意见不一致吵起来,隔着桌子就要动手,拉开后,还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
张宏杰还说:“曾国藩是同时代大人物当中最笨的一个。”父亲曾麟书考了16次,直到43岁才考上秀才。曾国藩比父亲略好,六次落第后,第七次考试终于中了秀才。曾国藩曾说自己“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批评他“才短”“欠才略”“于兵机每苦钝滞”。甚至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他“太儒缓”。
如果你遇见的是二十多岁的曾国藩,或许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有“立德、立功、立言”立志做圣贤的人。
而立之年,立志当“圣人”,坚持“写日记”
一个“愚柔”又“顽劣”的乡下青年,为什么忽然想要做“圣人”,靠什么做“圣人”?
实际上,在进入翰林院之前,曾国藩除了四书五经外没读过什么书,也谈不上什么学术修养,“入京为官之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都非常庸俗,从小听闻的不过是鼓吹变迹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功名富贵”。
当操着一口难懂湘乡土话的他到了翰林院,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此时他已近而立之年。他认真研读了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才明白,科举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读完这些,他才发现自己的视野多么狭窄,境界多么低劣,如何洗刷自己的身上的鄙俗之气,成为他新的焦虑。”
张宏杰说:“湖南历史上有一个规律,一个人只有出湖,才能褪却身上那种在闭塞环境下产生的狭隘偏执,变得大气宽广,有所作为。”
曾国藩做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张宏杰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也跟大部分普通人一样,日记写成流水账,还没法坚持写下去,确定的目标也不能完成。1840年6月,十六天的日记里,“关于‘宴请’的记载八次,起床失败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他说要天天记《茶语偶谈》,结果这个月,他只记了两次……”
直到唐鉴和倭仁告诉他,记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要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还要用恭楷来写,当作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更重要的一个技术性细节是,把日记给朋友们看,并请每个人做点评。“外力远远大于内力,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张宏杰说。曾国藩将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甚至在外带兵,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们看。父亲16次科举的韧劲和湖南人的“骡子”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张宏杰说他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
当曾国藩确定了做“圣人”的终身奋斗目标,他的选择也与常人大不相同。在太平军渐成燎原之势,众人皆不敢直言进谏的情况下,他锋芒毕露地指出皇帝的缺点:“打仗打了一年,皇帝连地图都没看过;表面上鼓励大家进言,但实际上并不真心采纳意见,还刚愎自用,出尔反尔……”
在国家正规军成溃败之势,国家危亡之际,他冒着极有可能灭门的风险,跳出国家体制,自创一支军队来取代国家军队,“这是大清两百年来没有过的,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而在建立和训练湘军的过程中,没有实权的“在籍官员”身份,使他在用人、筹饷、购械等各方面皆万分艰难,但最后却是曾国藩的湘军挽救大清王朝于危难,迎来了所谓的“中兴”。
张宏杰说,“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高明。他的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笨’的极致就是‘聪明’,‘拙’的极点就是‘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
“半圣”曾国藩,为何“杀人如麻”?
那为什么立志成“圣人”的曾国藩,又会留下“曾剃头”的名声,只剩下“半圣”?
张宏杰认为,他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里:“一方面,他对这个国家、民族、家族充满了仁爱,他是以仁义处事的;但与此同时,他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又表现出很残忍的一面。”
他刚出山协办团练时,在长沙严打地方黑恶势力。“曾国藩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询问,立即砍头。”四个月时间,他就亲自杀掉了一百三十七人,他指示各地杀掉的人数,就几倍于此。
“在南京城被围困的时候,他曾经要他的弟弟曾国荃最好不要让里面的老弱妇孺出来,让他们留在城里和太平军一起抢粮食吃,这个做法当然是非常残忍的。另外,所有的‘老长毛’,即从两广时期追随太平军的那些‘革命骨干’一律要杀掉,这些人投降的话也不能让他们投降。”
“仁爱”和“残忍”为何同于一身?“残忍的产生,一方面是他吸取了很多传统文化里‘法家’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他实际作战的经历。他感觉作为一个‘老长毛’,太平天国起义坚定的追随者,放出去之后会有很大的破坏性。站在曾国藩的角度,他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乱世用重典。”
尽管在张宏杰心中,曾国藩是他评价最高的人,但在《曾国藩》里,他依然把这些都写了出来。他说:“我们写人,他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这个人真实的组成部分,没有必要去避讳它,这才是历史的本分,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还原历史的真相。你不可能百分百地去还原它,但是你要尽无限可能去接近它。”
曾国藩内心的“灰色地带”
曾国藩在要求自己无限接近“圣人”的过程中,并非完全理想主义。
当圣人不能贪,但没钱怎么办?
得罪了皇帝和同僚的曾国藩在北京过得很不愉快,他很想回家,当时他已经40多岁了,可是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张宏杰曾算了一笔账,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文官,年俸是一百二十五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两万五千块钱,一个月两千零八十块钱,“今天的一个京漂这点钱都不够花”。
但当官还得置办官服,租一套体面的四合院,都得花钱。“因此在那个时代做京官实际上是一个赔钱的事。很多京官解决财政赤字,只有两个办法,一个靠家里补贴,另一个是营谋灰色收入。”张宏杰说。
但他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但经济压力如此之大,立志做圣人的曾国藩居然在梦里梦见了这样一件事,“白天跟人出去吃饭,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昨天有人送了他一笔别敬,数目很大,他当时就很羡慕”。醒来,他自己在日记里反省,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可见自己已经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
又有一次,他在日记里说起一件事,通俗大意是:“这段时间我随份子都很周到,谁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样做呢?今天我想明白了,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贺礼,以度过目前的财政危机。想想自己是一个堂堂的京官,一个要发誓学做圣人的人,居然打这么一点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差不多的,都有非常复杂的灰色地带,甚至是比较丑陋的一面。但是大部分人不会写出来,但是曾国藩不一样,他把整个修正过程记下来了,然后留下来日记。所以我们看到了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共鸣。甚至有的人看了以后,会感觉曾国藩也就是这样嘛,他也没怎么了不起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因为曾国藩勇于解剖自己。”张宏杰说。
对话 张宏杰:有一种说法,湖南人只有出湖才能成才
记者:湘军集团的强势发展让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湖南人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近代湖湘政治精英几乎都与曾国藩有关联,他与近代湖南人才辈出有怎样的关系?
张宏杰:确实,曾国藩对湖南的影响非常大,湖南原来在整个中国文化版图中也是比较边缘的一个地带。湖南是到晚清曾国藩的时候才崛起,那么曾国藩的崛起实际上一定程度是因为当时天下大乱的形势,湖南人又有经世致用的学风,这种朴实的学风在天下太平时不容易出头,但一旦天下大乱需要一些办实事的人,那么湖南人顽强拼搏的性格、霸得蛮的精神就显露出来了,就成为中流砥柱了。湘军崛起之后,一方面让很多湖南人获得了功名地位,湖南的官员走向了全国,另外通过镇压太平天国,江南的财富源源不断回到湖南,助催了湖南教育的发展。当时人发了财都是要培养自己的孩子。在整个全国的文化版图中,湖南文化上的分量就越加重了。同时,曾国藩赤手空拳创立湘军打天下的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记者:您曾说,曾国藩如果生在乾隆时代,可能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儒臣。那么为何曾国藩在他那个时代脱颖而出?
张宏杰:我感觉曾国藩他身上的一个特点是有担当精神。在咸丰刚上台的时候,别的大臣都不敢说话,但他勇敢地站出来指出咸丰身上的性格弱点。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他也不是为了出名,是因为当时国家积累了很多问题,我必须得把这个皇帝喊醒,虽然我自己可能遭到不测之祸,但是对整个国家有好处。后来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虽然好多官员都被任命帮办团练,但是别人基本上都没怎么做事,只有曾国藩一个人挺身而出,赤手空拳创立湘军,就是他要把那个时代最艰巨的任务自己承担起来。后来李鸿章说,曾国藩曾经向他传授过十八条“挺经”,一方面是说他要能挺下去,另外一个是关键时刻你要能挺身而出,担当这个责任。
记者:青年时期的曾国藩也曾经是个典型的“暴脾气”,但经历了几次大的挫折后,他学会了妥协,以更柔软的方式去碰撞这个世界?
张宏杰:有一个说法就是,湖南人只有出湖才能成才。如果你一生都局限在湖南,那么这种“刚”有可能变成偏执,只有你出了湖南,有了全国的眼光,你的这种刚才能变成刚柔相济,经历过很多事的磨炼,你才能够变成一个恰到好处。
责编:张璐
来源:潇湘晨报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