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南客户端 2017-12-26 10:01:20
新湖南客户端整合
今天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24周年的日子。据新湖南客户端报道,25日上午,湖南中联天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袁浩卿向韶山捐赠图书《毛泽东读书集成》,表达对毛主席的崇高敬意与深切缅怀,以及对家乡发展的支持与关心。《毛泽东读书集成》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历史、科教、经济、艺术等不同领域,其中大量手稿及毛泽东笔记都是首次向公众公开,是国内唯一一部将毛泽东阅读过、圈阅过、批注过的书籍进行系统归类编辑的大型类书,是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真知宝典。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尤其喜欢阅读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书籍。四大名著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曾让毛泽东为之痴迷。
今天,新湖南客户端带您一起了解,毛泽东是如何读四大名著的。
【红楼梦】
毛泽东谈《红楼梦》:不看三遍没有发言权

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毛泽东对古典小说情有独钟,而其中最令他倾心的无疑就是《红楼梦》了。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国家建设时期,毛泽东总喜欢提到《红楼梦》,并用不同的视角来解读《红楼梦》。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向来很高。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谈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提到:“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在毛泽东看来,把《红楼梦》当故事来读,是读小说的初浅层次;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才能进入到读小说的较深层次。
如何把《红楼梦》当历史读,毛泽东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要了解《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以及《红楼梦》中的思想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进步要求。第二,要把握好《红楼梦》的历史内涵,要把它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一个缩影。
《红楼梦》书中包罗万象,被称为“百科全书”,因为视角不同,所以每个人眼里都有一部 《红楼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1961年12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当刘少奇谈到自己已经看完《红楼梦》,说该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时,毛泽东说道:“《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还说道:“大家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毛泽东提出了“第四回总纲说”,是理解整部小说的“一把根本的钥匙”,而那张“护官符”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和地位的牢固形式和法宝,反映了他们利用这一法宝对财富的剥夺和占有,对平民百姓的肆意欺压。而这一切,没有敏锐的阶级斗争眼光,是不容易发现和领会的。
“青少年锻炼身体,男的不要学贾宝玉,女的也不要学林黛玉”
读了很多遍,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细节烂熟于心,信手拈来,经常评论和引用其中段落。
井冈山时期,贺子珍在谈话时说她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喜欢读《红楼梦》,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反驳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土地革命,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读《红楼梦》,与政治紧密结合。
对于宝黛的评价,毛泽东也自成体系。工作人员孟锦云有次说:“我同情林黛玉,可不喜欢贾宝玉,他对那么多女孩子都好,这叫什么事啊,一点都不专一。”毛泽东则反驳:“贾宝玉,是个很有性格的男孩哩。他对女孩好,那是因他觉得女孩受压迫嘛。大观园里的女孩总比那些男人干净得多,你还不懂贾宝玉。”
195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接见周世钊等几位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你们都是干教育工作的,应该把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必须记住:有志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须锻炼身体,使身体健强,精力充沛,才能担负起艰巨复杂的工作。《红楼梦》中两位主角:一位是贾宝玉,一位是林黛玉。依我看来,这两位都不太高明。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这种全不肯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瘦弱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今天的青年学生应该既有文化,又会劳动;既用脑,又用手;既能文,又能武的全面发展的新人。男的绝不要学贾宝玉,女的绝不要学林黛玉。”
1955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休息期间,爱新觉罗·载涛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同载涛热情握手,指着周恩来说:“我是《红楼梦》里的老夫人,不大管事,他才是掌家,有什么事可以找他。”毛泽东以书中人物自比,使严肃的气氛瞬间轻松。
《红楼梦》第八十二回里,林黛玉听到袭人评论尤二姐之死时说道:“这也难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说:“现在我感觉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性的优势。”
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有阅读能力,不可不读《红楼梦》
毛泽东喜欢向人推荐《红楼梦》,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秘书、卫士、厨师、司机和保健医生等等,这些人的职业各异,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毛泽东除了要求他们加强学习外,无一例外都推荐他们看《红楼梦》。毛泽东常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有阅读能力,不可不读《红楼梦》,不读就不懂中国封建社会。读一遍也不行,最少看三遍,不看三遍没有发言权。”
1938年10月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间休息时毛泽东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不看完这三部书,不算是中国人。”徐海东表示自己看过其他的,没看过《红楼梦》,毛泽东笑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
有次在广东珠江游泳休息时,毛泽东问时任吉林省公安厅厅长薛焰最近读过什么书,有没有看过《红楼梦》,薛焰回答:“这是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看过。”
毛泽东认真说:“搞公安的就不要看?你知道那里面有多少人命案子呀!这是一本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
戎马一生的军事家许世友反对读《红楼梦》,有次在部队干部集训上即兴说,红楼梦说的尽是吊膀子(男女间谈恋爱的事),有什么看头?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他指着在座的南京军区总司令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你能看点《红楼梦》吗?要看五遍。”
经过这次谈话,许世友真的读了《红楼梦》,不过却不是全本。他让秘书找到南京大学,要学校搞一个删节本,南大领导指定中文系吴新雷执笔,将大部头的《红楼梦》删减到5万字左右。删减工作是保密的,吴新雷也不知道是许世友要看,只知道是南京军区下的任务,要求“对《红楼梦》是压缩,而不是缩写,要全部用原文,不能有自己的话;主要人物、情节都要有”。吴新雷说“搞了五个月,我倒是真的读了五遍,不然串不起来。《红楼梦》 中的诗词只保留了一两首,《葬花吟》还是保留了。”
一次毛泽东问许世友读完红楼梦有什么感受,许答道,没什么感受,无非就是些吊膀子、搂搂抱抱呗。毛泽东笑说,你还是读得少,要读四遍才能懂。
《红楼梦》 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不只读红楼梦,毛泽东还看了很多研究红学的著作。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写了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研究《红楼梦》的著作中,毛泽东圈画和批注都比较多; 特别是俞平伯的 《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对“作者的态度”、“《红楼梦》的风格”这两节,圈画最多。
如在“作者的态度”一节中,作者俞平伯写“《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一句旁,粗粗地画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红楼梦》的风格”这一节,毛泽东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画了七八个问号。比如,就在这一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的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画下两条粗道,然后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写下“不同意”。
【三国演义】
毛泽东如何熟读活用《三国演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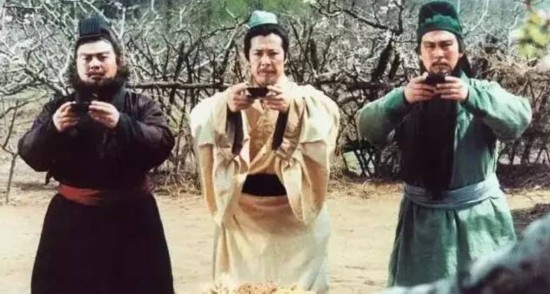
老版《三国演义》剧照
从少年时代到人生结束,毛泽东至少读了70年《三国演义》。他熟读《三国演义》,经常运用并赋予《三国演义》以时代含义,传播他深刻的思想。
从小就是“三国故事大王”
少年时代,出生于韶山农村的毛泽东就爱看书。当时在他老家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三国演义》还不多见,毛泽东第一次读到这部书,就爱不释手。毛泽东不但爱看《三国演义》,还喜欢把看到的内容讲给同伴听。少年毛泽东是同伴们中最有才学的人,每当他讲起《三国演义》时,就连村里的大人也情不自禁地前来倾听。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对儿子爱看书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毛泽东聪明伶俐,对读书很有天赋;忧的是毛泽东爱看闲书,怕他受到书籍的影响长大后惹事。为此,毛顺生特地把毛泽东送到韶山井湾里,拜堂兄毛宇居为师,在毛宇居开设的私塾里读书。
当时的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毛泽东却不感兴趣。在毛泽东看来,“四书五经”枯燥无味,而《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栩栩如生,仿佛是一双无形的手,紧紧地揪住了他的心,让他欲罢不能。有一次,毛宇居在台上讲《增广贤文》,毛泽东就把《增广贤文》盖在《三国演义》上面,偷偷地读。因为看得太入迷了,以至于毛宇居走到面前他还不知道。
虽然毛宇居对毛泽东不好好读正书很失望,但学堂里的同学却很喜欢毛泽东,经常偷偷地央求毛泽东给他们讲《三国演义》,为了听毛泽东讲故事,同学们都想尽办法去借来各种古典文学送给毛泽东看,然后通过毛泽东讲故事的方式传授给他们。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四大名著均爱不释手,但《三国演义》是他的最爱。
毛泽东有浓厚的求知欲,无论是什么书,他都喜欢涉猎。广泛的阅读让他视野开阔,深受师生的爱戴。1910 年,毛泽东去县城的东山学堂读书。他只带了一套换洗衣服,此外全是书籍,其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被他端端正正地放在箱子里。
熟读活用《三国演义》
在那个黑暗的社会,毛泽东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名著,一边苦苦地探索中国的前途。毛泽东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他要用革命的火种,去点燃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思想,领导人民去推翻压迫人的旧制度。毛泽东一生都在读书,他是在研究历史,他是在探索真理。《三国演义》是他读了70 多年的书,他对《三国演义》拥有浓厚的情结。井冈山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低谷时期,毛泽东生活异常艰苦,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书籍。读书是他艰苦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每当革命遭遇挫折,他就把自己关起来读书,或者躲在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读书。他在思索中读书,在读书中思索,每一次都会豁然开朗。
若要问毛泽东不但是位诗人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他的军事理论和水平,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三国演义》。毛泽东读了几遍《三国演义》,恐怕连他本人也记不清了。他读《三国演义》,有时候是一本书一次看完,有时候是选择性地细看某一个故事章节。毛泽东每一次看《三国演义》都会有新的见解和收获,这也是他对《三国演义》百读不厌的重要原因。在中国革命最低谷时期,党内的少数左倾主义分子极力诋毁毛泽东,说他是个书不离手的书呆子,说他是用旧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封建主义来指导革命。当时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毛泽东熟读古典文学,熟读《三国演义》,并且引用历史上的典故为今天所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作法。”说得这些人哑口无言。
长征途中借书的笑话
在长征途中,因为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还曾闹出过笑话。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敌人的“围剿”和反“围剿”中艰难行进的,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有时候为了摆脱困境,连吃饭的铁锅都要丢掉,更不要说带书了。为了每天有书看,毛泽东只能东借西借。有一天,红军队伍经过一个村庄,毛泽东命令队伍在村外扎好营地,然后派警卫员去村里借书。
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员说:“小王,你去村里看看有没有读书人,想办法帮我弄‘水浒’和‘三国’来。”警卫员找了几个读书人,其中有一个私塾先生,他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好兵,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听说红军首长需要“水壶”和“三锅”用。私塾先生二话不说,拿出家里的水壶就给了警卫员,可是,他家里实在没有“三锅”,只有“一锅”,但他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一口烧饭铁锅交给了警卫员。
警卫员谢过私塾先生,喜洋洋地把水壶和铁锅带回了驻地。警卫员说:“主席,水壶拿来了,村里人没有一家有‘三锅’,我就借来了‘一锅’。”毛泽东抬头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小王呀,你有空要抓紧学习文化知识才行啊。我要你去借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而不是烧水的水壶和做饭的铁锅。”警卫员听了满脸愧色,他连忙把水壶和铁锅还给了私塾先生,并说明了原委。私塾先生重新拿出了自己珍藏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并叫警卫员带路,亲自把书送给了给毛泽东。
没想到,这位私塾先生也是一个三国迷,当他和毛泽东聊起三国的历史,听见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以及世界形势的发展,分析得头头是道,禁不住无限感慨。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干工作要看《三国演义》”
“干工作要看《三国演义》。”这是毛泽东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的话。毛泽东在看《三国演义》中收获很多,因此,他也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平时多读书,有时间看几篇《三国演义》中的文章,以此提高工作能力。毛泽东是个三国迷,他的许多独特见解来自于《三国演义》,他的许多军事智慧也多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受毛泽东的影响,在当时中共的高层领导圈内,许多领导也都爱上了《三国演义》。1942 年,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时,延安和晋、冀、豫解放区都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古典战争小说,每一场战争都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战术,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军事战术指南。《三国演义》同时是一部残酷的战争史,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博大精深的力量贯穿其中,把《三国演义》带在身上,毛泽东仿佛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寄托,每时每刻都处于一种振奋的状态,所以,每一场重大的战争,毛泽东都学习孔明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毛泽东深深懂得,干革命不能光靠热情,还要靠勇敢和智慧,而智慧离不开知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总是利用战后的空闲时间,教导部队官兵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对于那些文化水平低,或者对读书不感兴趣的战士,毛泽东就引导他们先看《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水平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
建立新中国后,毛泽东仍然对《三国演义》爱不释手。直到晚年,由于眼睛不好,看书明显减少了,但他的枕头下还压着一套《三国演义》。1976年,毛泽东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还时刻牵挂着台湾,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三国演义》里的话把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寄托于后人,他的临终遗言一定能实现!
【西游记】
毛泽东如何从政治视角阅读《西游记》
据说,毛泽东一生都对《西游记》抱有极高的热情,直到晚年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搜集起来互相比对,从政治的视角去阅读这部小说,不能不说是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的一大特点。

《西游记》剧照
从政治的视角阅读《西游记》
毛泽东读《西游记》,和读我国其他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一样,开始是当故事读的,后来就联系我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实际,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理解,去运用,去说明实际问题。
毛泽东是怎样从政治的视角阅读《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的呢?这里,我先向读者介绍一下毛泽东有关的几次谈话。
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写下诗句:“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严峻形势的写照。
1963年7月,中、苏争论进一步公开化。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中央攻击的回击形象地比喻为 “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在斗争的实践中,他号召全国人民“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直接与现实联系在一起,号召人们站在孙悟空一边,保护孙悟空,为孙悟空欢呼,向孙悟空学习,与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作斗争,这是毛泽东从政治斗争视角读《西游记》的一个独到之处。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之所以能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不止。毛泽东爱读《西游记》,这大概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与一些领导干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到《西游记》时都说过,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坚强的信仰。毛泽东还说,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一位领导同志听后认为,毛泽东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不要怕有不同意见,不要怕有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最后总是会成功的。
这是毛泽东从政治的视角读《西游记》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坚定的信念,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团结奋斗,毛泽东对此是极为关注的。
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向《西游记》寻求启示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河中,毛泽东一贯非常重视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在读 《西游记》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个神话故事时,他也非常注意从政策和策略视角去寻求启示。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又一个独到之处。
早在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作斗争时,毛泽东自己曾这样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
这里,毛泽东将孙悟空比喻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西游记》第七回谈到这个神话故事,说孙悟空虽然能够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上尽力翻筋斗,总是翻不出去。如来佛翻掌一扑,将五个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压住。
毛泽东在这里借用这个神话故事说明,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斗争是必然会胜利的。同时还谈到了“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的具体的斗争政策和策略。这里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思想。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中,在谈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时,毛泽东指出: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毛泽东说:“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
最后,毛泽东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883页。)
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用《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孙行者变为小虫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孙行者就是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
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
这里毛泽东又一次谈到《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故事,不过是反其道而用之,把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比作孙行者,把我们自己比作铁扇公主。
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有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时,又一次谈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故事。他说: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武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
“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
许多的政策和斗争的策略,通过毛泽东的口用《西游记》中的人物或故事来加以阐明,说来引人入胜,道来妙趣横生。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一大特点。说到这一点,笔者在这里再向读者介绍一段小故事。
1961年国庆节前夕,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浙江省绍剧团来北京汇报演出根据 《西游记》改编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当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演出。剧情的发展和演员的精彩表演,使毛泽东对这出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演出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始终很有兴致地观看。他时而点头,时而微笑。当演到“天王庙”一场戏时,看到孙悟空被贬,唐僧被白骨精擒住,猪八戒逃走时的蹉步、蹁步、跑跳等夸张动作,毛泽东捧腹大笑。这出戏先后在北京演出多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曾三次观看演出。看了演出之后,他特意写了一首七律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全诗是这样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郭沫若的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唐僧的憎恨,提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毛泽东看到郭沫若的诗后,不同意郭诗敌视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的看法,认为郭沫若对唐僧的看法有些偏激。因此,他于1961年11月17日,也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了毛泽东的这首和诗后,认为毛泽东的诗,气势宏伟,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看问题。他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改正他对于唐僧的偏激看法。于是,于当天又依韵和诗一首《再赞〈三打白骨精〉》:“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千万里明真谛,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警惕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次来!”
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这首和诗后,于1月12日,非常高兴地挥笔在郭沫若这首诗旁边写道:“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浙江省绍剧团的主要演员也挨了整。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对绍剧团著名演员的“解放”工作很关心。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南巡到杭州时,第二天,他就向有关方面询问了扮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美猴王的那位演员的情况。毛泽东十分风趣地问道:美猴王现在是不是还被压在五行山下?9月5日下午,当时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后来,绍剧团的著名演员都很快“解放”了。
这里,毛泽东把“对中间派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对著名演员的“解放政策”,和《西游记》中的有关故事联系起来,话说得不多,但寓意深刻,通俗易懂,字字句句都印在了人们的心中。
【水浒传】
毛泽东常用《水浒》典故和人物,处理日常工作

《水浒传》剧照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尽人皆知的毛泽东对《水浒传》这本古典小说的一句著名的评价。
在毛泽东的读书评语中,《水浒》是一部政治小说。而毛泽东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这本书。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他最早的读《水浒》记载,出自毛泽东自己的自述。在1936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我)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
这段话是最早毛泽东关于读《水浒》的记载。这次谈话中,毛还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在他主持新民学会期间,还曾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
在从事农民运动时,书籍奇缺,但毛泽东仍不放过每次“打土豪”和搜集“战利品”的机会寻找这本书。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凤友回忆,在长征路上,有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毛泽东万事不做,仍然是急着要找一本《水浒》:“……我们进驻了一个地主庄园。战士们高兴地聚在一起,用歌声驱赶着整日行军的疲劳。这时毛主席走了过来,只见他环顾一下院子四周,把警卫员叫到跟前说:‘小鬼,这家人看来蛮富有,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到本《水浒》来,我想用用。’”结果,那个战士给他找来一个大水壶!此事在红军中曾传为笑谈。
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此外,毛泽东还经常引用《水浒》典故和人物,处理日常工作。比如,他把红军游击队里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的人称为“李逵式的官长”。1939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时称: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
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种“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经典,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运用发挥到极致。
同时,他还以《水浒》的经验、教训与他的革命相参照。1939年12月,毛泽东就这样评价农民起义:“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更是系统地总结《水浒》,他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直到建国后毛泽东还颇有感触,他曾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借用《水浒》的故事归纳成一句话:“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在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中,《水浒》也是一个决不含糊的“媒介”。据《贺子珍的路》的作者王行娟记载,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毛泽东与秘书贺子珍海阔天空的议论中,《水浒》就是一个话题。尽管作为一个女人,贺子珍不喜欢《红楼梦》令毛泽东有点遗憾,但她和毛泽东一样,也很喜欢《水浒》。贺子珍之后,江青受到毛泽东的关注,直接原因也是因为她出色地表演了《水浒》故事《打渔杀家》。毛泽东看后,给延安平剧院的编导们写了那封热情洋溢的信: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里、卧室的书柜里一直放有几本不同版本的《水浒》。据逄先知记载,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的时候,还要过《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们先后又送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依照当时登记的顺序,这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是: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1─24册
《水浒传》顺治丁酉冬刻本,1─20册
《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12册
《五才子水浒传》上海同文书局版,1─16册
《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上、下册《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4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66年版,1─20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8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1─100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32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
《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
以上不同版本的《水浒》,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其中李贽作序的《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线装大字本1─20册)和金圣叹评点过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版本。1975年8月,他发动“评水浒”运动之后,还指名要看“李本”。
与战争年代一样,建国以后的毛泽东需要《水浒》,同样因为它能够为他的“内部整合”、“反修防修”和“继续革命”提供经验。
譬如,毛泽东从《水浒》学到了要警惕“腐败”,以及如何处理共产党队伍中的“山头主义”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
“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申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1955年10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谈到犯错误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在毛泽东的晚年,《水浒》更是他意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维拐杖。在林彪事件、陈毅逝世等“重大历史事件”前后,《水浒》都是他不可缺少的朋友。在谈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话题时,毛泽东再次谈到了“三打祝家庄”: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新湖南客户端综合自《毛泽东读书十法》、《党史文汇》、《国家人文历史》、《中华读书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政协报》等)
责编:朱晓华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