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南客户端 2015-10-18 12:20:12
「被誉为曾国藩研究第一人的唐浩明,从曾国藩传世的大量日记中挑选出三百来篇,逐一加以评点,篇幅短小、笔调轻松,由表及里地探索曾氏的内心世界,发表作者的读史领悟。将文、史、哲冶于一炉,通过解读曾国藩日记,窥斑见豹地探索他的文韬武略、待人处世与生活态度,面对困厄与成功时的心态、遇到得宠与失意时的处理方式。
既益智敦品明事晓理,又赏心说日休闲养性。《唐浩明点评曾国藩日记》近期在“新湖南”客户端连载推出,敬请关注!」

■戒烟
□原文
黎明起,走会馆拈香。归,圈《汉书》《冯奉世传》、《宣元六王传》、《匡衡张禹孔光传》。下半天,走雨三处、寄云处、敬堂处。夜归,早睡。是日早起,吃烟,口苦舌干,甚觉烟之有损无益,而刻不能离,恶湿居下,深以为恨。誓从今永禁吃烟,将水烟袋捶碎。因念世之吸食烟瘾者,岂不自知其然?不能立地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拔耳。(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
□评点
曾氏有吃烟的不良嗜好,甚至到了一刻都不能离开的地步,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烟管、佩烟袋,形象已属难看,更重要的是对身体戕害甚大。不只是他说到的“口苦舌干”,更严重的是影响他的肺部。曾氏三十岁时就患有肺病。《年谱》中说他道光二十年进京散馆,正月到的北京,“六月移寓果子巷万顺客店,病热危剧,几不救。同寓湘潭欧阳小岑先生兆熊经理扶持,六安吴公廷栋为之诊治”。
肺病重得几乎要夺去性命,幸亏靠了欧阳兆熊、吴廷栋二人的医治护理,才渡过那道难关。欧阳与吴,也便因此成为曾氏的挚友。曾氏晚年委托欧阳开办金陵书局,他一生最后见的旧友即吴廷栋,生死之交结下来的友谊维持终生。
曾氏以捶碎水烟袋的决绝态度立志戒烟,希望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世间很多吸烟者,都曾经有过戒烟的经历,有的人后来戒掉了,也有人屡戒屡复,最终没有戒掉。曾氏戒掉了吗?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七日日记:“本日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他的日记为此一问作了回答:近一年时间了,他还没戒掉。
■聪明日减,学业无成
□原文
早起,温《诗经》《鼓钟》、《楚茨》。饭后,走俪裳处拜寿。因走蔡春帆处、?仙处、少鹤处。归,阅《汉书》《马宫传》、《王商史丹傅喜传》、《薛宣朱博传》。下半天,小珊来,余走吴和甫处。
三十年为一世。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聪明日减,学业无成,可胜慨哉!语不云乎“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道光辛丑初度日识。(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
□评点
曾氏生于嘉庆十六年,岁次辛未,到了道光二十年,刚好三十岁整。孔子说三十而立,可见三十岁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照世俗的眼光来看,三十岁的曾氏已是“立”得出类拔萃了。但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以“聪明日减,学业无成”来概括眼下的自我处境。对于一个三十岁的人来说,这种衡量标准有点过于苛严。可能曾氏鉴于记诵能力不如早几年,以及尚未有学术专著问世这两个方面来责备自己。这应该说是取法乎上上了。古人曰: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说的是自我要求不妨高些。曾氏之用意亦在此,故而告诫不能“自逸”。
■研幾工夫最要紧
□原文
丑初起,至午门外迎送圣驾,在朝房不能振刷出拜。杨朴庵论《四书》文有诞言。至会馆敬神,饭周华甫处,言不由中。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照。”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以知幾。”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又云:人心善恶之幾,与国家治乱之幾相通。又教予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出城拜客五家,酉正归寓。灯下临帖百字。(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评点
这一天的日记虽然短,但内容丰富。先是对自己本日的所作所为做了三次反省:一是在朝房内精神不振作,二是与人谈论文章时说了虚诞之语(细揣“杨朴庵论《四书》文有诞言”一句,“杨朴庵”前当缺一“与”字),在别人家吃饭时,说了假话。曾氏如此省身,真正做到了《论语》中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接下来,简要记下倭仁的话。
倭仁对曾氏说的这番话,核心在“研幾”二字。幾是什么?幾就是事物出现前或变化前的细微迹象。《易•系辞》说:“幾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举动前之细微,吉凶前之征兆即幾。对这种“幾”细致地考察,详尽地研究,就是研幾。倭仁对曾氏说,人心善与恶的幾微,与国家治与乱的幾微是相通的,道理是一样的。人在恶念初萌时不能遏制,则有可能酿成罪恶行为的发生;国家若不能在动荡征兆出现时予以制止,则有可能爆发大动乱、大灾难。涓涓细流,汇成江海。处在细流时毕竟好改变,一旦成为江海,则不能对付了。恶处于细流时,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有可能知道。此时如果能自我反省,就有可能将它堵塞。故而,一个时时反省的人,只要他是真诚的,便可以杜绝大恶大罪的出现。
最后,倭仁还告诉曾氏要赶紧写日课。所谓日课,即每天将自己这一天来的思想行为予以反思,并记录下来,随时督促。光绪二十六年,偶读曾氏文字后便大为震撼,决心以曾氏为人生榜样的梁启超,在写给朋友叶湘南、麦孺博的信中说:“弟日来颇自克厉,因偶读曾文正家书,猛然自省……弟近日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立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盖此五者,皆与弟性质针对者也。时时刻刻以之自省,行之现已五日,欲矢之终身,未知能否……近设日记,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梁启超这段话,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日课的做法与意义。
■静坐
□原文
辰初起,静坐片刻,读《易•咸卦》。饭后昏昧,默坐半刻,即已成寐。神浊不振,一至于此。读《咸卦》,卦彖辞能解,《系传》释“九四爻”,不知其意,浮浅可恨。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田地方好。昏浊如此,何日能彻底变换也。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饭后,走恽浚生处商公事。灯后,临帖二百字。读许文正公语录,涉猎无所得。记昨日、今日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
□评点
日记说的是通过静坐来澄清昏浊事。静坐可以净虑去杂,让心安定下来,本是佛家、道家修行的重要途径。释迦牟尼静坐菩提树下参悟大道,达摩祖师面壁少林终日默然自修。庄子更认为静坐可以忘记一切,浑然物我是非,这便是著名的道家坐忘。三十二岁的曾氏正处于血气方刚的青春躁动期,外间的应酬繁忙,内心的欲望很多,要想安静的确不易。他的日记中常见的“嚣”、“浊”、“昏”、“浮”等字眼,便是他日常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对此种景况非常不满意,然一旦坐下来,便又想打瞌睡,这很令他沮丧。如何让静坐达到净虑的目的?他总结出“天地位,万物育”的六字体会。
这六个字,初看颇为玄虚,其实恰到好处。所谓天地位,就是天地正位的意思,泛指大脑、四肢、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都处于正常秩序之中。正常秩序就是自然状态,不必做作克制,更不要紧张霸蛮。所谓万物育,就是万物发育,也就是身体内的各种运行畅通无阻,生命处于一种蓬勃盎然的兴旺状态。如同朱熹所说“鱼跃于渊,活泼泼的”,又如曾氏后来所作的联语“养活一团春意思”,说的便都是“万物育”。这既是一种恒常境界,也是一种高尚境界。这样的静坐,方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日记又反省自己今天的不当之处,与朋友谈话有游言、巧言,也就是有无根据、讨好乖滑一类的话,责备自己没有实实在在地改过自新。
■诤友陈源兖
□原文
一早,心嚣然不静。辰正出门拜何子敬,语不诚。至岱云处,会课一文一诗,誊真,灯初方完。仅能完卷,而心颇自得,何器小若是!与同人言多尖颖,故态全未改也。归,接家信。岱云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着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天头:直哉,岱云克敦友谊。默坐,思此心须常有满腔生意;杂念憧憧,将何以极力扫却?勉之!复周明府乐清信。利心已萌。记本日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评点
古人有诤友、畏友之说,意谓能直言规劝、令人敬畏的朋友。日记中提到的岱云就是这种诤友、畏友。岱云姓陈名源兖,湖南茶陵人,与曾氏为同科进士、翰林,关系密切,后又结为儿女亲家:曾氏次女纪耀嫁陈氏次子远济。陈源兖品学俱佳,然命运并不太好,咸丰三年死于安徽池州知府任上,年仅四十一岁。
陈源兖指出曾氏三个缺点:一是对人怠慢,二是恃才自负,三是处事刻薄。能如此直爽、如此不讲情面地批评人的朋友,现在已经不容易见到了,而像曾氏这样把别人的批评记在日记上,心悦诚服地接受,并称之为“药石”的朋友,现在可能更难找了。这三条批评,对曾氏震动不小,甚至可以说他一生都在以此为警戒。他后来为人处世的谦虚谨慎、大力提倡恕道,特别是晚年将书房命名为无慢室等等,都可以看到陈源兖之诤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
此篇还检查自己的“语不诚”、“器小”、“杂念憧憧”、“利心已萌”等毛病。其中所说的“满腔生意”,又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万物育”的静坐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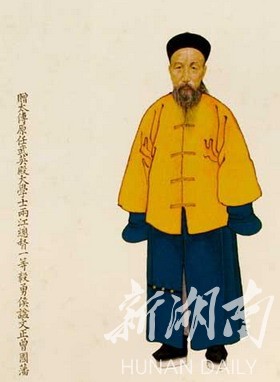
责编:李婷婷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