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1-02-11 16:35:05
年味
文/何云波

一
孩子上一年级时,经常为背书发愁。课本里有一篇《春节童谣》,并不是正式课文,只要求“和大人一起读”,孩子却每次都念得兴高采烈,不知不觉就能背下来了: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
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磨豆腐。
二十六,去买肉。
二十七,宰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
初一初二满街走。
也许,这里面就有着中国许多孩子曾经的共同记忆。
年味,就是童年的滋味。
小时候盼过年。因为穷,平日里天天吃红薯丝饭,喝真正的看不到几粒米的稀粥,青菜里难见油星,偶尔有客人来,能吃到一次肉,那仿佛就是“过年”了。
而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要过年了。家家开始磨豆腐,酿米酒,炒花生,南方不蒸馒头,而是用糯米做糍粑。如果碰得好,还可以杀年猪,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杀猪,对普通人家来说,是个浓重的仪式。丰腴的日子,需要请亲友一起来分享,几大碗猪头肉、猪内脏、血灌肠(将新鲜的猪血灌进洗净的大肠中,再清水煮熟)、油豆腐,然后,满屋都是肉香了。
对孩子来说,那也是最幸福的一天。因为可以敞开肚皮,饱餐一顿肉了。
终于到了除夕。一大碗走油肉(新鲜的半瘦半肥的肉,在油锅里炸得金黄,然后切成大块,放佐料煮熟,一块就有一、二两),一块肉下肚,一年的饥饿,在那一刻终于有了饱满的感觉。
然后就是守岁,中间几次瞌睡又醒来,等着深夜12点,新年的钟声敲响,父母给压岁钱。一、两毛钱,就是巨款了。
大年初一,清早起来,除了放鞭炮,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拜年。同一村,无论是否沾亲带故,都上门去,叫着拜年了,拜年了,主家便会热情地拿出一些花生、瓜子、红薯片之类,或者半块红片糖,塞到你的口袋里。慢慢的,各个口袋都丰盈起来,然后回家,把这些美食倒出来,再兴冲冲地出门,继续拜年了,拜年了……乐此不疲。
春节对孩子最有吸引力的,还有跟着大人走亲访友。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走姑表……初一在爷爷奶奶家,初二去外公外婆家,初三开始去叔伯、姑表家,拜年。去某舅、某姑家,一般堂兄、堂弟、表兄、表妹们都会约到一起,浩浩荡荡,过田野,走山路,早出晚归,那种热闹的气氛,许多年后想起来,还念念不忘,如在眼前。年味,成了人生的一份绵绵的回味。
二

上大学,离开了故乡,年味,便成了一缕动人的乡愁。
放假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家。
在湘潭上学,离假期还有好些天,便开始掐着指头,算着放假的日子。好不容易熬到那一天,上午刚考完,下午便收拾行李,回家。
回家,从湘潭坐汽车到株洲,等到深夜,绿皮火车终于慢吞吞地来了。人山人海,好不容易爬车窗进去,在煮人肉饺子一般的车箱里,杵着,火车晃晃荡荡,慢慢悠悠,每站必停,一停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晃动,十几个小时,下午终于到了郴州,第二天回县城车票,早已售完。在小旅店里对付一夜,早上,想方设法,连蒙带骗,机智勇敢,百折不挠,混过检票口,到了车门前,拿出学生证,跟随车的售票员好说歹说,对方看你是大学生(那个时代,大学生还是稀罕之物),终于开恩,帮你补一张站票,然后站着,三、四个小时,颠簸到县城。再赶小中巴、小三轮之类,到镇上。离家还有十几里路,就只能完全靠全自动的两条腿了。有一年到了镇上,天已黑,只能去邻村嫁到那里的一户人家,敲门,过夜。还有一回,下着雨,一手打伞,一边挑着两个行李袋,快到家了,一滑溜,行李落在了水田里,自己也一身湿透。
不出省,三百多公里的路程,竟要奔波三天。即使这样,也阻挡不了回家的热情。因为那里是故乡,有母亲,有亲朋故旧,有浓浓的年味。
后来,在城里结婚成家。回家过年的时候渐渐少了。有时,在城市的阳台里,一个人望着星空,出神:
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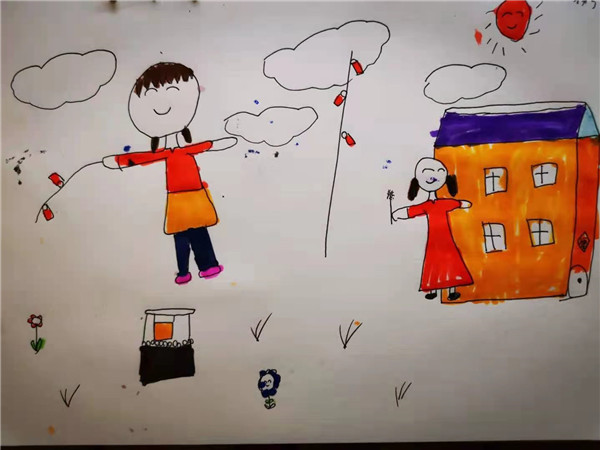
慢慢地,年味就淡了。
甚至,年味里有了一些中年的苦味。
小时候,盼着过年。终于盼到了,年过了一半,心里便会生出一些失落。过了元宵,便开始掐着指头,算着下一个“年”的到来。
结婚生子,孩子慢慢长大,自己也成了孩子眼中的大人。上有老,下有小,拿着那点微薄的薪水,平时日子就过得紧紧巴巴,回到故乡,你却成了乡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各种的拜年、应酬,一天喝四、五场酒是常事,猜子划拳,喝得兴高采烈、热闹非凡,有时也喝得人仰马翻、疲惫不堪。世故人情,花费自然也不少,结果能孝敬父母的银子,反而微乎其微了。还有,大年三十陪父母,然后就再难在家,一家人安安静静吃餐饭了。心里负疚着,过年,有时便成了一种负担。
而在城里过年,跟平时日子没什么区别,又寡淡无味,然后,又会怀念起乡村过年的热闹,那份累并快乐着的滋味。
后来,父亲不在了,母亲也住到城里来了,故乡的年味,便变得越发遥远了。
有时,过年时,因为还有一个弟弟在老家,母亲坚持要回去。我们便劝她,你看,你一个人回去,家里亲戚又多,你都要招呼,不嫌累啊?
母亲不说什么,却仍然执意,回乡过年。
后来,母亲过不惯城市的生活,索性回乡下常住去了。
母亲在哪里,“年”就在哪里?
然后,回家过年,又成了生活的一种常态。并且,日子渐渐地好起来,衣食无忧,交通也方便了,乡村公路通到了家门口,开车三个多小时就到家了。回乡,也就不再是一种负担。
小年那天,母亲打电话来,说家里要杀年猪了,老三家养了好多头猪,纯大米青菜喂养,还种了禾花稻,稻田里养了禾花鱼,纯天然无污染,就等着你们回来了。
因为又一次汹汹而来的疫情,想起去年的惊魂,我犹豫着,说看情况再说吧!
然后,好几天,一个声音说:响应号召,就地过年。
内心却总有另一个声音,仿佛那远山的呼唤:回来吧,回来吧!
归去来兮。原来,年味,就是那无尽的亲情的滋味啊!
四
其实,年味,就是人生的况味。
童年的期盼,少年的乡愁,中年的苦味,老年的守望,都在其中了。
曾经,孩子最喜欢课文里的一篇《春节歌谣》:
春节到,真热闹,
家家户户哈哈笑,
黄狗帖春联,山羊把地扫,
猴子买糖果,花猫蒸年糕,
公鸡大婶撮元宵,
松鼠宝宝剥花生,
你来舞龙灯,我来踩高跷
三只老鼠来拜年,
穿着新衣戴新帽,
放起烟花噼啪响,
恭喜恭喜春节好!
这歌谣一下子唤起童年的许多记忆。
尽管如今,连乡下也没有了往日过年的那份热闹。但是仍然架不住许多人回乡过年的那份冲动。
对于那些离乡打工的人来说,只有故乡,才有真正的年味。因为那是他们的家。
而对于我等早就离开了故乡的人来说,父母在,故乡就还在。你就有“家”可回。
哪一天,如果父母也不在了,连接故乡的那根线,也许就断了。
有在长沙的亲友写《家@回家》:
腊月二十八,距离过年还有两天了,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已经渐渐稀少,早点铺,各种饭店的老板也渐渐停业了,诚想可能是很多单身的、成了家的、有父母健在的人都提前回家过年去了吧!
我的灵魂也跟着钟声的将近快飞走了,但肉体还要坚守,原地过年,因为,生养我的父母早已云端仙游,老家已是故乡。而我的栖身之地,亦是女儿孙辈之想回的家。
然后,你不再有可回的“家”,你就是“家”,你就成了孩子的归属与期盼。
然后,人生留给你的,就如同你的父母曾经的那样,日日,年年,年味就成了苦苦的守望。
责编:曹漾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