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晨报 2025-10-25 07:41:53
科学巨匠何以“归来仍是少年”
杨振宁传记作者林开亮:我们把“宁拙毋巧,宁朴毋华”这句话放在了书的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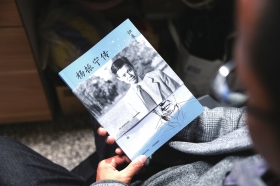 《归来仍是少年——杨振宁传》。组图/记者杨旭
《归来仍是少年——杨振宁传》。组图/记者杨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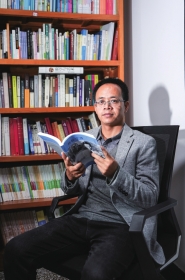 林开亮。
林开亮。
本报记者周诗浩北京报道
10月的北京,天高云淡。24日清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前,人们手持素菊,面色肃穆,安静地排成长队。
他们都是来送别10月18日逝世的世界知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杨振宁先生。一颗探索了宇宙至理一个多世纪的伟大心灵,停止了跳动,一个时代的故事,也在此画上了句号。
然而,故事的终章,往往也是回望的起点。正如杨振宁最喜爱的诗人艾略特的诗句所述:“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魂归故里,臻于圆满。先生虽已离去,但他之于科学的求索精神,之于家国的无限情怀,早已点亮许许多多后辈的前行路。
在前来送行、缅怀的人群中,刚刚出版的《归来仍是少年——杨振宁传》的作者林开亮,感触尤为深切。这位与杨振宁有着十余年“忘年交”的数学科普工作者,他手中的传记,此刻承载着更重的分量。
“‘宁拙毋巧,宁朴毋华’,这是伴随杨振宁一生的治学格言,我们这次也把这句话放在了书的扉页上,这也是对这位世纪智者一生最好的注脚。”林开亮说。
从“冒昧邮件”到“忘年之交”
2012年,来自常德的29岁博士生林开亮做了一件在旁人看来颇为“冒昧”的事——同时给时年90岁的杨振宁和89岁的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发去邮件,提出想做两位科学家的比较研究。
“没想到两位都很快回复了,杨先生还给我打了电话,约我去清华见面。”回忆起十三年前的初遇,林开亮眼中带光。
在清华大学科学馆的办公室里,年轻的数学研究者与耄耋之年的科学巨匠一见如故。“我们的初次见面并没有金庸《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巧遇风清扬那么传奇,却有如阿拉丁神灯梦幻般被点亮了的感觉。”林开亮回忆说,“当我在沙发上坐稳以后,杨先生首先问我叫什么名字,并让我写下来,然后慢慢地问我,是哪里人、导师是谁、研究什么……语气平和温暖,我们当天聊了很多数学相关的话题,当天杨先生给我的感觉可以用‘春风大雅能容物’来形容。”那次见面,杨振宁送给这位湖南小伙许多珍贵书籍,包括他本人的论文集。“他那里有的、我想要的书,都给了我。”
“当我骑车返回,从清华园出来时,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我看到的杨先生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长者,我印象中的杨先生始终是一个正当壮年、意气风发的杨振宁。这是因为,杨先生一直没有停下脚步,上下求索于大自然的微妙。”林开亮表示。
这份始于“冒昧”的缘分,也改变了林开亮的人生轨迹。他后来在杨振宁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弗里曼·戴森的传记文章,并得以发表,这成了他科普事业的“名片”和“处女作”。此后,杨振宁连续四年邀请林开亮到清华访问,为他提供研究环境,不断鼓励、提携他,甚至提议合作写文章、翻译著作,“他是真心实意为我考虑,希望我能发展得好”。
“有一次,我博士毕业参加工作后回京出差去拜访他,许久不见后,杨先生先问起我在陕西高校工作的概况,而后跟我提起作家贾平凹,他特别提到了当时他正在读的《带灯》。他说贾平凹写出了陕西人的市井生活,如果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会考虑给他……”
回忆与杨振宁交谈的过往画面,林开亮感慨道:“他这种对后辈的温暖关怀,与后辈推心置腹地交流,只是为了见证年轻人的成长,而不要求立即出成果,这是真正的忘年交。”
一次出版邀约与一份深藏的情谊
谈及为何由自己来为杨振宁写传记,林开亮坦言,他最初是拒绝的。“杨振宁先生的传记,业内已经出过,其中作家江才健花费四年心血写就的《杨振宁传》,在我心中就像一座高山,我觉得很难逾越。”
思想的转变来自两方面。一是来自湖南教育出版社编辑的诚意:“出版社希望找一位年轻的作者,为青少年群体创作,他们认为我是最恰当的人选。”二是林开亮内心的触动:“某种意义上讲,我欠杨振宁先生一个很大的恩情。他之前对我的特别关照、鼓励让我感念很深,而且编辑也说得对,在国内可能确实找不出一个比我更适合为青少年写杨先生传记的人了。”
林开亮多年从事数学科普,常在报告中讲述科学家的故事,掌握许多关于杨振宁的一手材料,拥有独特的见解。“我想为青少年还原一个‘真实完整’的杨振宁,也希望我们的青少年读者,通过这部作品读懂这位科学巨匠的百年科学人生。”
在这部传记中,林开亮在讲述杨振宁的科学成就时,没有陷入晦涩的理论阐述,而是巧妙地将规范场论、杨-米尔斯方程等专业内容以生活化的类比来描述。“比如讲述‘杨-巴克斯特方程’,配图中,我用生活中‘编辫子’的过程来解释——三股头发经过六次交叉回到原点,这就是方程的核心思想。”在描写杨振宁的人生经历时,林开亮也展现了捕捉细节的敏锐眼光,西南联大时期历历在目的片段、远渡重洋时的踌躇满志和坚定信心、1957年获诺贝尔奖前前后后的点点滴滴、与邓稼先重逢时的真情流露、晚年在清华园晨练时的感慨,这些零散的生活片段,都被他编织成表现杨振宁精神世界的重要线索。“我始终相信,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那些充满温度的生活细节,这些看似微小的片段,恰恰是理解他科学成就与家国情怀最重要的钥匙——因为最伟大的科学,源于最本真的人生。”
林开亮介绍,这次在《归来仍是少年——杨振宁传》中,还特别设置了“亲笔篇”,收录了杨振宁亲笔撰写的五篇小传。“包括陈省身、吴健雄、邓稼先和他的父亲杨武之,还有一篇杨先生自己写的小传,也是首次出版……他敬重陈省身的数学才华,钦佩邓稼先的奉献精神,而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更是深远。”林开亮说,“杨先生身上有一种儒家气质,这种精神种子正是父亲种下的。”林开亮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来表明“亲笔篇”的选择,“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一生中最主要的东西,正是在于他所想的是什么和他是怎么想的,这个附录就是杨先生的价值观地图——他看重什么品质,敬佩什么样的人。”
难以逾越的“高山”与不得不做的“取舍”
撰写大师传记,挑战不言而喻。
在林开亮看来,公众对杨振宁存在一些空白和误解。“我最初关注杨先生时,社会上热议的是他与李政道先生的‘分合’,以及晚年那场婚姻。但在学术圈,我们更关注他的思想。”
对于那些复杂而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广为人知的“李杨纷争”,林开亮表示“这是一个很难讲、也讲不清楚的话题”:“首先我们是局外人,其次那段历史非常复杂,我们并非当事人,也无法还原真相。”最终,林开亮选择诗意地“回避”:他在书中引用了“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来表达遗憾,而未着墨于具体细节。“我想请青少年读者原谅我没有能力讲出这个故事。”
相比之下,对于杨振宁与翁帆女士的婚恋,林开亮觉得自己处理得更为顺畅。他引用了翁帆在访谈中的一段话:她最喜欢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未选择的路》——“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让我的人生如此不同。”
“这段话让我产生了深深共鸣。”林开亮说,“其实选择做科普,选择一条更少人走的路,心境是相通的。感情的事,主要看当事人,翁帆女士的付出,让杨先生得以安度晚年,时间会证明,这不仅是一段罗曼史,更是一份深厚的、相互成就的情谊。”
而更重要的,是澄清杨振宁的爱国情怀。“很多人因为杨振宁先生晚年归国,认为他是回来养老的,这是很大的误解。”林开亮引用了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的评价:“杨先生有两颗心,一颗是做伟大物理学家的心,一颗是做一个热爱中国的中国人的心,这两颗心在他身上合二为一。”
为佐证这一点,林开亮分享了一个杨振宁亲口告诉他的“震撼瞬间”。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到阔别二十六年的祖国时,他急切地想向好友邓稼先求证:“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当他最终得到邓稼先“除了早期苏联的极少援助,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的肯定答复时,杨振宁热泪盈眶。
在离别的信件中,好友邓稼先在结尾化用苏轼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这句词深深烙刻在杨振宁心底,他明白“共同途”的深意——“无论身在何方,心系同一片土地;无论选择哪条路,终点都是祖国的繁荣富强。”五十年后,在自己百岁诞辰的演讲上,杨振宁以“千里共同途”为题,深情回应了这份嘱托,这个画面,也定格了两颗赤子之心。“这份深藏在历史褶皱中的家国情怀,正是我们这本书想要传递给年轻读者的精神内核。”
“归来”与“少年”的精神传承
“归来少年”与年过百岁的科学大师联系在一起,看似矛盾,背后却藏有深意。“它不仅是这本传记的标题,更是对杨振宁跨越世纪仍不改初心的科学赤子情怀最生动的诠释。”林开亮说,杨振宁的赤子之心,历经百年风雨愈发鲜明,“这也展现出他对科学的纯粹热爱、对祖国的深沉情感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西南联大时期,在烽火连天、物质匮乏的峥嵘岁月里,战火未能磨灭杨振宁对知识的渴望,反而坚定了他追求科学真与美的决心。“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也在演讲中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面对海外优越的条件,他始终心系故土,从搭建中美学术桥梁到晚年毅然放弃美国国籍、全职归根清华,每一步都印证着他跨越半个世纪的家国情怀。”
在林开亮看来,“归来”不仅是地理上的回归,更是精神上的“认祖归宗”,是“少年”誓言的最终兑现。“杨先生曾多次与我讲过‘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要当数学家’的肺腑之言,这不仅道出他对知识永不满足的探索精神,也让那股‘少年气’中彰显着对科学传承的执着和热爱。”
“从整个宇宙结构讲起来,人类的生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个个人的生命那更是没有什么重要的。”这是杨振宁对于生命的解读,也让林开亮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起初听到这句话,会感到一种宇宙尺度下的苍凉与渺小,”林开亮坦言,“但当我合上先生厚重的传记,再回味这句话,感受到的却是一种释然与激励。”
林开亮说,杨振宁留给世人最宝贵的遗产,是一种精神偶像的力量。“他让你相信,我们中国人是可以在科研上做到世界顶尖,可以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他曾说,‘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不如人的心理’。我们对一位大师最好的致敬,不仅是记录他的一生,更是让他的精神通过我们的笔触,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采访临近结束,林开亮还谈到了他不久前离世的父亲,言语中流露出深深的怀念与遗憾。林开亮第一次拿笔是父亲教的,如今著书立说,却无法亲手奉上。林开亮还动情地回忆起传记中的一段描写:1957年,杨振宁与分别十二年的父亲在日内瓦重逢,看着年迈的父亲与小孙子在公园发现“秘密通道”,一老一少准备出门时,父亲对镜梳头,儿子欢呼雀跃,“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只有当了父亲、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才能深切体会这种幸福。”林开亮说,当时他读到此处,便迫切地想带自己的孩子回去见见爷爷,可惜终未如愿,成为心中“月有阴晴圆缺”的憾事。
谈及杨振宁先生的离去,林开亮显得更为平静。“杨先生给我的精神,已经融入我的骨子里。他在与不在,那个精神都在我身上,也会通过这本书,传递给每一位读者。”
责编:周秋红
一审:唐煜斯
二审:唐能
三审:文凤雏
来源:潇湘晨报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