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霖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5-10-16 08:56: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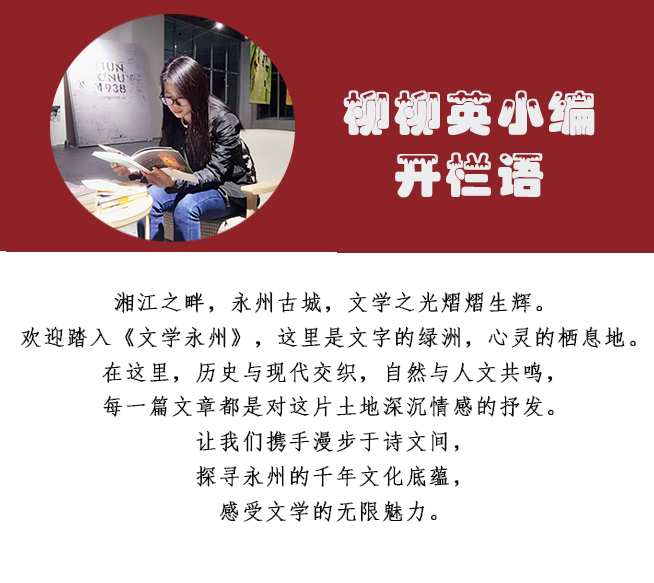
父亲的担当
■王霖
我永远记得父亲晚年坐在阳台上的样子。
南方的晨光,总是慢悠悠的,带着水汽,透过那扇绿色的纱窗,在他花白的鬓角上踱步,柔和得像一首无声的诗。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目光穿过栏杆,投向远方,仿佛在检视一条由他亲手铺就、却再也无法重走的路。而我的目光,则落在他那双搭在膝头的手上——一双布满了沟壑与故事的手。
这双手,曾在刺骨的井水里搓洗过岁月,曾在粗糙的粉笔灰中握紧过未来,也曾与砂石、泥土、滚烫的沥青搏斗了半生。
1、透明胡萝卜
记忆的闸门,被一句轻轻的问话冲开。
“爸,那时候,苦吗?”
他转过头,目光穿过几十年的烟尘,异常清澈地看着我,摇了摇头:“不觉得苦。那是我的娘啊。”
那一刻,时光仿佛倒流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那个湖南湿冷的冬天。
十二岁的父亲,蹲在院角,对着一口破旧的搪瓷盆。盆里是浑浊的、泛着异味的井水,水面上,几块薄冰像命运的碎片一样漂着。他那双小手,在冷水中浸泡、搓揉,从通红到肿胀,最后,竟冻得像一根根透明的胡萝卜,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折断。
奶奶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爷爷远走他乡谋生,空荡荡的家里,只剩下这个沉默的男孩,守着他气息奄奄的娘。
邻居阿婆挎着菜篮经过,总要停下脚步,叹一口气:“造孽啊……这么小的伢子,当成大人用。”父亲从不回应,只是把头埋得更低,紧紧咬着下唇,更加用力地搓着手中的布料,那“唰唰”的声响,是他对苦难最早、也最倔强的回答。
洗完衣服,他还要踮起脚,在灶台前生火,为奶奶熬那一碗碗墨汁般苦涩的中药。他总是先自己尝一口,试试温度,再小心翼翼地扶起奶奶羸弱的身体,一勺一勺地喂下去。夜晚,在一盏跳动的煤油灯下,他铺开作业本。昏黄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瘦,像一个过早承担了生活重量的问号,在墙壁上无声地书写着坚韧。
奶奶去世前一晚,忽然异常清醒。她看着眼前这个瘦小却撑起了整个家的儿子,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嘴里喃喃的,全是愧疚。十二岁的父亲,紧紧握住母亲干枯的手,说出了那句让我一生都为之震动的话:
“应该的。因为您是我的娘。”
一年后,十三岁的父亲,永远地失去了他的母亲。
 本文插图由AI生成
本文插图由AI生成
2、 讲台与公路
生活的重担,催着他飞速长大。为了生计,他放下了心爱的书本。十八岁那年,他站上了乡村小学的讲台。
家里那张泛黄的照片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身形单薄,但眼神里的光芒,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据说,台下坐着的学生里,有好几个个头都比他高。可当他转身,在黑板上郑重地写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整个教室都安静了。他教语文,也教算术,把每一个字、每一道题,都讲得一丝不苟,仿佛要把自己错失的知识,全部灌注给这些孩子们。
然而,教师微薄的收入,终究撑不起现实的风雨。两年后,当公路段招工的机会摆在面前时,他犹豫了。我猜想,他一定在无数个深夜里,反复摩挲过那些叠得整整齐齐的教案,凝视过窗外他教孩子们认识的星空。但最终,抬头看看家中渗水的屋顶,他还是做出了沉甸甸的选择。
离开学校的前一晚,父亲在他的教室里坐了一夜。天蒙蒙亮时,他将那些一笔一画写就的教案,在讲台上码放得整整齐齐。然后,他走向那站立了两年的讲台,教室里空无一人,只有歪斜的桌椅。他清了清嗓子,像平时上课那样,对着空荡荡的教室认真地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上最后一课……”
话未说完,这个十八岁的青年已然哽咽。他深深地、郑重地对着他的讲台,对着学生们的座位,鞠了一躬。抬起头时,脸上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晨露。
许多年后,他和我聊起这事,自己却先笑了:“你猜怎么着?我当时正鞠着躬,我们班那个最皮的学生,趴在窗户外面看见了,吓得扭头就跑,第二天逢人就说,‘王老师是不是气疯了,在给桌子鞠躬呢!’”
这个带着泪花的笑点,让那段沉重的往事,瞬间有了温度,也父亲的形象,从一个悲情英雄,变回了一个有血有肉、会窘迫也会怀念的普通人。
从此,父亲的生命便与公路段的砂石、泥土和滚烫的沥青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童年记忆里,他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特殊的沥青味。那不是污浊,而是奋斗的印记。他常带我们去工地,指着那新铺的、乌黑发亮的路面,用一种近乎虔诚的语气说:
“崽啊,你们看这路。要我说,路就是躺下的碑,碑就是竖起的路。”
那时我不懂。直到多年后,我驾车飞驰在他参与修建的公路上,看到路旁昔日闭塞的村庄建起了新楼,开起了商铺,孩子们能顺畅地去往远方,我才猛然惊觉——父亲他们修的啊,哪里是路,分明是一个时代奔涌向前的血脉,是通往未来的希望。
3、 石子与金融
为了供养我们兄弟上学,每个寒暑假,父亲都会带着我们去锤石子。
工地上,烈日炎炎,我们坐在小马扎上,挥舞着小铁锤,将大块的石头砸成合乎规格的石子。汗珠滴落在滚烫的石头上,“刺啦”一声就化作白烟。父亲的手掌,老茧叠着老茧,他锤得又快又准。休息时,他喝着凉白开,看着我们,郑重地说:
“记住,国家好了,路通了,咱们的小家,才能真正好起来。”
这句话,像他锤下的石子,坚实而朴素,成了我们家的座右铭。
一九八七年,我面临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与我长谈。他敏锐地感觉到,国家要发展,经济血脉必须畅通。他建议我:“报考湖南财经学院,学金融吧。未来,国家需要这个。”
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并幸运地被录取,成了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临行前,父亲在车站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只嘱咐了一句:“好好学。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4、 铺路石与杜鹃红
后来,父亲成了公路段的负责人。他力排众议,重用有真才实学的技术员,因为他深知,事业为重,人才是根本。
退休后,我们本以为他终于可以安享晚年。可黄田铺镇的党委书记来请他修驾校前的路,他二话不说,背起工具袋就去了工地,全程扑在那里,分文未取。双牌阳明山修建上山公路,领导请他做技术指导,他也义无反顾地重返大山。
然而,当我的女儿上学路途遥远,需要他回来帮忙时,他只接到我一个电话,便毫不犹豫地放下了手头的一切。在他的天平上,家与国从来一体,而对家庭的责任,是他最无法推卸的担当。
他总是叮嘱我们,在岗位上别忘了为国家出力。他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修了多少路,而是把我们几个子女,都培养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他是在回来后的第十个春天离开的。
如今,我驾车行驶在阳明山那条蜿蜒的盘山公路上。这条路上,浸润着他的汗水,镌刻着他的智慧。我将车停在山巅,走下去,站在云雾缭绕处,看着漫山遍野、如火如荼的红色杜鹃,迎风怒放。
那一刻,泪水毫无征兆地奔涌而出。
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生于苦难,长于奋发,一生历经坎坷,却始终用沉默的脊梁,背负着“孝悌”“忠信”“仁爱”与“担当”,步履不停。他们不曾有过惊天动地的伟业,他们只是一块块平凡的铺路石。但正是这无数微小的坚持,这日复一日的负重前行,汇聚成了推动我们这个民族走向复兴的、最磅礴的力量。
如今,我们兄弟几人仍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他的孙女,站上了三尺讲台,圆了他最初的梦;他的大孙子,投身于高新技术研发,奔赴在新时代的征途上;他的小孙子,学业优秀,拿到了国家级的奖项,未来可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每一代人,都是后人的铺路石,都用青春、汗水和生命,去铺就那条通往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而我的父亲,他只是万千铺路石中,沉默而坚实的那一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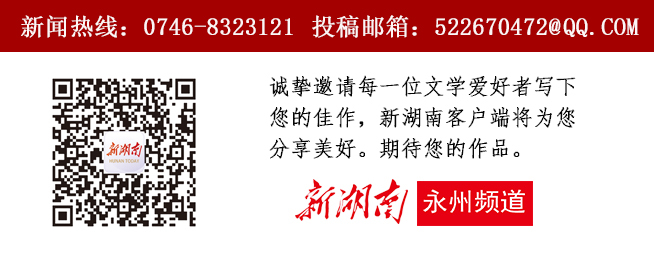
责编:黄柳英
一审:黄柳英
二审:严万达
三审:李寒露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