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30 11:37:46
文/聂茂 毛远影
何石作为湖南乡村题材文学创作颇具影响的实力作家,其创作始终关注湘西地区的山乡巨变、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主题,是湖南新乡土文学创作的标志性人物。在谈及自己在文学中的故乡情怀时,何石说:“回眸我的创作,真正满意的还真就是那些故乡题材的作品。”在他的笔下,始终萦绕着“和着泥土的芬芳”、描绘着“群山一样真性情的乡里乡亲”,这种深入骨髓的故土思念已经化为了何石作品的独特气质。从《大山的儿子》《山那边的那边》《小渡风流》,到《将心比心》《那山那村》《掰腕》,何石的文字不仅生动展现了故乡崀山乡村的时代风貌,更深刻体现出一名大山儿女对乡村振兴的深刻理解与人文关怀。
作为何石的最新力作,长篇小说《驻村冻江源》延续了其一贯的创作主题,将视角聚焦于袋子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新农民”风貌与“新农村”变迁。作品通过宏观的组织策略与微观的人际交往,立体地呈现出一个鲜活的、发展的、呼吸的袋子田村。在这个鸡犬相闻、溪山如画的乡村图景中,何石深入挖掘了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出现的新矛盾、新形象与新路径,既在实践意义上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行的经验分享,也在文学意义上展现了与时俱进的新乡土文学叙事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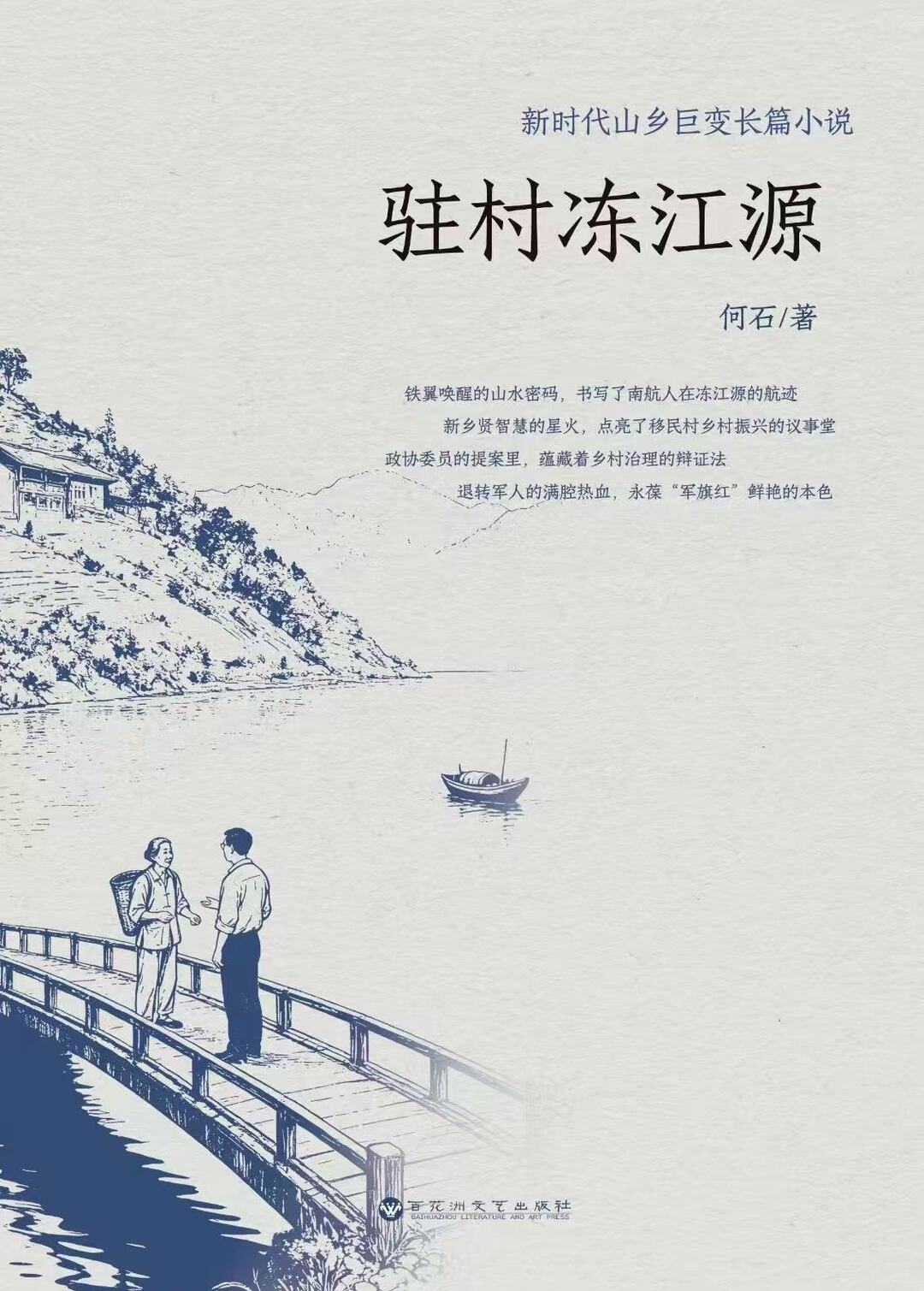
一、“新乡土”发展中的“新矛盾”
“乡土文学”最早是鲁迅提出来的概念,新文化阶段的乡土文学之“乡土”,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抽象化的概念,即远离乡村的作家对乡村意象的一种重构式的想象和表达。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这样阐释“乡土性”: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种解释下的“乡土性”具有与“现代”“城市”“西方”对立的某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所呈现的中国乡村寄寓了一种具有固定文化属性关系的“综合形象”,也就使得这个时期的乡土文学是为了揭示国民性,唤醒受压迫的国民而存在。
在经历了以阿Q为代表的“旧”乡土文学之后,乡土创作在40年代迎来了农村题材的“总体性目标”的转型。又在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和不断提升的基本国情中,孕育出了脱胎换骨的“新乡土文学”。所谓“新乡土文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乡土文学,其最终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乡土中国的转型,完成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这是一种热烈且全新的乡村叙事,相比起传统的乡土文学更具有细节上的真实体验、主题上的与时俱进、技巧上的融合突破。作为新时代产物的“新乡土文学”,虽然脱离了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创作的功利性和教条化,但迄今仍然没有达到成熟的文学体系应有的高度:困囿于旧的乡土主题而没有对新问题探查的敏感度、缺少“高于现实的高贵的诗意”“真诚的大爱”“诚恳的关怀”“怦然心动的感动或会心一笑的理解”。如何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挖掘独属于乡土中国的真实与崇高,是新乡土文学的破茧,也是乡土文学的重生。
作为新乡土文学的破局之作,《驻村冻江源》首先观察到了乡村振兴中出现的“新矛盾”。
为了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九大强调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所谓“乡村振兴”,是与“乡村衰落”相对而言的:乡村衰落是工业化前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它伴随着生产方式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以及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超越。在这一过程中,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在发展中遗落了农村,农村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导致工业化成果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了显著的差距。这种差距使得农村在相对运动中呈现出一种落后的状态,正如书中大塘村为了响应国家水利建设的号召而迁居至偏远的山窝之中,尽管水库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大塘村民们却面临着诸多陈年难题。“乡村振兴”正是为了扭转这一趋势而出现的策略。
在时代巨变中,乡村振兴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举措,也衍生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矛盾”。何石以其敏锐的文学触角,精准把握了这些矛盾,并通过“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叙述方式,将其真实而深刻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袋子田建设的两个首要矛盾,在曹劲松和黄大牛的酒桌上就被明确地指了出来:重修鸭婆桥和恢复大塘小学。前者表面上是交通阻塞的一般性问题,实际上是关系着大塘对外交往贸易、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的关键“要塞”。而恢复袋子田小学,则是所有扶贫乡村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教育问题,它关乎乡村未来的希望与孩子们的成长。唯有解决这两个关系人民幸福指数的根本问题,我们才能谈未来、谈发展。在曹队长为首的南航队伍帮扶下,袋子田迈出了全面振兴的第一步。
但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第一步”并非轻而易举,南航在袋子田的每一步部署都充满了坎坷与挑战。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种地方性局限了人的思想、行为、习惯,让他们对长期保持的现状和历史坚信不疑,这也构成了我们乡村振兴的一大难题:如何打破陈旧的思维模式与矛盾,将积极、新颖且现代的观念引入农村地区。在《驻村冻江源》中,黄一先便是这样一位深陷守旧泥潭的“顽固分子”。他自诩为掌握奇门异术的“半仙”,对自己的名声与风水之说极为看重,以至于坚决反对挖山修路的计划。面对这样一个好言难劝的死疙瘩,曹劲松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策略。他先是巧妙地利用人工降雨,实现了黄一先梦寐以求的呼风唤雨之愿,后又促成黄一先和徐五娘的一桩晚年婚事,彻底转变了这位老顽固的态度,为后续的乡村振兴工作扫清了障碍。
除了“人”的障碍,大塘振兴也经历了“策”的偏差,在首轮精准扶贫中,袋子田也进行了生态水稻、红薯等农副产品的种植工作,还成立了袋子田开发公司。但成果颇少,并不成气候。南航队伍敏锐地总结了经验,开始就脐橙为切入点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生产,成功扭转了局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面对亟待解决的袋子田特色“新矛盾”,《冻江源》从生态、技术、历史、文化的四维发展角度给了我们答案。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特别设立的“乡风文明和庭院美化建设专干”这一职位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不仅让刘小五从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转变为一位积极倡导卫生、爱护环境的乡贤典范,还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袋子田乡村卫生环境的整体改善,使得袋子田村面貌焕然一新。在文化与历史建设方面,何石更是苦心埋下了许多伏笔,从求雨情节就开始介绍杨再兴的历史,到永莲寺锁住的一文一武两段青史,再到将脐橙的发展与黄龙镇的地名来历结合……此外,书中介绍了大量当地相关的诗文,诸如“风吹红叶胭脂色,雁叫空林橙柚香”等,这些诗句不仅让原本严肃的小说主题变得诗意化,也让读者深刻感受到袋子田独特的文化韵味与历史积淀。在技术运用方面,袋子田村一是借助“橙园丽日”的融媒体宣传渠道扩大知名度,二是建设了以航天科普体验馆为核心的知识基地,让全国的孩子来体验、学习航天知识,并进一步推动袋子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袋子田建设的“新矛盾”与“新路径”,构成了《驻村冻江源》的核心脉络,我们也能深刻体味到作者对于新时代农村建设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就湖南山区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扶贫点,了解到传统与发展的碰撞与矛盾,而作者又十分巧妙地化矛盾为方法,例如黄一先好神鬼,就成全他的半仙名;霍东明看重与黄小二的情谊,就顺水推舟促成黄小二的一桩“老牛吃了嫩草”的姻缘。作者用可爱的民风民俗化解了经济矛盾的叙事严肃,也告诉我们农村建设的必然之举:“见了袋子田村民的面要叫得出每个村民的名字,要让袋子田村民家的狗狗见了自己会像见了熟人一样会摇尾巴”,这种深入骨髓的了解,是解决群众矛盾、满足群众需求的前提。只有真正站在群众的角度,倾听他们的声音,才能找到破解农村发展难题的金钥匙。
二、“新乡土”建设中的“新农民”
“农民既是20世纪中国文学书写最庞大的形象群体,又是乡土中国现代转型、文化重建、百年中国农村建设运动的被启蒙改造主体与建设主力军”。对新时代农民形象的塑造,不仅与对乡村振兴的总体规划的理解相关,更与长期连贯的乡土文学的农民形象变迁一脉相承。传统乡土中书写的农民往往以“愚昧”“无知”“麻木”的形象示人,但新乡土文学所塑造的农民顺应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并不在思想水平、知识储备上落后于城市居民,相反的,新时代农民善用技术、积极向上、善良朴实。在新农民的形象搭建中,何石又在“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体”上完成了辩证统一。从集体层面来看,这种统一主要体现在南航驻村队伍与乡贤群体的紧密合作与互动上;在个体层面看,又表现为以“曹劲松”和“黄大牛”为核心的“平民英雄”形象塑造。
(一)新乡贤在乡村振兴舞台上的崛起
乡贤文化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明代汪循说:“古之生于斯之有功德于民者也, 是之谓乡贤”,传统意义上的乡贤是指乡村中德高望重的乡约、里正。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道德修养,是乡村知识分子的另一重身份。但在新时代,“乡贤”的身份认定逐渐平民化,我们不再强调乡贤的知识水平,而是关注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示范与领导作用,这在《驻村冻江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黄大牛、刘小五、黄小二等人都是没什么文化积累的“粗人”,甚至蒋光秀还是一个缺少本地属性的外乡人,但曹劲松并没有因此小瞧他们。相反,这些不被囊括在旧乡贤群体中的村民们都在袋子田建设中各显神通,成为了新时代新乡贤的代表。
《驻村冻江源》中的角色横跨了三辈,分别是以黄一先为典型的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的老一辈;以黄大牛为代表的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行动力的中坚力量;以及以黄小牛为主力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知识与创新的活力。黄大牛、黄小二、刘小五、王岐贵等人组成的乡贤群体,在袋子田的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复兴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塑造这些人物的过程中,作者避免了单一维度的美化或夸大,而是细腻地描绘了他们作为有血有肉、虽有瑕疵却满怀激情的“振兴先锋”。
最初,黄小二和刘小五都在黄大牛场部打下手,黄大牛虽然给了两兄弟足以饱腹的工作,却未充分察觉到两人在生活品质与职业发展等更深层次的渴望。刘小五,平日里以言语机巧著称,缺乏实干精神,行事既不主动亦少规划,在老婆负气出走之后,他一直走下坡路,直到被“扶志”,人就真正“挺直”了。然而,反观黄小二,他在广州为一水果摊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举动,显示了他并非无可救药之徒,实则亟需一个恰当的时机与一位引路人,来展现并实现自我价值。在解决了个人单身问题后,成功转型,成为“大塘脐橙加工与冷藏公司”的领航者,与刘小五并驾齐驱,一同在事业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一转变既得益于南航公司的机遇,也是乡村振兴大潮中的一份馈赠。证明了在面对家园建设的挑战时,每一个曾被轻视的“小人物”,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力量,为家乡撑起一片天空。
黄小牛是黄大牛的儿子,早年在长沙职场摸爬滚打,但没有显著的成就。当他回归故里,反而在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找到了归属感,例如黄小牛在修建鸭婆桥和校舍方面的努力、在“一桥两翼”“大桥经济”的发展提议中展现出的远见卓识等。与此同时,他的妻子蒋丽作为一名自媒体工作者,凭借自身的独特优势为袋子田的脐橙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宣传支持,推出了一系列短视频作品,使得他们的项目能够迅速扩大影响力。
“回归”是乡土文学永恒的主题,在越来越多青年人选择离开家乡奔赴城市的大背景下,黄小牛与蒋丽的“回归”显示出年轻人获取社会价值的另一种途径,他们既有城市打拼的经历,又有回归乡土的情怀。这就呼应了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乡村振兴一样需要年轻的血液,离开写字楼,年轻人一样能在广袤的山野中寻到心之所向。
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主动担当起振兴袋子田重任的黄大牛、黄小牛、蒋光秀等人,都是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先富者”。他们并不属于“脱贫”帮扶的对象,也没有急于逃离乡村的意愿。相反,他们在乡村深深扎根,对个人财产持淡泊态度,甘愿为了集体的福祉承担个人风险。比如,在与曹劲松讨论脐橙产业时,黄大牛毫不犹豫地缴纳了五万元的“诚意金”,并以坚定的语气签署了承包三千亩土地种植脐橙的承诺书,其魄力和大义令曹劲松“一双眼睛瞪得像两个桐子壳”。同样,拥有自己脐橙产业、还居住别墅的蒋光秀,在得知好友的召唤后,毅然前往袋子田,为当地的脐橙产业提供专业指导。这些无私大义的“乡贤”切身实际地践行着“先富带动后富”,不仅抛却了个体的利益,更用长远的格局谋一个集体的未来。
(二)乡村振兴的“关键行动者”
《驻村冻江源》虽然刻画的是为袋子田服务的集体群像,但其中也有特别突出的个体英雄,既体现出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又表现为“新时代公民个性张扬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英雄主义”。黄大牛和曹劲松就是这种“平民英雄”的两大代表,前者是乡村本土的能人乡贤,对家乡存有先天的热情和善意,后者是外来帮扶的资助力量,具有超越现有格局的意识和视野。黄大牛与曹劲松体现了在新时代背景下,个体价值与集体力量的和谐共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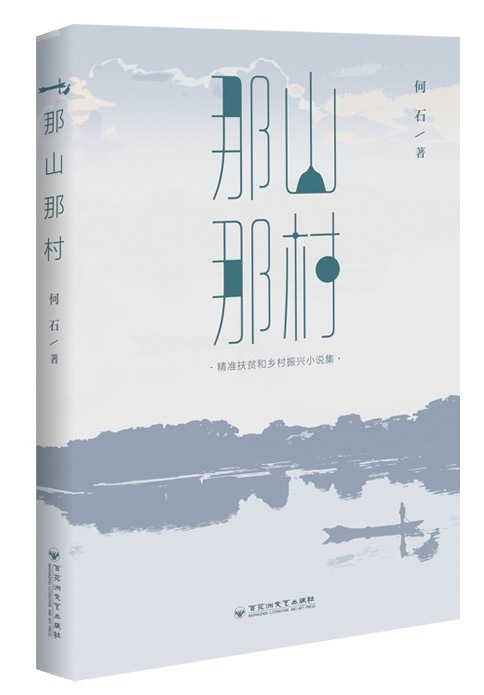
黄大牛与曹劲松在身份背景上有一个显著的共通之处——他们都是退转军人。事实上,在何石的作品中,退役军人形象屡见不鲜,如《那山那村》中的张清平、《浪里白刘》里的王德海等,甚至《驻村冻江源》里的刘小五、蒋光秀等人也是退伍军人,“退转军人”形象在何石的作品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这种对军人身份塑造的痴迷,很大程度上源于作者自身的军旅经历。何石本就是武警部队退伍的军人,因此他对军人性格与军营生活的体验更加深刻。在《驻村冻江源》中,我们也时常感受到军人朴实纯真的生活模式,比如黄大牛通过掰手腕来决定事情,这在非军人看来或许略显随意,比如他的妻子一开始就不能理解,但在两位退役军人的眼中,这却是一种既合理又可爱的“仪式”。或许掰手腕并非是决定选择的唯一条件,却是两个退转军人惺惺相惜的交往模式。
除此之外,黄大牛与曹劲松均展现出军人特有的果敢与勇气,他们敢于破局、敢于创新。这一点在他们共同推动脐橙产业发展的决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外界普遍持悲观态度,只要他们内心认定可行,便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在黄小牛提出“大桥经济”构想的会议上,众人对黄小牛的想法都表示是“异想天开”,唯有曹劲松迅速发现大桥经济的实践可能性,毅然决然地站在黄小牛一边,力排众议,最终为袋子田贸易城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大牛和曹劲松之所以是袋子田乡村振兴的“关键行动者”,不仅在于他们具有足够承担行动责任的能力和底气,更在于他们具有十里八乡的号召力。他们“为袋子田好”的正面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就是引路标,因此黄大牛率先对非法捕捞进行自查,而群众们也就纷纷效仿上交捕捞工具。
“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新史诗的农民形象,至今还没有实现其审美建构,正在等待着当代中国作家来书写、刻画下那新历史的一瞬,以此来‘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在“关键行动者”的指引下,袋子田的村民们拧成一股绳,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均展现出蓬勃向上的集体气质,这彰显了新时代乡村振兴所塑造的新农民风貌。正因这些“新农民”的不懈努力,袋子田得以从昔日的荒凉山村蜕变成为繁荣的贸易小城。
三、“新乡土”记录中的“新文学”
当乡土中国的格局发生改变,新的山乡巨变正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发生,如何“从历史的、审美的和人性的视角来看乡土文学在当下的书写呢?我们是否需要拟定一条新的主题路径和审美标准呢?” 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随着乡土矛盾的新转向及乡村面貌受现代化影响的深刻变迁,作家需调整创作视角,聚焦“新乡土”中异于传统乡土的情怀——那是一种不同于留恋、回归与感伤的新型乡土情感。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对语言表达形式和组织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呢?是否要在发展中的乡村土地里挖掘新的本土化的故事和细节?面对这些问题,《驻村冻江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与启示。
何石富有善用方言和俗语的文字表达能力,这在《驻村冻江源》中可见一斑。“大打村‘两委’一回扁担”“带了轮子”“牛懵子”“斗啵”“扳栗树门槛”等充满了民间风味的方言在小说中时常看见,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湖南地方色彩。这种方言的运用,基于袋子田村民或外向或内敛的性格展现为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小说赋予了独特的语言魅力,在读者接受的角度更加自然地融入了乡村生活的情境之中,流露出朴实真诚的乡土气质。
《驻村冻江源》中角色大多是袋子田村民,但也不乏外来支援的领导团队,何石在描写这些群体时,采用了“公文式”的语言,譬如书中时常以多个四字词语排比出现,“产业兴盛、文化绚烂、生态文明、组织有力的全面振兴和新质发展”等,这样的语言运用不仅使得阅读感受上更加有力、有节奏,更传达出说话人的坚定和信心。尽管这种风格可能会牺牲一部分文学的诗意,但它却与乡村振兴这一宏伟主题紧密相连,相得益彰。
再者,《驻村冻江源》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极具代表性,涵盖了“闯入者”——驻村书记、“守护者”——基层干部,以及“践行者”——贫困群众,这些角色共同贯穿了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同时也构筑了“新乡土”文学独特的审美框架。在这些人物身上,罕见有惊心动魄的恶行,他们更像是普通的乡村居民,带着各自的小瑕疵,却满怀脱贫致富的热情与决心。他们展现出的积极向上、鲜明的生活态度,无疑是《驻村冻江源》最为耀眼的精神亮点。譬如“闯入者”曹劲松,虽然偶会破戒和黄大牛小酌一杯,但在关键时刻他总能秉持公正无私的原则;“守护者”黄华平,面对黄小牛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虽会感到压力,甚至偶尔做出不利于对方的小动作,但他一生勤勉奉献于大塘村,且不惜努力为边贸城争取大订单以证明自己的价值;“践行者”黄小二等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了身份的转变,正是乡村振兴的浪潮激发了他们的潜能,使他们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个春天。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脱贫攻坚题材文艺作品所追求的审美理想与审美旨趣。
尽管《驻村冻江源》在形象塑造和叙事手法上独具匠心,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作品中部分情节和语言表达显得过于粗俗,比如黄大牛的脏话和一些对女性的调侃等,这些内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乡村生活的真实面貌,但也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其次,《驻村冻江源》对女性角色的描写还是较为片面和刻板,书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局限于传统角色,更多展现的是“贤内助”形象,缺乏独立性和深度。蒋丽作为自媒体工作者为乡村振兴做出了贡献,即使有“袋子田村K”的突破,但她仍然依附于丈夫黄小牛的事业支撑;欧倩虽然是村校校长,但她的工作是黄大牛帮忙打点的,书中也没有对村校教育的详细叙述,仅仅在村校成立后戛然而止。可见女性在乡村振兴中多元化的价值还未能充分展现。
一本书,讲得完的是袋子田振兴史,讲不完的是中国复兴路。《驻村冻江源》虽不是纪实文学,但却拥有纪实文学的细节和格局,他既有非虚构文学的厚重感,又有虚构文学的灵动自然。袋子田村不仅是黄大牛等人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一幅中国乡村的缩影。通过袋子田的振兴,何石展现了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困境与希望。像袋子田这样的亟待脱贫的村庄在中国还有许多个,我们需要更多的曹劲松、更多的黄大牛、更多的黄小牛,需要更多点燃乡村振兴的星星之火。《驻村冻江源》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对“乡村振兴”这一时代主题的回应。
结语
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语境里,《驻村冻江源》像一首抒情诗,叙说着作者对家乡的深切情怀;又像一首长篇史诗,描绘出袋子田从荒凉乡野到安居乐业的时代图景。正如作者在书中说的 “劳声互答,人影绰绰,鸡犬相闻”,袋子田已经成为了脱贫攻坚路上的一道风景线、一个世外桃源。《驻村冻江源》渗透出的作者对乡村生活的观察与感悟,走出了新时代的乡土文学发展的经典道路,他不仅在讲述每一位乡村奋斗者的“新乡土”英雄传奇,更在叙说着“新时代”“新农村”“新文学”的未来展望。
(作者聂茂系中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毛远影系中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责编:周洋
一审:郑丹枚
二审:曾佰龙
三审:邹丽娜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