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5-09-09 22:43:25

文丨蒋祖烜
直到离开它时,才真正注意它。它是一栋老楼,一位老友,我们的老家。
单位曾经在这栋老楼第三层办公,许多年在这里流逝、许多人在这里往来、许多事在这里定格。我有缘在老楼度过十几年光阴。第一次走进大楼时,不到而立之年;分别时,已接近知天命的门槛了。
起初对老楼的印象,一是气度不凡,沉稳庄重,透出无声的威严;二是环境幽雅,环抱在绿森林之中,周围几乎看不到别的建筑。直接感受到老楼恩惠的是,楼内因空阔造成的小气候,冬暖夏凉。从炎热的外部世界回来,跨进一楼大堂,顿觉凉风扑面。其实,当时楼里的冷气未开,只是最热的几天,从防空洞输送来了天然冷气而已。
也曾经为它的陈旧失修而苦恼过,有一年大雨倾盆,雨水从天花板飞流直下,淋湿了我的书桌和资料,此后类似的节目经常重演,直到维修队来了一次彻底的检修。走廊里的灯泡瓦数较低,照明度不够,朦朦胧胧的,让人感到些深邃和神秘。我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我的奋斗、苦乐、进退、荣辱,生命中的一万多个日子,有将近一半浓缩在这栋体量巨大的建筑里了。
从没有用心多看过它几眼。最初的陌生感消退之后,渐渐被一种漫不经心的麻木所取代。上楼、下楼、进楼、出楼,脚不点地,顺理成章。直到那一天,突然得到要暂时离开它的消息,陡然生发对这栋朝夕相处的老楼的情感。停下匆忙的脚步,环顾相伴多年的老友,才发现它不同凡俗的美。
这是一栋砖混结构的建筑,尽管只有四层高,但它的造型不是那些大同小异的“方盒子”可以比拟的。主体建筑一字展开,中央部分以方形攒尖屋顶突出,给沉稳平实的主体造成向上和提升的感觉。 建筑立面干净利落,窗户之间的灰色面板凹凸错杂地安排着,造成特殊的韵律节奏。空间尺度宜人,宽大的窗户、宽阔的走廊、超拔的层高,采光、通风良好。使用功能齐全,六个会议室、四个进出通道, 满足办公的需求,方便人员的组织和流通。建筑材料受到时代的局限,并没有使用如今流行的高档大理石、大块面镜面砖、珠光宝气的玻璃幕墙、闪闪发光的金属配件。水磨石的淡彩地面,勾画着湖湘气韵的装饰图案;纯铜的饰物拉手,磨洗出岁月的光亮;清水红砖砌体正直平稳、严丝合缝。精工细作竟营造出沉着与大气之美,简洁而绝不烦琐,质朴而绝不奢华,从容而绝不漂浮。在香樟林起伏的绿浪中,老楼像岛一样坚定、沉稳,大方中透出精致,朴素中闪耀着华彩。一定出自一位高手,我想请教单位的老同志,听到老楼的一些掌故。最光荣的,是当年毛泽东主席从附近的宾馆散步到大楼的前坪,与普通机关干部打招呼,合影留念。最传奇的,是泥水工刘师傅,反手砌砖,又好又快。最搞笑的,是当时含有的水磨石地面和暖气系统,被外人越传越神:地上打滚不沾灰,烧火取暖不见火。但对建筑师的说法各不相同,有的说是苏联专家,有的说是日本友人。于是,越发想问个究竟。

在长沙市近现代保护建筑的名单中,我发现了短短的一行文字: “湖南省委一号办公楼,建成年代,1952年。”查阅《中国现代建筑史》,发现了老楼的名字,还找到了建筑师的名字——吴景祥。张傅先生的《我的建筑创作之路》一书给我指引了新的线索:“上海陈垣、吴景祥一行来京,商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上海!于是集中查阅上海方面的资料,终于,在同济大学的一本论文集中,我找到了建筑师供职的单位——同济大学建筑系。
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向大师靠拢。我要设法拜访大师,请教悬在心中的许多疑问。我想象着我们见面的情景,他一定会关心我的楼,当然首先是他的楼。我准备了照片,我还预备了接受感激的心情,那毕竟是一次跨越半个世纪的回访呀!
追寻一路顺当,甚至奢望有机会当面请教。这时,杨永生先生赠送我他的新著《建筑百家书信》,其序言中写道:“去年,给上海同济大学吴景祥教授去信索取1958年上海六教授关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设计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久久未复。又托同济大学沙永杰同志去吴先生家里面谈此事。未料,他欲前往的前一天,吴先生竟病逝。那封非常重要的信件,至今未能收集到。”杨先生深深遗憾,这又何尝不是我的遗憾。
《建筑师》杂志终于给出了一个简要而完整的设计师简介:吴景祥,广东省中山县人。1905年生,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1933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建筑专门学院。1933—1949年,任中国海关总署总建筑师。1952年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主要作品在北京、上海、湖南。1952年担任湖南省委大院的总建筑师,设计建造了湖南省委一号办公大楼、俱乐部(省委礼堂)、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干部住宅。同期杂志还刊发了老楼的老照片、整个建筑群的风貌。显然那是刚刚竣工时的情景,大院的树木还没有生长起来,地面也显得粗糙不平。那是新生的省级人民政权为数不多的新办公建筑。
今年六月,我出差路过上海,在好友同济大学吴国欣教授的陪同下,访问了吴景祥先生20世纪50年代为自己单位设计的教学北楼和南楼,两座楼至今仍是同济大学的主要教学楼,从那同样记录着岁月沧桑的大楼上,隐约可以发现与一号办公楼一脉相承的风格,可以体味建筑巨匠留下的嘱托。也许冥冥中有缘,在建筑与设计系的大楼面前,我同吴景祥先生的继任、现任建筑系主任莫天伟教授不期而遇,他听说吴景祥先生在湖南的作品而感到意外和欣喜,询问了一些情况,还热情赠送了许多介绍建筑系历史与学生成绩的资料。在先生的同事和学生的回忆中,吴先生的形象和个性更加完善起来。
吴景祥先生学识渊博而又平易近人,治学严谨而眼界开阔。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预见了我国高层建筑的发展趋势,确立了相关的课题和课程,并开始招收研究生,为中国高楼大厦的潮流提前做了理论和人才的准备。值得记述的是,他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营造了两幢一模一样的小楼,他一直住在自己设计建造的小楼里,这种荣誉和地位在当代中国建筑师中几乎是一个特例。
经历了多少岁月的风雨雷电,目睹了多少人间的阴晴冷暖。该过去的都过去了,甚至就像不曾发生过一样。老楼依然屹立,沉稳得像一座青山。五十年不落后,六十年不过时。岂能用“过时”“落后”来贬损老楼的价值?应该用“新潮”“经典”来赞誉这栋历久而弥新的老楼!许多二十年甚至刚刚十年楼龄的新楼,因为设计的抄袭与营造的粗糙,已经明显落伍了,老楼却以毫不张扬的姿态显示着越是经久、越是高贵的气质与华彩。
老楼四层塔楼上有个不小的空间,那是部里的图书室、阅览室兼资料室,书报刊藏量不亚于一座市级图书馆,那曾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安静、亮堂的氛围,特别是难得一见的老书、旧刊,让我乐而忘返。后来单位搬家,全部家书转赠给了另一座图书馆。我手上还有一本没有及时归还的《世界史》,泛黄的封面和书页、淡蓝色的藏书印章、书脊上手工的分类编码标签,成为老家和家书永久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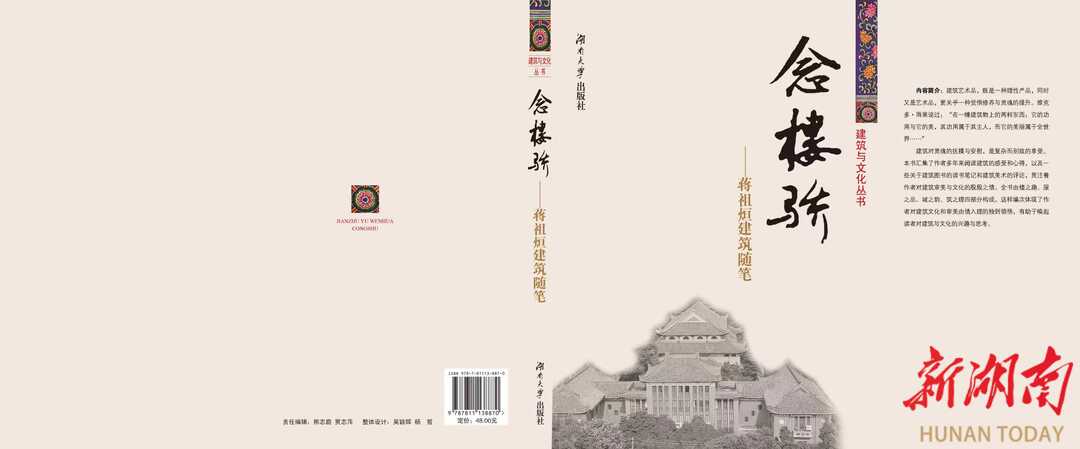 《念楼骄》书封
《念楼骄》书封
写作此文的时候,我从我的江南转场到遥远的北国,客居京城的日子,陡然有了写《念楼骄》的情绪和文字。题目是我从词牌名“念奴娇”那里转借而来的,但感受却是真实深切的。在大师构造的空间里度过十余载寒暑,那是我一生的骄傲。当然,我也为寻找大师和理解大师而骄傲。
(2003年10月)
责编:刘瀚潞
一审:刘瀚潞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