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国剑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5-09-05 08:5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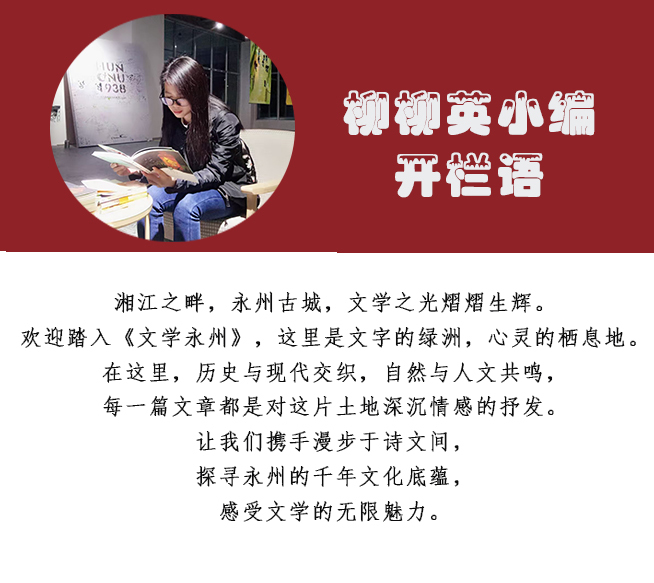
作家龚盛辉印象记
■熊国剑
欣闻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龚盛辉的长篇小说新作《六月花》顺利完稿,并进入出版流程,估计明年即可出书上市与读者见面。这将是龚盛辉首部取材于江永家乡的文学大作。
非常佩服龚盛辉超高的创作效率。前年深秋,我们家乡的几位文友跟他座谈交流,才听他亲口提起要专门创作一部江永题材的长篇小说,书名就叫《六月花》。去年十一月中旬,他专程回到江永,为即将投入创作的《六月花》搜集素材以及实地采风。至今年清明节期间他再回江永,说《六月花》经写出六万多字,计划六月底完稿。
结果与既定的写作计划一天不差,《六月花》恰好在六月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不愧是大作家,可以如此轻车熟路地“玩转”一部长篇小说,丝毫无碍于自己将近67岁的年纪。很荣幸亲眼见证一位家乡作家的重要新著酝酿创作的全过程。
虽然认识龚盛辉先生还不到两年时间,见到他也不过三次而,但他纯朴的性格,他的师长风度,他的军人气质,他浓厚的乡土情怀,他对文学的执念与追求,无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与龚盛辉相识的过程,说起来非常有趣。
第一次听说龚盛辉是名字,大约是2017年,不记得具体的时间,甚至不记得在什么场合,是谁不经意中问我:“下甘棠村出去的有个龚盛辉,国防科大的教授,是一位作家,出了很多书,你知道吗?”“没听说,不知道,不认识。”我也是不经意地答道。
事实上我也真没听说过其人其事,所以并未在意,也未放在心上。
过了两年,2019年10月的某一天,县里一位老文友特意打电话问我认不认识龚盛辉?我仍然如实回答说不认识。
老文友直呼怪哉!他说他经在熟人圈里先问了一遍,都说不知道、不认识,然后才来问我。他不相信竟然连我也不知道。
不说老友不相信,我自己也不相信。江永人干文学创作这一行的,县内县外的,怎么会有我不知道的人?
这次我丝毫不敢怠慢,立马上网搜索,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这个“神秘”的龚盛辉到底何许人也。
 龚盛辉。图片转自网络
龚盛辉。图片转自网络
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网上搜索到的信息显示:龚盛辉,著名军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防科技大学教授,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国防之光》《铸剑》《向着中国梦强军梦前行》《决战崛起》《中国超算》等,著有长篇小说《绝境无泪》,中篇小说《导师》《章鱼》《通天桥》《老大》《与你同行》等。曾先后荣获昆仑文学奖(两次)、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
千真万确!龚盛辉是位作家,是江永走出去的一位大作家,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知名作家,在自己的家乡竟然鲜为人知。
何以如此?我继续追根究底,然后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情况”。
龚盛辉于1978年参军入伍,服役于野战部队,1989年调入国防科大,工作长达30年直至退休。自始至终,龚盛辉与江永家乡的官方素无交往,与家乡的文学界人士素无交往,他也没有写过家乡题材的文学作品。龚盛辉每次回家乡看望母亲及家人的时候,除了相约那三五位与自己深交的老战友见上一面,再不惊扰任何别人。并且龚盛辉每次回家探亲,都是只身一人悄然来去,非常低调。
龚盛辉在家乡的行止低调至此,难怪大家对他鲜有所知。
也许有人会疑惑,龚盛辉作为一位成果卓著的知名作家,单是凭借他的作品,就会赢得大批读者,更遑论家乡的读者,无论如何在自己的家乡的名气都不该如此之低。
显然,这与龚盛辉创作“门类”的“偏高偏冷”密切相关。龚盛辉的创作以报告文学为主,写的是军事领域的题材以及高尖端的军事科技题材,而非大众题材,读者面自然而然受到较大的局限,“曲高和寡”是也。
我也曾在自己的文朋书友圈中挨个问了一遍,“读过龚盛辉的书吗?”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
惭愧的是,我也没读过。
我特意去过几次县新华书店,都没见着有龚盛辉的书,连荣获鲁迅文学奖的《中国北斗》也没有。于是问店员们书店进过龚盛辉的书没有,她们说“从来没有。”她们也表示不知道江永出了这样一位大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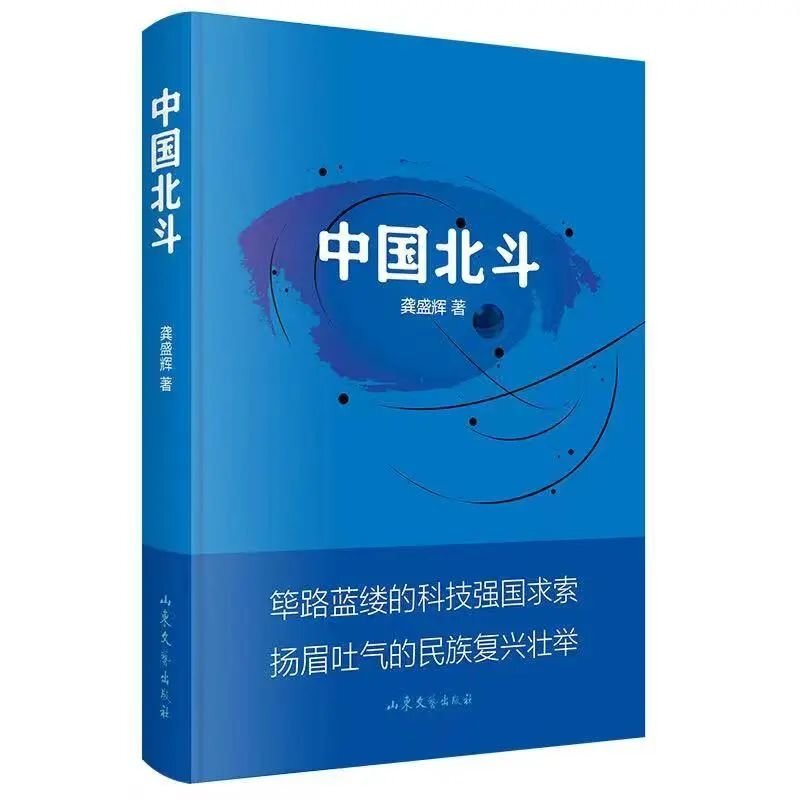
龚盛辉在自己的家乡的知名度,与他在文坛的地位及其成就,太不匹配。
之所以这样,除了上述种种因素,根本还因为龚盛辉太过低调。
如果龚盛辉想在家乡搏一点名声,实在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无论他是以作家的身份,还是以国防科大教授的身份,直接出面还是间接出面,只须与家乡有关方面沟通一下,张罗一次诸如作品研讨会或者新书签售会之类的活动,小县城也就人尽皆知了。
但龚盛辉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不说在山区小县城的家乡,就是在别的任何层级,我也从未见过有关龚盛辉作品研讨会,或者新书发布会、宣传推在广会之类的任何信息。网络媒体上龚盛辉的介绍尤其扼要,只显示他国防科大教授、作家的身份及主要代表作,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甚至都没显示他的江永籍贯,也没有他的个人照片。
我不禁冒昧揣测:龚盛辉这般低调,是顺其自然的,还是刻意保持的?或者是职业上“保密”的需要,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龚盛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会不会因为离开家乡久了,对家乡的感情薄了、淡了?
一番追寻下来,我对龚盛辉这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大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好奇。
那个时候龚盛辉刚刚退休。
我曾经闪过这样的念头,就是想自己有无必要以县作协主席的名义去省城拜访一次,或者直接邀请他回江永与家乡作者来一次交流互动。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一念头,觉得这样做未免一厢情愿,不如一切随缘,等有缘相见的时候自会相见。
时间来到2022年8月25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龚盛辉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获奖榜单中,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北斗》荣获报告文学奖。
龚盛辉所在的省、市、县官方媒体相继发布了这一重大喜讯。
随后,各级报刊以及网络媒体对龚盛辉的各种报道、专访陆续登场,全方位地展现他的方方面面,包括他的家庭背景、少年经历、军旅生涯、文学追求以及创作历程等等,几乎无一遗漏。
有个很有趣的细节,就是我发现每一篇报道或专访中,几乎都着重写到龚盛辉的“江永籍”身份,且他早年的山村生活经历、家世背景,毫无例外都有大篇幅的体现,这与早前个人介绍中的“极简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一时间,网络上有关龚盛辉的文字信息及图片影像可谓“铺天盖地”。透过媒体的密集传播,一个实实在在的龚盛辉完整地呈现在广大公众面前。
龚盛辉想低调都难了。现在,江永的父老乡亲再也不会有人不知道他的大名。
原本期待着有什么机会走近并了解这位“从家乡走出去的作家”,没想到机会说来就来,一切都自然而然。
之后不久,我与龚盛辉在江永,接连有了三次愉快的见面。
2023年10月22日上午,以江永著名瑶寨勾蓝瑶命名的中篇小说集《蓝蓝的勾蓝》作品研讨会在勾蓝瑶民俗表演厅隆重举行。省、市20多位作家、教授、主编应邀参加,龚盛辉就在邀请嘉宾当中。这是龚盛辉首次以作家的身份,回家乡参加的一次公务活动。
此次研讨会由湖南省作家协会及永州市文联、永州市作协与江永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
作为县作协主席,我对应参与了本次研讨会的对接、联络工作。
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到了慕名久的作家龚盛辉。
打眼相见,跟网络上看到的他高度一致。龚盛辉身高170余厘米,剃光头,四方大脸,说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初看他的言谈举止自在随和,细看就会发现他无论站着坐着,腰杆总是挺拔,不愧是个军人。大家一定见过他那张在网上被反复引用的身着少将军服的戎装照,其霸气侧漏的将军风度一览无遗。
龚盛辉朴实沉稳,没有一点将军的架子,也没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仿佛一位邻家大哥。他跟谁说话都是客客气气、笑容满面,一点也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尤其他那一口纯正的江永乡音,让我惊讶于他的乡土烙印之深。
大概因为在同一个地方成长,共同沐浴一个地方的阳光雨露,所以我们虽是初见,彼此间却跟老熟人似的,一点也不生分。龚盛辉大我几岁,自当尊其为兄长。我们之间完全没有代沟,大家一起吃饭喝酒、说话交流,都是其乐融融。就是在这头一次的相见相谈中,我们家乡的几位作者听他亲口说起自己正准备写一部家乡题材的长篇小说《六月花》。
这次回家乡参加研讨会之外,龚盛辉还应县委宣传部之邀,走进江永一中校园,作了一场主题为“热爱与奋斗”的精彩演讲,向300多名县内文学爱好者、学生分享他独特的人生故事和文学创作经验,受到学生们热烈的欢迎和追捧。
因为文学,我和龚盛辉就这样不期而遇,彼此相识了。
第二次与龚盛辉相见,是在一年之后,也是没有事前预约。
那是2024年11月11日,县文联打电话告诉我,“龚教授回江永了。”
龚盛辉此次回江永,一是为他即将创作的长篇小说《六月花》搜集素材及实地采风,二是应邀参加他们村里举办的首届丰收节。此外,他很爽快地同意与家乡作者举行一个座谈会。文联希望我出面安排陪同一下。
于是,我和县文联主席安欣等人陪同龚盛辉一起去了上江圩蒲尾村参观了女书博物馆,一起去采访了源口水库以及沿岸村庄,一起去下甘棠村参加了热闹非凡、别开生面的首届丰收节。另外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文学座谈会,由龚教授现身说法向本土作家们分享自己宝贵的创作经验,并给大家提了一些很好的创作建议。
龚盛辉这次在家乡驻留超过一周,我全程陪同了三天,诸多当面讨教,受益匪浅。
聊到他即将投入创作的《六月花》,我冒昧地给他提议,是不是可以考虑里面的地点都采用实名,他说他也正是此意。
我为我们彼此的不谋而合感到高兴。
龚盛辉说他这次返回长沙就要动笔了,计划2025年6月底写完。
转眼到了今年清明节,龚盛辉回家乡扫墓祭祖期间,我第三次见到他时,知道他的《六月花》经写了数万字。
又三个月后,我听到的消息是《六月花》经完稿并交给了出版社。
不妨跟读者诸君先“剧透”一下,《六月花》写的就是龚盛辉所在的下甘棠村的村史、家族史,写的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非常值得期待。
龚盛辉反复说到他三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写作难度最大、投入精力最多、耗费时间最长(五年)的作品,当属《中国北斗》。相比之下,看他创作《六月花》,似乎显得“格外轻松”。想必是因为该作品的故事在他的心里孕育久,早生根发芽,到如今便自然而然地瓜熟蒂落了。
在相见的日子里,我从龚盛辉的言行举止中,从他创作《六月花》的过程中,都能深深感受到他对于自己家乡那种浓浓的情意。
有两个特让我“服气”的例子:
其一是,前年下甘棠村举行“丰收节”那天,我沾龚盛辉的光也应邀参加。当天的活动可谓盛况空前,上下邻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如潮涌来。一整天里,我看到龚盛辉不断地跟本村的、上下邻村的老乡亲们大大方方、亲亲热热地打着招呼,而且讲的全是当地土话。看他的姿态之“低”,丁点都没有一位大将军、大作家的影子,也不像一位村里请回来的嘉宾,而活脱脱是村民中的一分子。我很惊讶他离开家乡40多年,怎么还认得那么多乡里乡亲,怎么还讲得来那么一口地地道道的土话。这不就是《父老乡亲》里的那句歌词,“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么。
其二,我见到龚盛辉的这三次,除了有集体活动需要住在县城,别的时间他一概住回村里。这点上,绝大多数外出工作的人很难做到,包括常常以“老土”自居的我也做不到。我至少有二十年没在乡下老家住宿过了,老家离县城近不是理由,不习惯才是真的。
龚盛辉不挑剔住的,吃的也从不挑剔,我们招待他,问他有什么讲究,他说“没有讲究,吃饱就好。”听凭我们随便找一个地方,点几个农家菜,上一壶三五块钱一斤的米烧酒,就对付了。
这样接地气的一位大作家,谁会不爱?谁会不服?
龚盛辉以自己切实的行为证明:他依然是他,他依然是那个不忘初心、不改本色的江永农家子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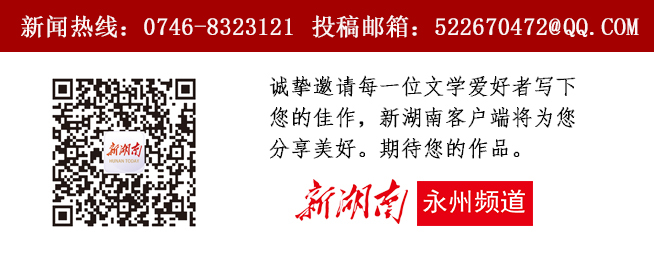
责编:黄柳英
一审:黄柳英
二审:严万达
三审:李寒露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