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钊 周君成 2025-08-26 10:44: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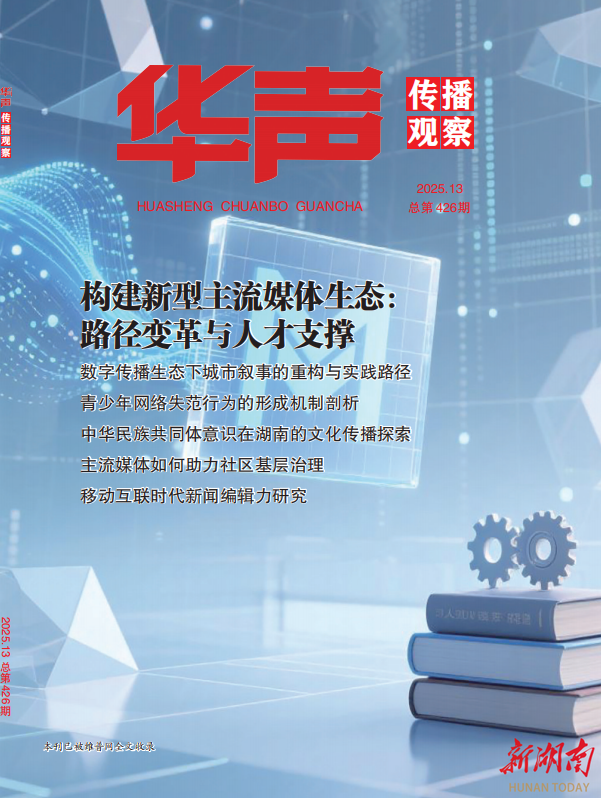
文/吴钊 周君成
系统性变革是党中央对我国主流媒体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是主流媒体重新塑造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牢牢把握思想舆论文化阵地主导权的必然要求,因而成为整个媒体行业必须予以重视的新课题。目前,我国数字出版已形成以互联网广告为龙头,以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音乐为核心,以移动出版、网络动漫、互联网期刊为补充的“一点突破、多点开花”的“增长型”产业格局,但是在面对媒介技术迭代、内容生态重构、消费升级扩容,以及数智融合、数实融合等社会新趋势时,数字出版企业常常出现应对吃力、效率低下、茫然无措的问题。可见,推进我国数字出版系统性变革的任务已十分紧迫。
一、推进我国数字出版系统性变革的依据
(一)顶层设计:十五年有序推进
回望我国数字出版发展历程,自上而下、有序推进的政策是发展之先决条件。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2010年8月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彼时,我国出版业正处于数字化转型起步期,主管部门确立了“加快推动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鼓励自主创新发展新兴出版”的目标和任务,也明确了出版转型的核心环节——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传播渠道网络化。经过三年探索和积累,我国出版业逐渐具备实现整体转型升级的思想、技术、组织和工作基础。2014年4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整体转型升级阶段的四大任务——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标准化工作、提升数字化转型升级技术装备水平、加强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新模式。两份文件对我国数字出版领域的部署都充分体现了系统性原则。
中央在媒体融合领域的战略布局同样深刻影响了我国出版业转型的进程。2014年8月中央出台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后文简称《意见》)确立“融合”为我国媒体发展的方向。次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作回应,确立了我国出版融合发展的方向和任务——创新内容生产和服务、加强重点平台建设、扩展内容传播渠道、拓展新技术新业态、完善经营管理机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2022年4月,中宣部发布《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出版业积极探索数字化、智能化的融合发展路径。2025年4月,面对技术冲击,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十部委联合制定《网络出版科技创新引领计划》,围绕“政策环境、技术平台、融资渠道、人才支撑”四大问题提出了系统推进我国网络出版科技创新的着力方向。在中央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引领下,我国出版业改革有序推进,逐步实现从数字化改造到整体转型升级、从融合发展到深度融合的各个阶段目标。
(二)理论依据:来自系统学和生态学的启示
党中央将“系统性”确立为主流媒体变革的目标和方向,亦有其深刻的理论来源。系统学大家钱学森认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依赖于两个部分的知识,一个是科学知识,一个是经验知识。科学知识是指成系统的、有结构的、组织起来互相关联的、互相汇通的学问,而经验知识则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初步规律总结,只有通过进一步提炼、组织、升华,才能真正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中,因此也被称为“前科学”。以《意见》为起点,我国媒体融合已走过十年,但实际上媒体融合的探索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报业集团化的出现。1994年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问题的通知》,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作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获批创办,开启了我国报业集团化发展的步伐。由此推算,我国媒体融合至少经过了三十年的探索和积累。现阶段党中央提出“系统性变革”,既是对过去三十年媒体融合经验的历史性总结,也蕴含着对我国媒体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期待。
系统性变革要求我们关注主体内部各个要素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性、有序性、持续性和完整性,这是典型的生态学思维。100多年前人们就开始从自然生态的角度解释人类社会系统,我国学者邵培仁则将媒介学与生态学结合发展出新的研究范式——媒介生态学。他指出,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统一却又不断变化着的生命系统,因此在媒介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媒介、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互动、共生共进。现阶段,媒介生态系统呈现出社会媒介化和媒介社会化两大表征。一方面,媒介渗透至社会系统,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社会事务均越来越按照大卫·阿什德口中的“媒介逻辑”来运行。另一方面,媒介也在“朝着更加符合人类需求或是前技术时代传播模式的方向继续发展”,譬如对多元生产主体的接纳、对生产工具的智能化改造、对用户视觉化感知偏向的体认。作为社会媒介系统的中坚力量,数字出版企业和集团应当积极响应党中央媒体发展战略,推进自身从“合而不融、融而不深”的混合型组织向“有机融合、自为一体”的生态型组织方向变革。
二、生态型组织:我国数字出版系统性变革的目标
日常表达时,人们常用“生态”来定义美好的事物,凡是健康的、美好的、和谐的事物均可冠以“生态”之名。理论研究中,生态则是指特定功能单位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通过彼此间不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及信息传递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方式。“系统性”与“生态”在内涵和意义上的共通性,启示我们锚定数字出版系统性变革的目标——建立生态型组织。何为生态型组织?本文认为,媒体领域的生态型组织应当具备坚实可延伸的技术支撑体系、超级用户基础、竞争力强的核心业务模块以及突出的团队协作造血能力。据此,提出建设生态型数字出版组织的四点建议:
(一)夯实技术底座,加强核心技术攻关
出版数字化转型已是业界共识并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技术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市场机制决定旧技术会被新技术取代。在此情形下,出版企业对技术的应用要从“作为工具的使用”转变为“作为逻辑的嵌入”。当前,云计算、大数据、数字权益管理、VR/AR、数据库、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发展并朝着更精准满足人类需求的方向迈进。出版集团应从积极“尝新”,推动技术逻辑的实际嵌入。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特别强调新技术的“早期采用者”角色,认为它在扩散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是技术“起飞期”到来的前提基础。而通过自主研发与创新,一方面可以提升出版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具有产业关联性的众多企业形成集群,推动出版集团纵深发展。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所言,“创新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上,恰恰相反,它们趋于群集而扎堆地发生。”企业在成功创新之后,会有一大批企业“步入后尘”,尤其是那些相关、相近部门的企业。
(二)基于新型用户关系建构逻辑加速平台化建设
平台优势在于超级用户基础,俗称“流量”。过去,大多数人对流量一词嗤之以鼻,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消费文化、兴趣经济以及短视频、网络直播平台席卷之下,“趋流”彻底成为网络用户生存的基本方式。“学习《决定》每日问答”中明确提出了“用流量和效果说话”的要求,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重新审视“流量至上”“流量为王”的价值逻辑。回望过去,在媒体融合总战略驱动之下,许多具有专业内容优势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融合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平台化的传播能力和竞争优势。对于出版集团而言,下一阶段的重要目标应当设定为打造“既拥有专业出版机构的内容权威性,又拥有面向用户平台所特有的开放性的数字内容实体”。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用户红利逐渐消失,平台流量增长逻辑正从“算法霸权”向“新型用户关系建构”转变。如我们所见,在自媒体平台和网络趣缘社群,用户可能会因为算法推荐技术和猎奇心理而短暂“驻足”,但是长时间“驻扎”还要依赖心动、信任和共情而建立的情感关系,这种关系会某个时刻物化为用户的情感劳动(传播活动)和情感消费(购买活动)。
(三)优化产业结构,开拓“长尾”市场
产业结构是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集中体现。产业结构失衡会引发明显的结构性问题,比如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这对企业发展来说非常不利。作为数字出版企业,首先要明确自身优势和短板,避免盲目追求“大而全”的行业布局。当前,垂类化已是内容行业公认的趋势,聚焦特定市场需求、全面转向“专精深”方能提升企业自身市场竞争力和用户价值。由此,数字出版企业可进一步思考开拓长尾市场。帕累托的“二八法则”让绝大部分数字出版企业都只关注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音乐这些“主要”的、风险低的业务和产品,但是实际上克里斯·安德森的长尾理论告诉我们,只要“长尾”足够长,每一个部分创造的微薄收益积少成多,也能够形成巨大的整体收益,比如数字藏品出版。数字藏品是近年来兴起的小众出版领域,深受年轻人喜欢,特别是“敦煌飞天”“九色鹿”等非遗类作品引起了市场的极大反响。我国古今载籍浩如烟海、文学艺术异彩纷呈,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和文艺作品中的经典IP,铸造为绚丽多彩的数字藏品,将助推我国数字出版迈向更广阔的市场消费空间。
(四)“微粒化”运营,释放人力动能
澎湃新闻在年初改革方案中大刀阔斧地提出“将13个涉及内容采编的中心缩减调整至6个采编中心,一次性关停新闻客户端20个栏目和15个社交媒体平台账号”,引发社会关于媒体裁员、媒体失业潮的猜想和热议。毫无疑问,采编中心缩减和客户端、平台账号关停会造成人力资源的重大调整,其中可能就包括裁员或调岗。然而,更为深刻地说,这次调整其实暴露了当前内容行业的一个通病——多平台粗放建设下的产能过剩。平台建设导向下,集体通过自主搭建平台或入驻其他平台的方式开设账号、投入资源,但这种“跑马圈地”式的粗放建设不仅难以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还使资源有限、实力不济的中小型企业“雪上加霜”。为了解决这个现象,澎湃新闻一面缩减采编中心、关停数十个客户端和平台账号,一面又重新组建了24个新的垂直IP工作室,以“微粒化”运营的方式充分调动人力资源、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适应不同用户对于信息的个性化需求。澎湃新闻的做法对数字出版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和借鉴。“微粒化”让每一个人都有施展的空间,也让数字出版企业内容和服务拥有更多的延伸空间。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双效’统一背景下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绩效评价体系建构与应用研究”(19YBQ102)】
(作者吴钊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周君成系该院学生)
摘自《华声·传播观察》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范彬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录华声在线官网www.voc.com.cn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