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恪 2025-08-19 17:40:18

文/刘恪
(一)
最有湖湘之气的是码头:从东南青草湖面传来的是恶臭的鱼腥味,太阳直射湖滩后,漂浮物里夹着潮湿的热气,还有码头上扛粗重货物的工人,头上正冒着灰白的热气,赤裸着背脊,把头夹在货物中,在阳光下像蚂蚁般地爬动……十年过去了,丘脊梁笔下的意象我还没忘记。那时,他拿来一堆稿子,说要我帮他判断他适合写小说还是散文。那时候他已经发表了上百篇的小小说了。我在那个热得心里发慌的天气下读完了他十几万字的稿子,无论他的小说还是散文都让我觉出一份生活的沉重,他的表达非常有生活的内涵,且有充沛的情绪与力量,这倒让我颇感意外。我说的是:“你主攻一种文类,另一种写法也不要放弃。”我曾读过他的《疲软的安全》,作品表现都市生活的一隅,但这一隅是心灵角落的某一湾,而这一湾正好对应了家庭生活中的某种隐秘。社会和家庭生活是安全的吗?每个人都会有些隐隐的担心,尤其到了今天都市状态下的社会生活,从家庭到公共领域,从社会环境到自然环境,无论哪一点都会有潜在的危险。这是今天社会生活的本质,“危机”一词有了特别的含义。今天,城市里的人首先考虑的一定是健康与安全感,这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点一滴了。从夫妻生活到机关的贪官污吏,从媒体红人到码头工人,均是人人自危的状态,都在寻找没有灵魂意义的安全感。今天看丘脊梁的作品仍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早年,他爱写机关、报社、饭店、书店、洗浴店,都市生活的漂荡,这大概与他在各行业打过工有关,三教九流,很具有社会生活的广度,表达的是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那么如何理解这些机关文员的本质呢?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提升级别到领导岗位,进入官僚阶层;另一条便是熬一辈子直到退休。《笔杆子》中的老梁是一个秘书,好笔杆子,按机关熬年头,他是可以正常地做一个小官的,但事与愿违,由于材料写得好,无论岗位怎么变动,他还是要写材料,提了副主任还是没用。他受给领导开车的好司机启发:好司机领导喜欢,而坏司机往往被领导调离还给安排好工作。因而,老梁如法炮制,故意把材料写得不好,哪知道一下被机关改革给精减了。老梁由最好的笔杆子变成了疯子。这个故事极具内在的讽喻力量。

(二)
近几年,丘脊梁的写作发生了变化,他把笔墨转向了自身,转向了他的故乡、他的家族。他有一个极富象征性的标题——“沿着一条河流回家”。这很重要,表明他以前的社会写作是关心他者,关心社会生活里的芸芸众生,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他者写作。现在他关注的是自我,是一种反思性写作。自我是什么?家族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根脉?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根脉及自身,通过反思我们才知道如何更好地生活。《满眼是根》中的王宗保从挖根到栽树,栽上树根脉才能得以延续,这是他至死的梦想。他死亡之前有一段想象的文字:“梦是绿的——千万条树根,在厚实的泥土里疯狂地生长,长出一根根的枝条……”根是一种写实,在今天的社会里又是一种想象,人们在无可奈何的失落中更充满对它的思念。《最后的种子》中的奶奶本人就是一个家族的根脉,她依恋茴,最后这种依恋变成了生命的形式,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嘴里还含着半截烧烤的茴。每一个人都会怀念自己的根脉,这不仅是出于“原型”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遗传学笃信无疑。我们个人一定是“直接而具体地来源于民族志和历史进步论的综合(威廉·亚当斯语)”。每个人都是“生物进化的继续”。那么,我们肯定有一个自己的源头,这观念是深入每个人的无意识状态里了。按理说,我们只要找到家族和个人的根脉就可以了,就能认识到自己就是其中一个。但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人类学的认识与研究是一种他者的研究,道理很简单,你不是你自己,居于氏族之中,你是一个家族的后代,你看不到你的家族,你只能证实你的家族。你只有通过他者的材料,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观察,既作为自我也作为他者。作为集体的人类社会就是依据这样一个心理学的基本假设:个体所见的自身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见的,但反之亦然。可见,一个人是不能单独认识自我的。要通过他者和社会进行反思。所以,丘脊梁的这一家族系列小说也有非常浓厚的社会性。他最近发表的《地盘》,受到了《小说选刊》的重视,这便是例证。表面上说的是作为治安联防队长的父亲与黑帮头目肖拐子之间的斗争。但里面包含另一个复杂视角:我观察父亲的态度,英雄还是狗熊。出人意料的是父亲的示弱反而激发出人性的光辉,从另一个角度获得了人性的尊严,三千元失而复得。我们仔细分析后可知这是两个群体的斗争,一方是执法者代表的正义,另一方是犯法者及一个区域(暗示地盘意识)。我和父亲显然具有家族的传承含义,敌手既有害怕又有复仇在里面,黑帮的力量更强,也很有整体性。我们也有害怕和不害怕的东西在内,这种抗衡对立,已超出个人的含义,所以小说一开始就具有群体较量的含义,这极大地拓宽了小说的社会性,这种对抗从表面看很罪恶,但仅是一个形式,如跳刀、摩托车灯,排开示威的阵势,实际都没有构成作恶犯罪的性质,仅仅是张扬,父亲和我也应用了许多张扬的策略。这些对应的形式如何构成最后的和解呢?这是双方剑拔弩张的形式,其内在的双方都有服软示弱的人性和解,要解决整体矛盾,个体都要付出部分牺牲,牺牲一些角色的身份,上升一些人的地位,不然《地盘》的故事会永远没有结局。这并不是现代社会城市里某一个角落的简单争斗,原始灵魂乞求和解是每一个人也是他者的愿望。这既是个人也是群体的愿望,这就是氏族社会以来为什么有那么多帮派团体,而个人也不断被纳入组织化进程。这就是马塞尔·莫斯说的氏族整体性,“一方面,氏族被认为是由某些人也即人物构成的;而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人的角色实际上是要各自预先表现氏族的整体性。”如果不立足共同的人性基础,人类和平便是一句空话,不仅如此,一个家族内部的传统、名誉、种族遗传特色都具有这种个人性与整体性。奶奶的象征具有极大的严肃性——最后的种子,奶奶最后毕尽了光辉,她是最后的吗?她的孙子身体里依旧还有茴的营养,人不灭物种不灭,作为食物灭的仅是个案,不灭的还是整体的流传,茴永远会作为粮食的一部分。但是某种生物学上的类的灭绝一定会产生巨大悲剧,从个案上讲,奶奶与茴有探索人类命运深度的启示。安南茴作为三百年前平江山区的主要粮食,它的传承成为奶奶家族的生产方式,也作为生活方式,继而成了安身立命的族传遗产,从粮食遗传到种族生命遗传,都与茴息息相关。这样写奶奶就是写茴种,写茴叶便是写生命,奶奶和物种无论生命性质还是日常生活方式均保持惊人的生命同步。家族是传承演变的,奶奶和茴也是传承演变的,奶奶在一个庞大的家族传承中,茴作为番薯的象征流传,从生命性质上保持某种同构,只不过茴在泥土中作为种子传递。人活在现实生活中以社会方式作为演变,表明了生物意义上的所有生命都是同根,人的生命并不比其他生命优先,伤害其他生命也是伤害人类自身,这就有了一个大的生物圈的理念。关键在于作者“我”作为“孙子”在这个生命传递过程中感同身受,具有一种命运反思与感叹,这样既增加文本叙事的可信任度,又增加了艺术真实的感染力。我们说把它作为人类学的一个标本,而且真正具有田野考察作用,特别是在社会特别强调生态平衡和物种生存的今天,它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今天我们考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无不与生态环境相关联,任何生命形式的存在与灭亡都会被视为人类史、地球史上的重大事件,再参照社会现代性反思,我们会有更具建设性的新的世界观。

(三)
丘脊梁以后将面对的是两个大问题:其一是如何处理大材料和大文本,在结构上把握文本的整体,使局部更有机地与整体融合。说得更明白一点是局部分布如何在一个宏大整体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在万字以内的文本中他可以得心应手地处理,庞大的中长篇呢?有时候可能凭借激情,一个局部拉得很远,再回头看它与整体就不合。或者又写一个更大的局部,这是一种结构上的控制能力,恐怕脊梁要加强训练。其二是运用一种什么样的话语方式,以何种口气一贯到底,当然,目前他以激情式的叙事方式,保持某种快捷的节奏,语言有流动性。但这并不能适应他的整体创作,也不宜风格化。似乎要另辟蹊径,选择,或者是锻造一种更成熟的话语方式。我观察他这两年的写作,他渐渐地找到了一种语言,并把这种语言方式文体化,渐成风格。这从两个文本里显示出特征:《从郊野抵达内部》(散文)、《最后的种子》(小说)两个文本的语言似乎构成了他对过去文本的反抗,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机制。过去他的文本过多地受情绪左右,特别是快节奏地安排语言关系,小说具有一种现代性氛围,这样很容易把文体变成一种煽情的读本。从这两个文本开始,他增加了语言表述的客观性,从容不迫地让词语展开,裸露词语与事物本质的勾连,在一种展示中消弭了些许节奏性,代之以句子带动词语的旋律感,应该说这是一种保守式的古典方法的写作,可这样它更有中国意象和中国风韵。为了记忆整理过往的事物,因为害怕遗忘便慢慢地铺展事物,清溪及清溪所有的景物,是靠事物自身的关联被连带出来的,注意句子和词语中声音因素的处理,有意使其和雨丝、溪流、轻风同时保持一种速度,这是语言速度带出的淡淡的抒情意味。一条与道路相连的河流,交汇式的江流,人生非常自然地进入了它的命运河流,侧重于河流上的纤夫,把流水写成命运之书、命运之关,这当然是常态书写,但因其语言、河流、心境三者是一致的速度,它的味道就产生于其中,写湖,落点在草地与树,揭示一种生命的真相,使它具有一种醒目的、让人心动的新的呈现,使一种生物生命与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可喜的是,他真正由表述一种事物外部达及了一种事物的内部和人物心灵的内在体验状态,所有客观物都有一种自我魂灵的掌握,舒收自如,仍由一种情韵的挥洒。真正做到了客观事物不能和主观情绪分离。自《最后的种子》开始,他有了一种自己说话的方式。我称之为本色叙事,这是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说话方式。首先,他使用地域性口语,压着语调,控制速度,和奶奶、父亲、家人保持同一速度,有一种情调上的对话关系,这样产生的效果便是如说家常,略带一点语言倾诉。其次,他的词语也带有地方性,首选的对象物红薯,他使用的是“茴”。关于茴的生产知识具有地方性,例如翻藤、挖茴、存种等方式极具地方性,山区是这样,而湖滨平原控制薯藤疯长是要剪藤的,同时红薯藤叶是可以做菜的。最后,他的口语因其家族的对话,一切生活风俗、节庆心理都保持了地方和家族特色。文本内人物命名、人称、生活故事与人物同步,家族传奇与茴的物种关联都是极具个人化的。由于这种本色叙事是与家族相关的,所以生产茴的过程也是家族教育的过程,奶奶是一个人性的教育家。本色叙事必须在语言上保持个人说话的特色,这包括家族和个人习惯的用语,这种语言有一个度,太私人化了别人会听不懂,太大众化了语言会平贱而俗套,还要安排一套合适的说话速度和韵调。可见本色一词是指个人之特色。安排好个人特色的语言,就要有独特的句子表达方式,长短句的处理,词汇组合的反常配置,口语的和书面的语言结合。尽量少用逻辑语言,强化词语的感性,要特别尊重个人直觉。总之,这是丘脊梁的本色叙事的开始。
2016年12月于岳阳
(作者系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先锋小说集大成者。此文为贵州民族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的丘脊梁中短篇小说集《地盘》的代序,有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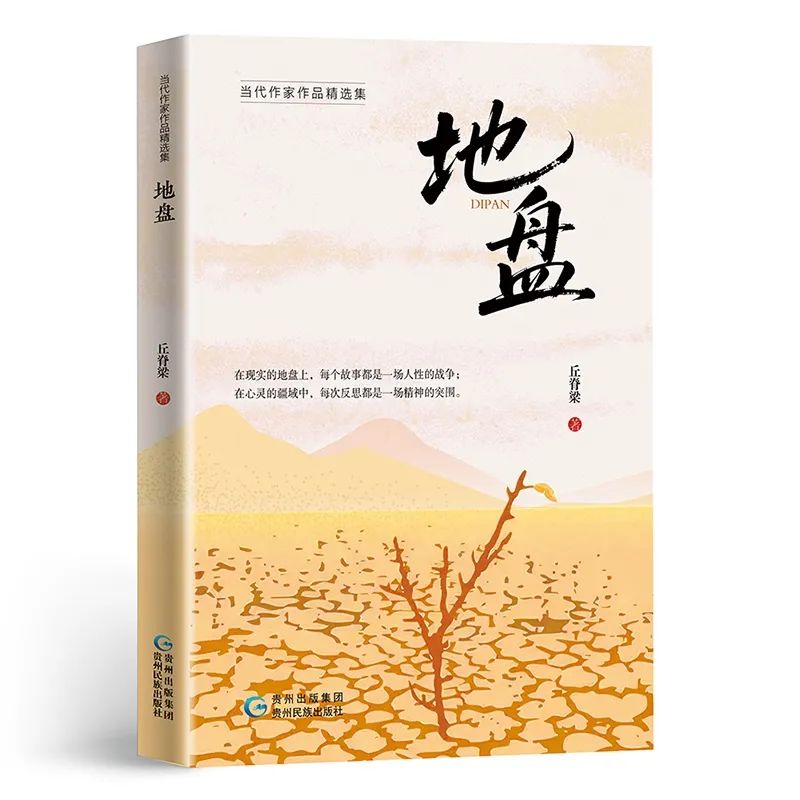
摘自《岳阳日报》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范彬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