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荣学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5-08-18 11:16: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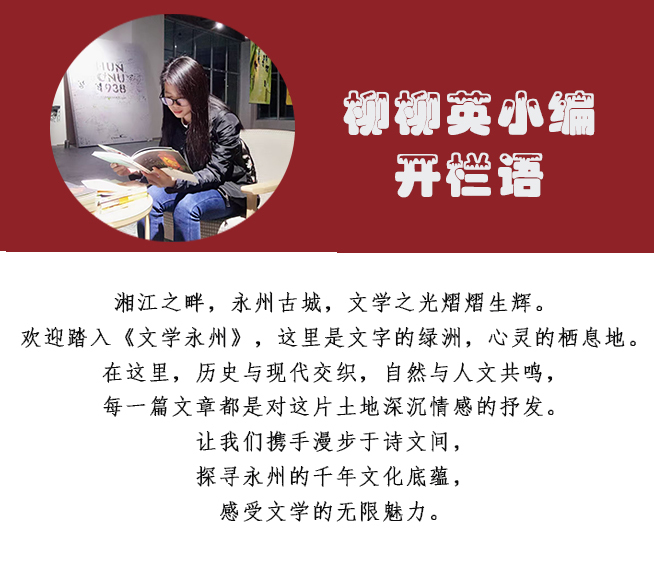
瑶人(组诗)
■赵荣学
瑶人是五岭山脉
脊梁上的一道印痕
盘王的马鞭抽过的地方
长出倔强的吊脚楼
像不肯低头的山鹰
在云雾里筑巢
瑶人的族谱
是用猎刀刻在
迁徙路上的记号——
过洞庭时丢下一支木桨
渡湘江时埋了半截牛角
最后把长鼓的鼓点
种在冯河两岸
长成好大一片油茶林
瑶人的脾气
是长鼓舞扬起的火屑
落在高山下的梯田里
嗤的一声
变成插秧时节
抛掷的泥点
瑶人的无畏
是放排人腰间
那柄从不入鞘的弯刀
劈开过十八道险滩
也削过木匠的墨线
最后钉在祠堂梁上
瑶人的坚持
是十八酿里
那枚总也煮不化的野山椒
老婆说太烈
瑶人却用它
就着县志里瑶族"义学"的记载
咽下三碗包谷烧
瑶人的魂魄
终将变成铜铃上的雪
落在瓦当
与青石板
当春风翻过萌渚岭
每一滴融化的水珠里
都有盘王图腾
和楷书碑文
在静静拥抱
 涔天河水库。李忠林摄
涔天河水库。李忠林摄
涔天河的雾和雨
涔天河的雾
是盘王未讲完的故事
在吊脚楼的檐角
缠了又缠
直到炊烟把它纺成
晾在晒衣竿上的
半截瑶锦
多雨的河啊
总在立春时分
把迁徙的苦楚
一遍遍淘洗——
上游沉的是铜鼓
下游漂的是斗笠
只有中游的漩涡里
旋转着货郎遗落的
算盘珠子
雾起时
长鼓声变得潮湿
像浸了水的火绳
怎么点也点不着
腊肉的香气
却趁机钻进对岸
祠堂的雕花窗棂
雨落处
放排人的号子
突然长出青苔
那些险滩下的暗礁
是祖先埋在河床的
倔强牙齿
咬碎过多少
顺流而下的谎言
如今大坝截住的
何止是流水
还有雾里
总也看不清的
瑶山倒影
多雨的河啊
终将把瑶人们的故事
冲积成
河口的
三角洲平原
 涔天河风光。李忠林摄
涔天河风光。李忠林摄
山那边
山那边还是山
阿爸的柴刀说
砍不完的杉树
像山主账簿上的数字
一页页翻过去
都是相似的年轮
山那边有圩场
阿妈的银饰说
要走过十八道盘山雾
才能换回
一包绣花针
和半斤盐巴的体面
山那边通县城
教书先生的地图说
铅笔画的虚线
穿过三个瑶寨
两个汉人村庄
最后断在
涔天河水库的蓝墨水渍里
山那边藏着海
放排人的酒话里
冯河连着洞庭
洞庭通着长江
长江的水啊
泡得软千年崖石
却泡不软
瑶人们系在腰间的
铜铃铛
如今高速公路
像条银蛇钻过隧道
把山那边
拽到车轮底下
后生们穿着混纺的
衣裳
在服务区便利店
买红牛饮料时
总听见收银台后面
传来隐隐的
长鼓回声
进城
瑶人的解放鞋底
还粘着盘王庙前的黄泥
在公交站台
踩出歪斜的印章
像祖辈画押的
那份永远不对等的
山场契约
电梯镜子里的银项圈
突然变得很重
压得二维码扫描仪
发出"嘀"的惨叫
像那年寨老
射中云豹时
箭镞的颤音
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把阳光切成
等宽的条形码
瑶人站在格子间
数自己的影子
突然想起阿爸的警告:
"城里人的屋檐下
要记得低头"
可电梯里的监控探头
正把瑶人的盘王印
拍得清清楚楚
快餐店的辣椒酱
淡得像掺了谎话
瑶人偷偷从挎包掏出
坛子里的酸辣剁椒
辣得隔壁穿西装的
后生直咳嗽
他衬衫第二颗纽扣
别着和瑶人一样的
瑶族图腾徽章
深夜加班时
手机突然响起
《盘王大歌》的铃声
主管皱起的眉头
像极了姑婆山
最险的那道褶皱
瑶人按下静音键
却按不住
显示器上
不断跳动的
瓜箪酒的节奏
瑶人娶了个客家人老婆
她的山歌比瑶人的盘王大歌调软,
像糯米酒里泡着的红曲,
甜得让盘王的猎犬都打盹。
她的围裙兜着梅菜香,
瑶人打来的野山鸡炖在瓦罐里,
她说太柴,
又加了一勺猪油,
像汉人的契约,
总要多垫一层人情。
她骂瑶人时像涔天河的急滩,
客家话混着瑶语,
溅得吊脚楼板啪啪响。
可夜里帮瑶人揉打猎扭伤的腰,
手掌又像晒软的糍粑,
黏住所有瑶人没喊出的疼。
清明她拜她的围龙屋祖先,
瑶人敬瑶人的盘王神位,
香炉挨着香炉,
青烟在半空握手言和。
孩子们在供桌下偷吃米粿,
齿缝粘着艾草和笋干,
分不清哪样是客家,
哪样算瑶山。
如今她的腌菜坛子,
霸占了瑶人泡蛇酒的角落。
而瑶人的芦笛,
成了她晒咸菜的压石。
寨老摇头说乱了祖制,
可山神昨夜托梦——
坛沿的水要是干了,
记得添一勺冯河的月光。
 水口镇水街风情。江华宣传部供图
水口镇水街风情。江华宣传部供图
瑶人的老母亲要在韶山唱瑶歌
她执意要带上那副银镯子,
像带着两轮小小的月亮,
怕韶山的太阳太亮,
照不见瑶山的雪。
她的瑶歌是祖传的,
比长鼓的麂皮还老,
在吊脚楼的火塘边煨了七十年,
如今要翻过五岭,
去红土地里,
种一粒带盘王印的音符。
瑶人怕她的调子太陡,
像瑶人们迁徙的山路,
城里人听不懂那些悬崖。
她却说歌里有糯米酒,
能醉倒所有坚硬的目光——
"当年红军路过瑶寨,
不也喝过瑶人们的油茶?"
她站在铜像前开嗓时,
山风突然安静。
那些盘旋的、属于伟人的鸽子,
突然学会了
长鼓舞的切分节奏。
归途的动车上,
她靠着窗睡熟了,
手心里还攥着
一片韶山冲的竹叶。
而广播里的到站提示,
正用标准的普通话,
轻轻复述着
她歌里那个
关于火塘与星子的
古老韵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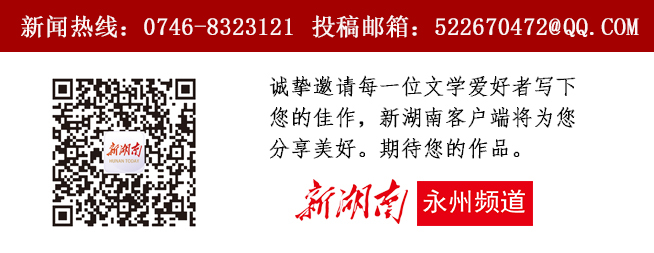
责编:黄柳英
一审:黄柳英
二审:李礼壹
三审:李寒露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