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书屋》 2025-08-07 17:0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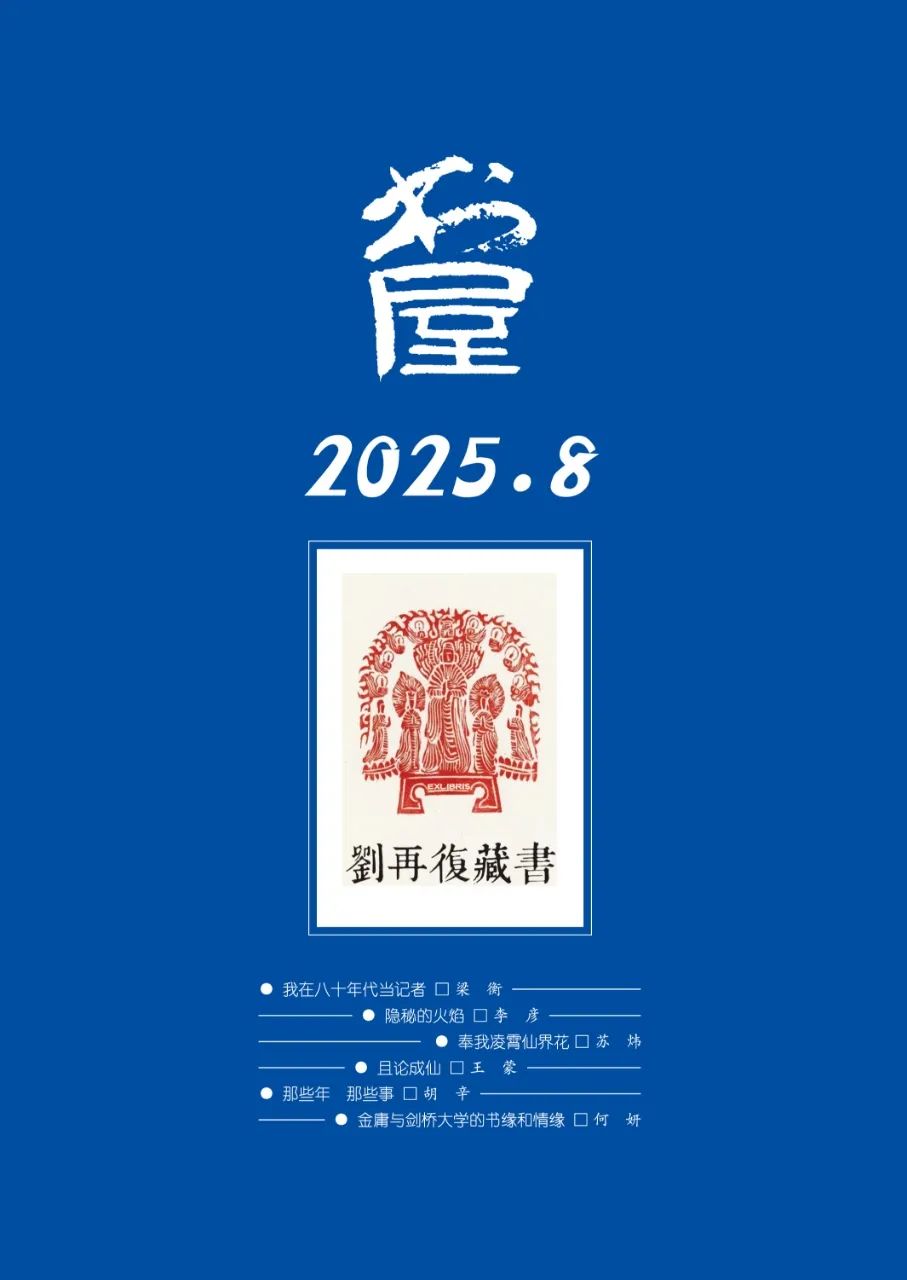
文/陈漱渝
儿时作文,凡形容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必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八个字,但用多了就成了陈词滥调。老来细想,时光瞬间即逝,用飞箭和织梭来形容,不正是十分形象贴切吗?可见不仅人生当中难免要受点委屈,连一个成语也难免会受委屈。今年是我本命年,恰逢八十四岁这一坎,所以学习鲁迅,凡事都“要赶快做”,不拖欠工作债。
《书屋》编辑说我对创办杂志“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完全是奖掖之词,只不过是一种缘分罢了。当年,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为什么要创办这样一份杂志,我完全不清楚,只知道最初为此事奔走的是周实和王平两位。周实的头衔开始似乎是“常务副主编”,后来成了主编,有终审之权,主要搭档就是王平,还有另外一位美编。所以《书屋》的老作者和老读者一提到这份刊物,就会想到周实和王平。
周实是一位诗人,又擅长写长篇小说,内容有的惊世骇俗。我曾见他牵一条猛犬上街,着实吓我一跳,读他的某些历史小说,我也有这种“怦然心跳”之感。按说周实已是古稀之人了,对新事物应该生疏,但他不仅能把自己的诗作配上图,还配上曲,在网上热播。可见他十分新潮,居然能使用AI工具进行“音乐生成”。我认识周实应该是在1986年。当时我到上海档案馆查阅宋庆龄的资料,因丁景唐先生介绍,下榻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招待所。同住这家招待所的,正巧有当时湖南文艺出版社《芙蓉》编辑部主任朱树诚——他后来因编辑著名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而广为人知。周实是他的同行者。因为都是湖南人,所以聊得开心,从此就成了熟人、友人,三十多年一直保持联系。周实写过一篇夸我的短文,题为《三哥陈漱渝》,还预告要再写一篇长的,再夸我一下。我在期待着。
至于王平,我舅舅的儿子,是有血缘关系的近亲。舅舅只是一个小职员,“文革”期间下放到车间,扛了几年麻袋——里面装的是沉甸甸的矿石粉。舅妈年轻时是校花级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初期想向苏联妇女学习,争当“英雄母亲”,因此一连生了七个子女,无法外出工作,全靠舅舅那五十几块钱的月薪维持生计。我这七个表兄弟姐妹中,没有人上过大学。王平在他的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小我十岁。我到天津上大学时他刚六岁。大约是小学六年级时,王平因患骨结核动了手术,躺在床上,把一只绑了石膏的腿吊起来,笑眯眯地叫我“三哥”,让我印象深刻。王平还喜好“涂鸦”,曾用毛笔把一匹马画在家里的白墙上,长约两尺,童年时代即显示出艺术潜能。据作家莫言说,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放牧牛羊。王平学历高于莫言,小学确实毕业了,只是再没上过中学。他二十八岁那年发表处女作,因为当时他在一个街道办的小厂当车工,所以赢得了一顶“工人作家”的桂冠。我清晰地记得,1986年岁末的一天晚上,我到北京火车站迎接进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湖南代表团,团员中除开残雪、何立伟、蒋子丹这些朝气蓬勃的作家之外,也赫然有我这位表弟的身影。1987年,他大胆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开设的作家班,考试内容当然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部分,王平只找人帮他补习了两天,居然考试合格,被光荣录取。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生活窘迫,因为街道工厂每月只补贴他五十元,他必须靠写稿和借贷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好在历经风雨即见彩虹,1989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后调入了湖南文艺出版社,后又调进了省出版局。他跟周实一起创办《书屋》,就是1995年的事情。
刊物办得好与坏,既取决于编者,也取决于作者。周实跟王平组稿之重点,当然首选北京,然后是上海。我当时所做的事,就是替他们邀请了七八位在京城文坛活跃的作者,在鲁迅博物馆对面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便饭,想通过抓住胃的方式抓住作者的心。后来《书屋》给我支付了一点组稿费,钱不多,但隆情厚谊。过了不久,组稿费自然就停发了,因为《书屋》的局面已经打开。来稿多版面少,不用任何人来“组”什么稿了。在初次宴请的作者中,有一位老学者舒芜。后来,王平去他家拜访,他怕外地人找不着门,七十多岁的舒芜长久站在家门口候着,迎来送往,让我十分感动。
现在话题必须由创刊人回到刊物本身。由于年事高,我在文化圈子里结交了各式各样的朋友。他们的学术专业和审美倾向不尽相同,但提起《书屋》杂志,除开希望能提高稿酬标准之外,真还没有听到什么差评。在提倡全民阅读的当下,读书一类报刊又在逐渐减少,《书屋》的存在本身就显示出了它的文化活力。《书屋》之所以一炮走红,至今仍然口碑不错,我认为是保持了刊物独有的思想文化品位。其独特性之一,就是包容性强。只需看看《书屋》开辟的栏目,将近二十种,就显示出了蔡元培先生在五四时期提倡的文化守正、兼容并包精神。即以我在《书屋》发表的文章而论,有书评,有自传,有文化随笔,还有不少学术争鸣性的文章——这类文章有些刊物是唯恐避之不远的。当然,政治有红线,宣传有纪律,但读书无禁区,学术无禁区。只有胆识兼备的编辑才能妥善处理好这种关系,使刊物始终洋溢着文化朝气。容我举一个例子:
2023年11月8日,温儒敏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九十沧桑乐黛云》,全文又被《新华文摘》转载。文中写道:鲁迅死后,刘半农写过一副挽联,词曰“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裴伟先生在《书屋》2024年第五期刊发了一篇质疑文章,题为《刘半农给鲁迅写挽联?》。文章指出:一,“这副联不像挽联”,并非为哀悼逝者而作。二,刘半农卒于1934年7月14日,鲁迅卒于1936年10月19日。刘半农比鲁迅早死两年,怎么有可能为鲁迅写挽联呢?我把《书屋》上质疑的文章转告老温。老温从善如流,立即回复了两个字“认错”。他接着表示:“非常感谢这位作者,我不该出现这硬伤。明明知道刘半农死后,鲁迅是写过《忆刘半农君》的,但下笔却把‘对联’(联语)误写成‘挽联’。我要公开认错。”后来,老温真的在他的微博上就此事表示了歉意,承认他记性不好,写文章还随意。这就是大家风范!这件事就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是意气之争。鲁迅历来主张批评家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捧杀”或“骂杀”,但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的确存在鲁迅所反对的这两种倾向:或者把对方捧为泰山北斗,佛光罩体;或者“谁红跟谁急”,奉行“骂倒名人自己成名”的文化策略。我希望《书屋》能继续发扬“激浊扬清”的文坛正气,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在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中迸发出真理的火花。
孔子说“三十而立”,“立”就是有所成就。《书屋》这三十年的成就,是通过编者、作者、读者三方面的合力而取得的。在今后的日子里,我期待《书屋》坚守办刊的初衷和本真,继续为读者提供一个群贤毕至、色彩纷呈的精神家园,让充满芸香的书籍熏陶心灵,用诸家荟萃的书屋丰富人生。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范彬
来源:《书屋》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