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联 2022-08-12 09:11:12
文丨方雪梅
我没有去过怀化的侗乡,却对那里的山水充满了敬意。仿佛一腔情志,与侗乡的晴阳秋月、寂寂青山以及风土人情融为了一体。这感觉的得来,缘于阅读姚茂椿散文集《苍山血脉》。从他疏壮、真挚的文字里,我感受到这个侗族作家的万丈乡情如遏云裂石的瀑布,直抵人心。更难得的是,在《苍山血脉》的字里行间,有一种清晰的文化路向,那便是从一个较大的角度,回望湘黔桂边地侗乡的历史风烟,关注其正在变化的现状,思考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体现了对民族地区的一种文化层面的大深情与大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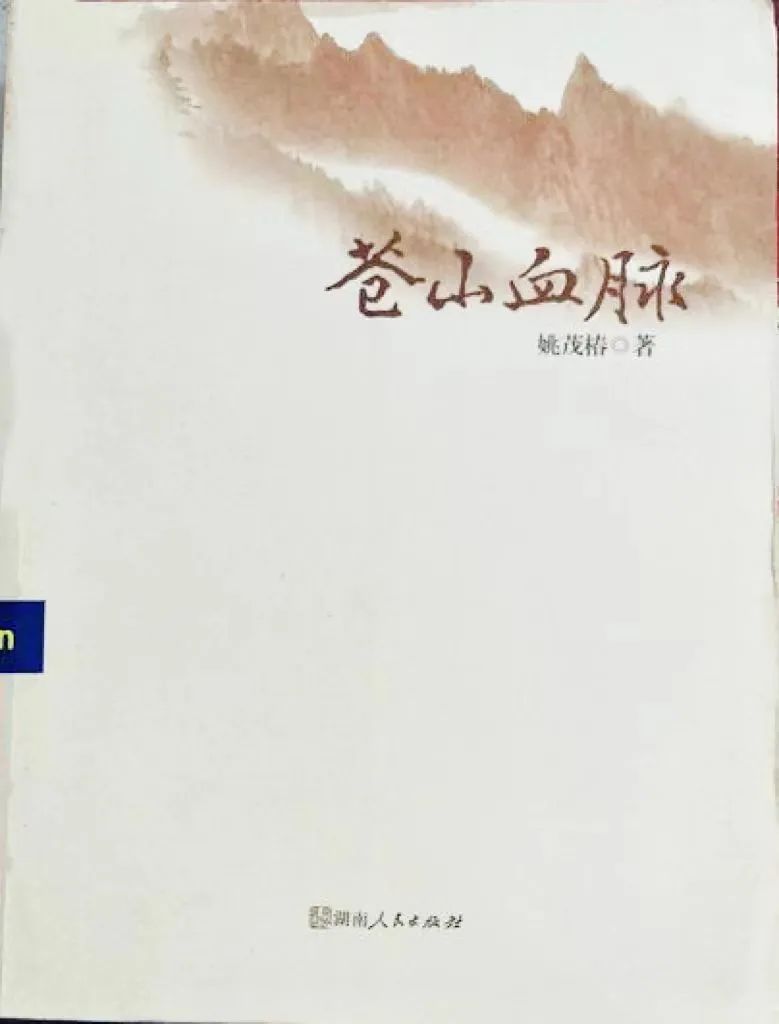
这种大关怀,在《故园屐痕》《长梦依稀》《心的律动》《大歌音符》这四辑里,随处可读到,可以说贯穿于全书。它牵情于连绵苍山里侗乡的一山一寨,一草一木;牵情于侗家的先祖足迹,故人旧事;牵情于家族亲情与民族血脉。这样的情感是宏阔的、大境界的。
作为一名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侗乡儿子,姚茂椿心头聚集着浓郁的乡情,可谓意绪绵绵。故乡山水的养育,侗家风士人情的浸染,朴实民风的教化,在他身上烙下了纯朴的印记,使他有了真诚的秉性与豁达胸怀,这也注定了他用特别的感知方式来解读侗民族的今昔,眺望其未来。这种解读,也可以说就是俯身自视、自肃自策般的解读。
在书中,我们看到作者关注的是湘黔桂边地、古老侗乡地域上,民生的改善、历史缔结的文明硕果,积淀的文化脉络,以及经济文化、社会进步与周边环境的变化。作者笔下,给我们铺展了一幅美丽的侗乡长卷画:风雨桥、古井、鼓楼、火塘、门楼、驿道、花阶、宝塔,拦门歌、侗族大歌、平溪、舞水;深山小学的孩子,开屋基的乡亲,老街店铺的乡邻,山里的牧牛人,乡场上的挑担者,八拱桥边的侗家歌手,还有扶罗镇外,苍茫青山里长眠的祖父、婆姨、叔祖母与母亲……侗乡的美丽山水与质朴人事,是作者心头最温暖的记忆,也成为读者眼睛里最具民族情怀的写作。
多年前,茂椿兄与众多侗家儿女一样,怀着理想,沿着出山的路,沿着绵延的花阶,告别侗乡,外出读书、工作,且“山里的人们还会在漫长的岁月里,扇动理想的翅膀,一群一群地走出大山”(《出山的路》),但故乡的风物,时时盘桓在他的心头,那充满生命张力的溪水、河流、侗族大歌、芦笙,总在他血管里轰隆作响:“生命里有的声音,渗入了灵魂,不论人们步入何时何地,都将伴随他们一生。”(《耳畔的夜声》)茂椿兄从侗寨出来,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名学子,毕业后又回到故乡,成为教书育人的园丁,此后,到县委工作,再到省城这个更阔大的天地发展,成为省人大代表。他的个人成长历史,契合着时代与社会前行的进程,亦见证着湘黔桂边地侗乡的发展与变迁。所以,他的写作,是从“小我”出发,关注民族“大我”、为民族发声的高境界写作。
在《苍山血脉》一书里,他没有单纯停留在对乡情、亲情、故土风物、往事的回味中,而是在咀嚼这份滋养着自己人生的情感时,将其疼痛处、诟病处与贫弱处,端放在心头,并被它不断煎熬和挤压。因此,他有了深重的忧思。
在南部侗乡行走,他从无数令人喜悦的变化里,看到了疼痛点:侗乡发展了,但横向比较,还处于相当落后的境地,当地父老乡亲生活的艰辛与内心的焦虑,让他感受到现实的沉重与人们希望的迫切;“大湘西地区”虽然享受国家西部开发的一些待遇,但发展的压力还很大,生产生活污染、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等问题同样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交通不畅成为最大的瓶颈,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缓慢,缺乏资金、人才……这一系列困扰着边远地区与民族地区发展的问题,在他的心里沉重如故乡绵延的高山。
尤其是,在多年后,看到故乡土地上,随着市场经济意识的日渐浓郁、一些老地名、一些历史遗存的消失,更是让他的文字承载起呼吁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的责任:“大多数时候,老地名有故事,老地名有文化,老地名甚至还有灵魂。对于这些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如果不论青红皂白地从生活中抹掉,总有一天,人们将会遗憾,甚至会痛心疾首。”(《醉卧乡间不知里》)与此同时,看到故土上,淳朴的乡风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部分人观念变得物欲、自私……他心里仿佛裂开了一道豁口。
所以,他在用质朴而真诚的文字,赞美故土的山水、缅怀履霜践冰的先人、回味童年趣事的同时,更多地用理性的思考在寻找本民族血脉深处的宽厚气韵与生命的来源;寻找边地的底蕴深涵,与走出地域囿困的发展通途。
这就决定了其散文走向的通善融雅,丰厚可读;也使得读者,不会单纯在他的文字里遣怀雨润烟浓的山水,而是时时体味感性与理性交融之美。
正如茂椿兄所言:“作者不应该只是时代与生活的记录者,还应该是有良知的思想者。”《苍山血脉》让我感悟到“乡情”这个永恒母题背后,永恒的赤子情怀与民族深情;感悟到民族的精神血脉正是在这种文化层面的大关怀里,才得以不息奔腾的。
所以,于我,这是一本真正值得把卷必尽的书。我想,于其他读者亦然。
责编:周听听
来源:湖南文联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