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网 2021-10-16 17:5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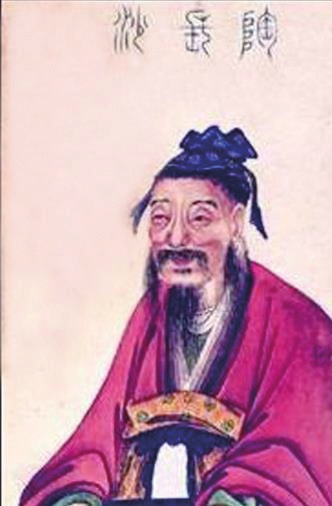
陶侃,字士行,鄱阳郡人。东晋初年,天下纷乱已久,外有胡骑野望,内有叛军挥戈,可谓国乏民疲,动荡四起。东晋政权在此情况下也是危如累卵,朝廷重臣个个心思浮动,或欲归隐山林,做闲云野鹤,或欲拥兵自重,伺机谋反。唯陶侃于此危难之际内击叛军、外震胡虏,力保东晋朝廷,体现了忠勇刚毅的品质。
始怀忠勇之心。东晋初立江东,大乱方平,根基未稳,此时的陶侃忠于东晋朝廷奋勇杀敌,开始在军中崭露头角,后又在征战中屡获战功。战功卓著的陶侃引起了大臣王敦的嫉妒,王敦出身“王与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是丞相王导的堂兄,东晋开国重臣。一次,他竟借故强留陶侃于军中,“被甲持矛,将杀侃”。但陶侃毕竟威名在外,王敦一时无法下定决心,以致往来传信的使者“出而复回者数四”。陶侃见此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后王敦经与谋士反复斟酌利害关系,放弃了杀害陶侃的打算,陶侃才死里逃生。咸和四年,陶侃升任侍中、太尉,都督七州军事,位极人臣。由于被权臣所忌恨和陷害,几经生死,他却从未对东晋朝廷生二心,虽然重兵在握也没有效仿王敦倾覆朝政自立为王,反而更加勤于王事。同年,郭默矫诏,袭杀平南将军刘胤,自立为江州刺史。陶侃与王导书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并请出兵讨伐,以绝天下不臣之心。迫于陶侃威名,大军刚到,郭默的手下宗侯便绑缚郭默父子五人及另一叛将张丑向陶侃投降,兵不血刃平定叛乱。
咸和九年,陶侃又于盛名之下急流勇退,在病中上表逊位,封印府库,并遣人向朝廷移交符节印信,以安人心。可见其忠勇之至。无怪乎苏轼亦盛赞他:“威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
力行刚正之事。众所周知,晋室立国不正,明帝听王导讲述“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后都感到羞耻,“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所以天下士人终两晋一代,或者趋炎附势,以求富贵,或者醉心清谈,言皆玄远,其中尤以后者势盛,他们专为虚言而鄙夷实务。而陶侃与他们截然不同,他性情刚正,反对虚妄时俗,“勤于吏职,恭而近礼”。《晋阳秋》记载:“侃勤而整,自强不息。又好督劝于人,常云‘民生在勤……岂可游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又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这番话于当时可谓振聋发聩,有提振世风之力。
陶侃力行实务,以身作则,如此要求自己,也如此要求僚属百姓。有次出游,他见路边有人手持一束尚未成熟的稻子,便问:“用此何为?”那人答:“行道所见,聊取之耳。”陶侃闻言怒不可遏,斥责道:“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扬鞭便打。百姓听说这件事后便更加勤于农事,家给人足。若有向他奉送礼物的人,他便“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故此他所治下尤为勤整,史称“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
一生坚毅隐忍。陶侃“在军四十一载,雄毅有权,明悟善决断”。早年任武昌太守时,其辖内有山贼出没,大肆劫掠往来商贾。陶侃设计抓获数人后,发现这伙山贼竟是西阳王司马羕的部下,但他没有畏于权贵,息事宁人,而是毅然整军列阵,奉公执法,逼迫西阳王交出匪徒,就地斩首。从此武昌境内“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此后陶侃领军作战更是“独当大寇,无征不克,群丑破灭”,威震海内。
咸和二年,苏峻叛乱,还将陶侃之子陶瞻残忍杀害。不久,陶侃即奉命与温峤、庾亮等会同剿贼,并被推为盟主。但他并未因报仇心切而鲁莽行事,反倒在“诸军即欲决战”时指出,贼军势头正盛,不可与之争锋。其临敌时内心的坚毅隐忍可想而知。后来两军对峙,久战无功,他也未情急生乱,而是从容分析形势,听取正确建议,最终阵前斩杀敌人,平定叛乱。而杀害了陶瞻的苏峻部将冯铁,虽然北奔于石勒,但石勒慑于陶公威名亦不敢多留,遂“召而杀之”。陶侃的功绩亦无愧乎配享武庙,受人供奉。
陶侃生于乱世,却因忠勇坚毅而成为乱世中的“定海神针”;出于寒门,却因“贞固足以干事”而于寒门中“拔萃陬落之间,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宏总上流”。作为东晋一代名将,陶侃以其忠勇、刚正、坚毅,在史书上留下了为后世所敬仰的风流神采。
责编:万枝典
来源:理论网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