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鼠读书会 2018-10-27 12:20:18

这些年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是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的?”
姚晨站在“星空演讲”的舞台上满脸困惑,“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先生这个问题?”
当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女性走入职场,但“女强人”却不是一个完全的“褒义词”,常伴随着“靠美色上位”的猜疑;而当生育期来临,职场女性又常面临着工作不保的危机,出现了“插队怀孕被辞退”等让人诧异的新闻;紧接着漫长的育儿期,许多丈夫缺席家务和育儿,让职业女性焦头烂额地奔走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丧偶式育儿”一词迅速走红。
五年生了两个孩子,身材走形,错失了很多好剧本,年近40的演员姚晨在电影《找到你》中说:“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如果你选择成为职业女性,就会有人说你不顾家庭,是个糟糕的母亲。如果你选择成为全职妈妈,又有人说生儿育女是女人应尽的本分,这不算一个职业。事实却是,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力;因为当妈妈,我才了解生命的意义,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残酷。这两个身份并不矛盾。”

这段话或许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旁白的最后一句并未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一场女性的自我“和解”。可是,电影中三个尝试“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女性通通失败了,现实生活中的姚晨知道,“事业和家庭是无法兼顾的”。
那么依然回到那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少人问“先生”,“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家务一定是女性的分内事么?男人回归家庭做家务会怎么样?对此,我们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一起来探讨今天女性所面临的“兼顾”困境。
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几乎是男性的三倍
李捷,职业律师,干练多金,一边拼命工作一边请保姆带孩子的成功职场女性,与前夫争夺女儿抚养权。忽然一天,女儿失踪。她深夜报警,警察一脸责怪,“这么晚才来报案?”她心力交瘁地说,“白天上班”。

朱敏,名校毕业,嫁入豪门,成为家庭主妇,但丈夫却在她怀孕时出轨。她患上了抑郁症,又没工作,在争夺孩子抚养权处于极度被动。而前夫的代理律师正好是李捷。李捷在庭外对朱敏说,“我既要照顾家庭也要工作,就是因为害怕有一天,像你一样被动。”

孙芳,出身农村,嫁到城市,但是丈夫有家暴行为。她生了一个女儿,却不幸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丈夫撒手不管,但她不肯放弃,甚至做妓女、做保姆为孩子治病赚钱。

这三个女人来自最近电影《找到你》,或许有人会说,电影太“戏剧”了,现实不会这么“惨”。那么,我们来看看现实。
杨菊华在《传续与策略:1990—2010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一文中,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丈夫和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分配。她发现,从1990年到2010年,无论在哪个时点,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都大大超过男性,家务时间几乎是男性的三倍。
那么,有人会说,丈夫要出门工作,当然没那么多时间做家务。可是,当杨菊华将性别观念、时间可及、资源多寡,以及年龄、户籍、子女数量、地区、时点等要素纳入考量,当条件都一样时,“女性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仍超过男性家务劳动时间100多分钟;而且,在所有自变量中,性别的作用仅次于工作时间,表明虽然男性家务劳动时间少与他们工作时间长有关,但性别仍是女性家务劳动时间长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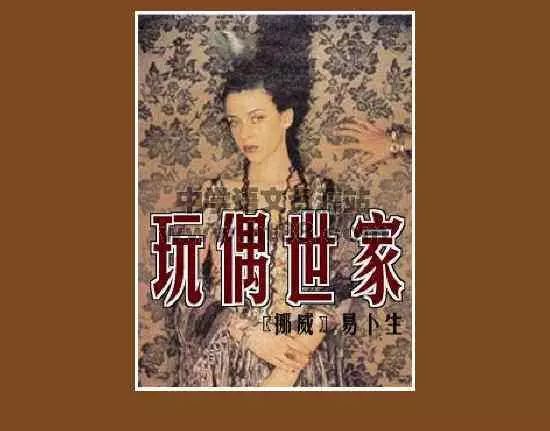
近百年前,鲁迅曾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在易卜生的著名戏剧《玩偶之家》中,看清楚丈夫真实面目的娜拉,毅然决然地走出家门。娜拉走后怎样?鲁迅说,“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除此之外那就还有第三条路,就是饿死”。但觉醒了的娜拉还是要走的,那么“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经济开始独立,她们有钱了,可是经济上的崛起和独立似乎也并未在家务分工上带来太大改观,“即便失业的丈夫时间充裕,但‘男性尊严’和‘男性气质’驱使他们远离家务”。
毋庸置疑,近百年的女性解放让女性终于可以走出闺房,接受教育、走入职场、拥有选举权,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位和权力。但在她们走进职场,与男性一起工作和竞争,分担起养家糊口责任的同时,依然肩负着做家务相夫教子的“义务”。“男女平等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以女性双肩挑为前提的。在西方国家,家务的分担模式是,将男性从家庭外部拉进家庭内部,形成男性的‘外-内’模式,丈夫成为妻子有效的替补人选。而在中国,则是在多数男性依旧延续着‘主外’的一元模式下,女性在普遍参加社会劳动的同时,依旧保持家务负担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形成女性的‘内-外’二元模式。”
于是,这形成了一种拉力,“一方面,根据传统角色定位,我们对于母亲妻子是有期待的,理想的妻子是可以随时随地为自己的家庭做服务;但同时社会和单位对理想员工也是有期待的,要求员工心中视职业高于家庭。在理想员工和理想母亲妻子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可能最后,女性会牺牲职场发展回归家庭,而男性却很少受到这种张力的拉扯。”杨菊华说。

做家务可能是女性的一种“策略选择”
更让人惊讶的是,做家务可能是女性的一种“策略选择”。
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要拴住男人的心,先抓住男人的胃”;自古至今夸赞女性的一个词汇是“贤妻良母”。电视里、广告里常看到这样的画面,温馨干净的厨房里,总有一个系着围裙忙碌在灶台边的妻子,她端出一碗碗热腾腾的饭菜,用温柔的声音招呼:“吃饭了!”
于是,在很多家庭中,女性会主动地打扫卫生收拾房子,烧出拿手的饭菜,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这是因为,“若家务劳动可给女性带来稳定感、安全感,并维持家庭和谐与稳定,则一直被看成负担的家务也可能被有意识地当成资源而加以利用。”杨菊华说。
她发现,不同女性采用该策略的动因可能有别:“对于地位较低的女性,她们可能希望通过做好家务而得到‘治家有方’的认可和肯定,进而维系夫妻关系、维持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对于在事业上较为成功的女性,她们也需要处理好家庭内部事务,平衡好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至于成为一个只有事业、没有家庭的‘女强人’;同时,通过做更多的家务表现对丈夫应有的尊重,以减轻丈夫的心理压力,亦避免因社会上的成功而可能产生的忽视家庭的歉疚感。也只有做好‘分内之事’,她们才能更好地得到家庭对她们在社会上打拼的支持。”
于是,又回到了姚晨的那个疑问,为什么不问“先生”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为什么男性不做家务没有“歉疚感”?为什么男性不需要通过做家务来经营婚姻?
杨菊华认为,“究其根源,男性与女性的差别正是父权制度的产物,即不能脱离父权制度来理解女性的这种策略。男性在婚姻中处于强势,在家庭和社会中有更大的选择,离婚的风险较低、成本较小;而且,他们不做或少做家务是理所当然、甚至天经地义的,而女性(即便是事业上十分成功的女性),不做或少做家务则是没有对家庭尽职尽责。因此,她们这种看似自我选择的策略和手段本身透视出的是女性的弱势,尤其是在婚姻市场上的弱势,根植于父权体制,且在该制度框架之下践行的。但是,女性策略不同于性别角色观念,因为策略是主动的选择,尽管选择本身是无奈的;而角色观念是被动的接受。”
男女两性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生活体验截然不同
做家务是女性的分内事,甚至女性自己也认同这个观念,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有人会说,女性天生细腻,适合做不需要太大力气、琐碎需要耐心的事,比如家务、文员、会计等等;男性天生好动,有野心,适合从军、探险、经商等等。所以,男性女性的气质和性格是生理决定的。
美国精神分析教授罗伯特·斯托勒在他所著的《性与性别》(sex and gender)中指出,性具有生物学的属性,而性别是一个心理学的亦即文化的概念,“‘性别’一词具有心理学或文化的而非生物学的含义。如果与性相对应的词语是‘男’或‘女’的话,与性别相对应的词语就是‘男子汉’的和‘女人气’的;后面这两个词很可能与性毫不相干。”
“正如加利福尼亚性别鉴定中心所研究过的那样,一个人可能在出生时就由于生殖器的畸形发育而被作出了错误的性别鉴定。对此,已有的发现表明,如果这是一位未成年的男性,尽管他的生物身份与被鉴定的身份相反,通过外科手术将性改过来还是比较容易的。相反,如果多年的教育已使这个人在姿态、自我感觉、人格和兴趣等方面具备了女人的气质,性的改变就要困难得多。”美国作家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说,“性别角色是由后天的力量决定的,而与实验对象的外生殖器这些解剖学与生物学的因素无关。”
她认为,“男子有着比较发达的肌肉,这一第二位性的特征存在于所有的哺乳动物。从本源上讲,这一差异是生物性的,但同时又是通过教养、饮食和体力运动等在文化的层面上受到鼓励的结果。”
“男子汉”“女人气”究竟是不是生理决定的,或许一时难有十足的定论,但文化在性格塑造上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凯特·米利特认为,“由于我们的社会环境所致,男女两性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他(她)们的生活体验也截然不同。”
“一个朋友生了女孩子,你可能会送洋娃娃,然后夸她漂亮;如果生了一个儿子,你可能会送乐高积木,送车和枪。尽管看起来,这些不过是个小玩具而已,却蕴含着送礼人的理念,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并没有此类观念的孩子心中。”杨菊华说。
或许,有的人看到女性在呼吁“性别平等”时,总会带着某种成见说,“又来要权力了。”实际上,再仔细看看“性别平等”四个字,包含着“男”“女”两性,是男女性别平等。
当没有了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和要求,女性可以果断刚强,男性也可以脆弱悲伤。女人可以不因为忽视了家务被指责内疚的时候,男人也可以真的像歌里唱到的那样“哭吧哭吧不是罪”。
“女性可以在事业上实现自我,男性也可以在家照顾家庭。当男女两性可以自由选择照顾家庭和职场发展时,对彼此的压力会小一些,男性和女性都拥有自己的自主权和选择权。”杨菊华说。
【对话】
杨菊华:“女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红利库”
问:近半个世纪,中国女性的地位和权力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能顶半边天”;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出现“剩女”、“耻感文化”、“插队怀孕被辞退”等现象,为什么有这样的拉扯和矛盾?
杨菊华:前几十年的性别平等主要靠政府在推动,这个推动是自上而下的,是强制性,所以遗留下很多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一旦国家力量有所萎缩,市场力量更强大,问题就渐渐暴露出来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反复有一种呼声是让妇女回归家庭。因此,文化观念的改变依然很重要。
这同时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为什么企业雇主不太愿意招女孩子?怀孕休产假给雇主增加成本,再加上漫长的育儿期,女性会分散很大部分精力照顾孩子和家庭,再加上公共政策对家庭的支持很少,这个责任成本都落在了女性的身上,于是女性就处在事业和家庭的夹缝中。如果有一些相应的公共政策,比如鼓励丈夫共同休假照顾育儿,这可以减轻妻子的压力和成本;如果男性也参与家庭事务不缺位,也可以分担女性的压力。
再者,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女性的作用。比如,都说中国生育率降低,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实际上女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红利库,女性价值还要被进一步认识;从家庭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家庭要很好的发展,男女两性共同分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对家庭的核心稳定具有正向作用。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家务的分担都有助于改善婚姻质量,这是西方相关研究得出的普遍结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项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分担家务是最新的幸福婚姻密码。
责编:李婷婷
来源:小松鼠读书会
我要问



 下载APP
下载APP 报料
报料 关于
关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